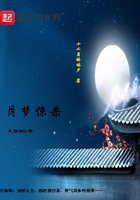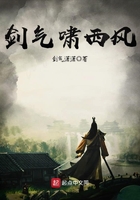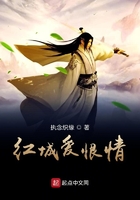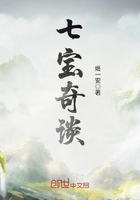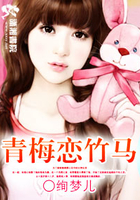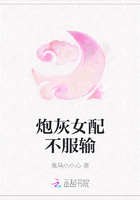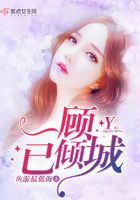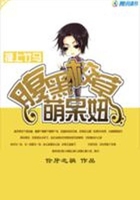浑圆的明月悬上漆黑的夜空,微弱的月光照进鬼气森森的山林。
我沿着崎岖的山路匆忙赶行,兜兜转转地不知绕了多久,最后停在一个黑黢黢的岔口前。两条同样幽黑又不知通往何处的岔路,我打量了许久,正犹豫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轻响。那声响离我很近很近,微微的动静像是——花豹!
我急忙回身,伸手去抓藏在腰后的匕首,连抓两把,匕首没有找到,只摸到一副空空的皮鞘,还没来得及吃惊和细想,听见有人冲我喊了一声,“丰年,跑!”
那话音还未落定,我已能感觉到有东西钻出草丛冲着我直扑过来,正想要闪身去躲,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翻倒在地!
阳光,就在我倒地惊醒的瞬间刺入眼睛。
梦?
我强忍着刺目的光亮,微微睁开眼睛,环看四周。一方很干净的庭院,院子中央长着一颗高高的梧桐树,有微风,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落在我身上。什么人从外面急忙忙地跑进来,小心地将我搀起,帮我掸去身上的尘土,轻声问着,“客官,您这是怎么了?”
我看着他,细细想了半天才记起自己这是在兰溪城,不觉痴痴地笑了起来,挥手让店小二走开,扶起翻倒的藤椅,坐回去,想着刚才的那个梦。
丰年,瑞雪兆丰年!
阅都,初冬第一场雪后的清晨,母亲为刚出生不久的我取下了“丰年”这个乳名,而后死于一场伤寒。父亲抱着我从中原的云国一直流落到南方的熙国,最终在卓木叔的安排下来到西南边陲,在一座名叫卓家村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
这一待就是七年。
七年间村子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过其中的大部分如今回忆起来都已经模糊不清,唯有那些与读书相关的桩桩件件清晰无比。
五岁。父亲在这一年正式地将我收为学生,教我读书识字。
按照这里的规矩,孩童拜师要举办一个或简单或隆重的拜师仪式,以示尊重。仪式上开蒙老师要亲笔为学童题写一个入学的名字,谓之曰:题名。父亲一开始的打算是将母亲留下的“丰年”二字题上,但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给我题了一个“器”字。
李器,庙堂之器。在这个连熙国教廷都很少听闻的小山村里父亲给我立下的志向可谓远大。不过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只觉得这个字好难写。
“是很难写”。父亲也苦苦地笑了,”所以你更要像东子那样用心刻苦,不要贪玩一时。”
东子比我大三岁,是卓木叔的独子,也是父亲教授的第一个学生。父亲多希望同样聪慧的我能够以东子为榜样,如他那般勤奋好学,心无旁骛。
然而事与愿违,我就偏偏没有将我的聪明才智用在功课上,而是在卓木叔的无心指引下喜欢上了打猎。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次幸运,记得我在村子西面的山岭上用陷阱捕获人生中第一只猎物时的激动与喜悦,当然更忘不了那只野兔的美味与可口。
后来的日子里每有空闲我都会缠着卓木叔,要他传授我一些打猎的技巧,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如卓木叔那样出色的猎手。
六岁。
年初的时候村子里修建多时的村庙终于完工。青砖的围墙,黑瓦的屋顶,朱漆的大门以及石板铺就的院子,这些在外人看来没什么特别,但在小小的卓家村已经够得上华丽二字。
卓木叔为此赶了五天的山路,专程去到西项县城,将消息上报给县寺的仲教大人,并从此被点为村庙的行尉。一个月后,在仲教的再三催促下村庙的主事——教者大人终于来到了卓家村。
教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气宇轩昂,更像是受了什么打击,有些萎靡不振。在初到卓家村的那段日子里,他甚至连村庙都没有出过,每天只是在大厅里讲经,偶尔给乡亲们看看病,仅此而已。不过我还是觉得新奇,每天做完功课都会去村庙听教者“讲故事”,坐在正堂的角落,精彩时聚精会神地听,乏味时盯着墙上的壁画出神。
一连几次,教者注意到了我,特意在一次讲经后把我留下,对着墙上的壁画给我讲了一个“先圣授火”的故事。我当时没太听懂,记在心里回家去请教父亲。父亲告诉我,“先圣授火”源自《大行经》的首篇《授火》,其中的“火”指的不单单是火,更多的含义是知识,看来教者是准备立学了。
几天后,果真如父亲说的那样,教者在村庙的院子里摆下书案,开设学堂。东子自然是第一个要去的,而我是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
自此,卓木叔再不对我提及打猎的事情,有的只是再三的嘱咐,叮嘱我读书要用心、要勤快。
七岁。
“各人天赋不一,以此才智不一。教者需细细教授众学子,从中选出天资聪慧者,勿使其碌碌终生埋没于世。”这段话出自双流城新任教宗的《选贤令》。
这一纸政令让教者一改往日的懒散,不仅对东子和我的要求骤然严格起来,无事时也开始在村子里走门串户的劝学。至于成效嘛,聊胜于无。
不久,县城录试的大纲发布下来:经义、诗赋、算术与通史。
四门功课里,东子只有通史和经义擅长,余下的两门稍弱。教者对此却意毫不在意,笃定地对卓木叔说,以东子现有的学识县里的录试难不住他,双流城的太学院才是东子真正该努力的方向。
卓木叔听后又惊又喜,一连几天来到家里同父亲商量给东子补题名的事宜,翻来覆去地嘱咐父亲要千万谨慎,千万给东子题一个合适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