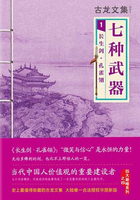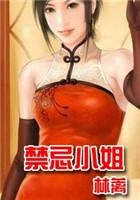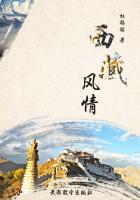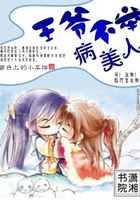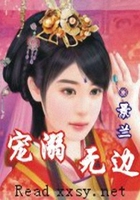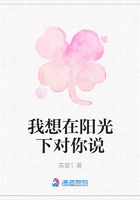来源:《清明》2012年第03期
栏目:中篇小说
我出生的第三天上午,父亲提了一瓶菜籽油,心怀虔敬去水月庵替我拜少儒老人为师傅。师傅是佛家人的俗称,其实就是干爷。
在我们那里,生下来精贵或不大好养的孩子,多会结拜干爷,而干爷的人选,最好是庙堂的和尚。假若哪个孩子能结缘到有德行的师傅做干爷,那他的一生都将得到神护,永享平安。我呢,说不上多精贵,但也不能说不精贵,我的父母已有两个儿子,再来我这个女儿,称意中自然也会宝贝我。但我拜师傅,更多地是为了好养。我出生时不到四斤,出世两天还不知吃喝,让父母忧心忡忡。这怨不得在母腹里只待了七个月的我,更不能怪母亲,母亲生我那天还在“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挑土围堰,我也被人笑称为“堰生”了。看着小病猫一样的我,父亲和母亲干着急,一心巴望我能开口要吃喝。我的大哥子实长我六岁,二哥子成长我四岁,在堂屋边帮父母搓草绳时,他们并不明白我的处境,居然也戏称我“堰生”。父亲不让他们这样称呼我,一心想给我取个好名儿。母亲把我往怀里窝了窝,说:“别费神了,俗话说得好:‘七生八落’,叫‘七成’吧,这名儿旺相。”父亲一听,重重地一拍脑袋:“求旺相,去水月庵呀,找少儒老人替女儿讨个佛名,再拜他作师傅,孩子不就好养了。”父亲母亲一拍即合,心下的担忧竟然去了不少。
三朝一大早,父亲和母亲用艾水给我洗澡,在水中我有了活人形,让父母欢喜不已。
母亲说:“看来七成这孩子命里注定要过继佛家,这事儿一说破,就灵光多了”
父亲说:“是嘛,水月庵的菩萨晓得我家的情形,照应着呢,我还是早些去。”说过,放下手中已搓柔的婴袍,先出了房门。
母亲替我穿好婴袍,将我层层包裹好,抱着我偎进床里,再次试着给我喂奶。这次我居然能含着奶头,虽说是浅浅地吸吮,总算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此时,父亲在堂屋又重新温了一盆水,放进艾叶浸泡一阵,再拿毛巾将自己的手脸净过,又将身上的衣物抹一遍,方才提着油瓶出门去。
水月庵离我家并不远,沿着平缓的河堤往上游走约两里路。正是初秋时节,河堤两岸的芭茅高举着穗,随风扬来荡去,搅得阳光璀然溅射,洒在一旁低矮的枯叶和灌木上。芭茅丛中相距三两米便有一棵桐树或木梓树,桐树的叶子已枯败,几乎掉尽,枝头挂着大大小小已然成熟的桐子。而木梓树的树叶依然笑在枝头,叶片儿呈渐变色,有橙黄、橘红,只等秋霜一来,一树树的叶儿全红了,如花开在深秋,到那时木籽儿自个儿脱了深灰色的硬壳,露出一球球洁白的籽儿来,缀在红叶儿渐渐稀少的枝头,扯着路人的眼。路过这里的人见了,赶紧着捋点,送供销社卖了,换回斤半盐或一管牙膏什么的日常所需。
路才过半,父亲远远瞧见少儒老人攀在一棵桐树上摘桐子,桐树边站着傻兮兮的忠友儿,张望着树上的少儒老人,脚旁摆放着两只筐,筐上横条扁担。
少儒老人每摘下三两桐子,就递给树下的忠友儿。忠友儿摇头晃脑接过来,低头把弄一番,才放进筐里,继尔趴在筐沿边,冲着桐子傻傻地笑,涎水长长地流出来,傻笑着任垂涎自箩筐牵到他的衣服上。少儒老人下树来,替他擦弄一把,顺手拍拍忠友儿身上的沙土。
忠友儿不仅天生痴傻,而且不会讲话,平时总是悄没声息的,喜怒时直着嗓子大叫大吼一阵,过了气自个好了。小的时候爱哭,有时是身体某处疼痛,有时不知因由地独自垂泪。问他吧,他又不会说话。于是大家猜测这孩子肯定是受了难言的委屈,许多人叹息他,也只是叹息。
少儒老人与他同村,都是叶家庳人,整个村子没有旁姓,全姓叶,一个小村落就是一个大家。忠友儿的父母在他年幼时相继过世,小小的他成了孤儿,虽说大队里有衣食照顾,可因他智障不知伺弄自己的生活。小时候的忠友儿时常溺坐一处,模样脏兮兮的,惹虫长虱,人见了多多少少生出嫌厌来。一个夏夜,少儒老人路过村头的一口粪宕,看见粪宕里有个人的影形,近前看个仔细,竟是忠友儿在里面睡着了。少儒老人一把将他拉扯上来,叮在忠友儿身上的蚊虫们“嗡嗡嗡”地四散而飞。少儒老人牵着他到河边,细细地将他洗净,领回自己的住处,做了饭让他吃,吃得一头汗水,少儒老人在一旁替他用蒲扇扇着风。忠友儿吃饱了倒头便睡,全然不知致谢,更添了少儒老人对他的怜惜,细晃晃地摇着蒲扇,扇了一宿。这事没过多久,忠友儿又差点吊死在一户人家的猪圈里。
那是一个上午,大人们出工去了,孩子们扎堆在田头河边玩耍,忠友儿在一户人家的猪圈里,将系猪的活套绳子套上了脖子,不知机关的他,用力拉扯绳子的一端,勒得自己直翻白眼。身体本能的反应,却让少知的他更加用力扯着绳子。正好少儒老人路过,见这情景,跑过去解救了他。忠友儿一缓过劲来,便对着少儒老人嚎淘大哭,少儒老人眼也潮了,回到家里,眼前老是晃着忠友儿被绳子勒住的模样,夜里也无法安眠,思来想去决意收养忠友儿。
那时少儒老人还在保管屋旁的小坯屋里住着,负责照看生产队的九头耕牛。
五岁的忠友儿自此在世上这才有了个可以依赖的亲人,对世事从不知问根由的他,时日天天,也只认少儒老人为亲人。
父亲对少儒老人和忠友儿的根源是详尽的,对少儒老人有着向来的敬重,远远瞧见年过半百的少儒老人带着少年忠友儿,心里添了几分怜惜与关爱,遥隔数步就大声招呼:“少儒叔,下桐啊。”
少儒老人呵呵笑,说:“下点桐,换俩钱给忠友儿买双球鞋。”
父亲加快步子走过来,及至跟前,从深蓝布褂里掏出半包“圆球牌”香烟,抽出一根,递给少儒老人,一旁的忠友儿看着,嘴里流出涎来。
父亲在忠友儿头上扭摸一把,说:“这个你吃不了,有给你的。”说罢,掏出几颗糖,让忠友儿双手拿住。忠友儿喜得闭眼笑,双手胡乱的抓握,糖也撒到了地上。少儒老人弯腰拾起,剥一颗塞进忠友儿嘴里,其他的替忠友儿装着。忠友儿吃着糖,一屁股坐进箩筐里,少儒老人任他自个儿玩耍。我父亲划了火柴,替少儒老人点上烟,自己也吸上一根,向少儒老人说了来意。
少儒老人一边听着,一边点着头,从箩筐里拉起忠友儿,将半筐桐子儿倒一半到另一只筐里,父亲拿起扁担替少儒老人挑起。少儒老人提着父亲给他的一瓶油,一起往撒满阳光的水月庵去。
水月庵坐北朝南,远远地便能瞧见暖黄色的外墙,墙面多处剥落,露出里层的白底来,更显出庵堂沧桑的意味。屋顶上的青灰黑瓦依然铺压得紧实,称得住前门厚重的双扇大木门。水月庵有正堂一间,宽大周正,先前供奉着菩萨和神佛,而今做了学堂。东西侧各有一间抱厦小厢房,将庵堂紧紧护卫着,西厢房先前为僧人的寝室,东厢房为他们的伙房,恰似精致简妙的人家。
一条小河汇聚了山里的几支泉流自西北方向流淌过来,到此又分成两支,一支叫睡港,绕庵堂后向东南方向去,流经畈野荒湖;一支叫醒港,入了水月庵门前的沁塘,又自西南方向流经我家的前塘及至沿途村庄的塘港,远远地两支小河港最终都归依了巴水河,入了长江。
沁塘面积不大,约两亩见方,呈满月形。上午的阳光好,虽说入秋水瘦,但更为清亮,尤显波光粼粼,反衬得水月庵一派的温厚祥瑞。
恰这时,庵堂内老师领读学生,一片朗朗读书声起,向水月庵四围融融散开。一群鸟自庵堂后不远处的万家店村叽叽喳喳飞过来,有的停落在庵堂前的树上,有的飞落在庵堂高翘的屋角上。忠友儿瞧见,挥手冲着它们高声大气地叫嚷,嘻笑一番。
父亲随少儒老人绕过庵堂后临架在睡港上的凉亭,进得水月庵的倒厅。倒厅已与前堂完全隔断,正墙上并排安放两口木格窗,保持已做教室的前堂空气流通,少儒老人将倒厅做了厨房,倒厅向东向西各有一小门进入厢房,少儒老人和忠友儿住西厢房,东厢房空闲着。
两百多年前万家店村一告老还乡的官人,行至水月庵处,见几处山溪至此汇聚一起,又自此一分为二,便决定在此建下水月庵,锁住三围山乡的钟灵之气,以便后世多出有用之人,还可以给附近的乡民一个息事安神的去处,顺带压服捷山上那些非寿终正寝的苦鬼怨魂。
由那时起,千人万命在活路上走,遇到迈不过的坎,便来这里絮叨一番,离开时把心中的坎尽管地放在这里,交由水月庵的神佛去理料,人们相信神佛会照拂心中的善求,自己安然卸下包袱。
文革时,水月庵的僧人被逐赶后,庵堂本也是要毁的。只因领头打菩萨的人一夜之间高烧不退,胡话连连,说的全是天神鬼怪的怒言咒语,人们惶恐开来,没人敢再动手拆除水月庵。后及至水月庵周边的一草一木没人敢去动,水月庵就此保全下来。
水月庵的菩萨被打砸没多久,附近的村庄纷纷闹起鬼来,天一擦黑家家关门闭户。人们纷纷传言水月庵的菩萨一打,惊走了镇邪的神佛,捷山的恶鬼趁机放了敞关,下山来吓唬逗弄山下的活人,若有时机,也可以将某些人变成鬼,来壮大它们的队伍。
一天晚上,本大队的书记做了一梦,梦中有神仙指点,说水月庵不能空置,要派上公用,必须派上个有德行的人来守持,只有这样才能免去他的灾难,水月庵的四乡八邻才能逢凶化吉。书记醒来,惶惶难安,下半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办法,天明时总算有个主意。
一大早,他就去大队部用高音喇叭下达了召开大队支委紧急会议的通知,支委会其他成员像他一样饿着肚子赶到大队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商定好将水月庵改制为学校,定作本大队小学生学堂,只设一个班级,三年后这个班级的学生转插栗寺中学里的小学班就读四年级。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守庵人,书记让大家提名几个人选,并告诉他们,他推选的是少儒老人。
少儒老人幼年得了祖上的庇护,读过几年私塾,能识文断字。六岁那年,重病一场,为了求得神佛的庇护,他父亲将他送至水月庵做了俗家弟子。少儒老人家离水月庵不足一里路程,常去庵堂走动,师傅们喜欢他,给他讲佛性法理,经年的润浸,对世事人情自然显得比同年龄人通达许多。可惜在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他只能辍学在家学耕作,耕作之余帮母亲照顾四个弟妹。二十岁那年,母亲故去,他便担当起家长的所有责任,料理四个弟妹成房立户。等安置好了他们,世事已几番轮变,换了人间,早年的家底多年前就已归公,可收留的小物件先后给了弟妹们。年近四十的他婚事早给耽搁,弟妹们各自成家后,也想过帮大哥讨门亲,可有心难照月。那时候穷人有个贫下中农好出身,可以昂头做人,而他们一家子必得处处显出低微来,替大哥讨亲的心事也只是一番空想。后来少儒老人收养了忠友儿,他们也算是有了去疚的理由,大哥的婚事是他自己愿意耽搁的,与他们不相干。
知道少儒老人的人,没有不敬重他的。即便是运动来了,大家也不过依样儿做做,并不当真。
好在大队书记是明白人,转得开,明白乡里乡邻,不能搞得活人要死死人翻身,处处不太平。他对与会的人讲:“少儒是改造的对象,水月庵是破四旧的对象,我看他住水月庵正合适,你们说呢?”大家心知肚明,看似对少儒老人的惩罚,实则是对他的照顾,住水月庵比住他的草棚屋踏实,也合乎他们的心事,都举手赞成。
自此,少儒老人带着忠友儿一起住进水月庵,水月庵上空又有了一日三餐的炊烟,增添许多活色。有他们住进水月庵,附近乡村渐渐安然下来,捷山的野鬼游魂好像也得到了安抚,再没人撞见它们。人们又传言,少儒老人不比常人,他是有道行的人,至于什么道行,没人说得清楚,反正他能稳得住人镇得住鬼。
再过不久,学堂也开了课,从此白日里水月庵又多了两位老师和二十来个小学生,倍添生机。
父亲随少儒老人进了水月庵。少儒老人端盆水净了手脸,带他进了东厢房。厢房靠南墙正面摆着一瘦脚桌,用蓝布蒙着,桌上摆着一陶钵,里面盛着半钵洁净的河沙。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悬空支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有个深灰色的小木盒,少儒老人取下它,盒盖是抽拉式的,从中拿出一个小册子,掀至一页面摆好。又掀起铺在瘦脚桌的蓝布一角,露出两只带铜环的抽屉,自一抽屉里找出一方砚、一支毛笔及半瓶墨水。
父亲有点茫然,问少儒老人要不要拜菩萨。
少儒老人捻开笔,说:“眼面前没菩萨供你拜,这事也依不了先前的规矩,我就随‘七成’的名字派生一个佛号吧,送她‘慧成’你看么样?”父亲连说要得要得。
少儒老人重新饱蘸了墨,一笔一画将“慧成”二字落在一禅师父名下,我就此成为半个佛家弟子。一禅师父是谁,我一直不知,父亲和母亲只当少儒老人是我的师傅我的干爷,是少儒老人的干女儿自然会和佛结成亲,佛就会保佑自己的女儿长大成人,所以从来没想过要问一禅是谁。多年后长大的我,无意中翻看到这一笔,心念丛丛,其时少儒老人已过世,无法考证,在心里,我想一禅便是少儒老人——我的师傅。
父亲讨得我的佛号,欣喜不已,对少儒老人感激不尽。少儒老人嘱父亲道:“慧成百日,定要带她来水月庵敬佛祈愿,莫忘了。”
父亲满口应承。一路兴冲冲回家来,见母亲恬然抱着睡熟的我,心下更生欢喜,一个劲地对母亲说:“桂兰,好多年没进庵堂的门,现而今的水月庵呀,神仙味更浓了,一进屋不光身子轻了,气息也松畅多了,你说怪不怪?”
母亲笑看着父亲,听他称奇道怪地讲来。她告诉父亲在他去水月庵后,我开始在母亲怀里吃奶,尽管吃得仍是不多,已经有劲了,冒汗了。母亲也能感到我用力地吸吮,她看着我和父亲,笑意不尽,身轻体盈,坐在床上,如同坐在晴空里的一团洁白云朵上,舒心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