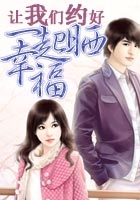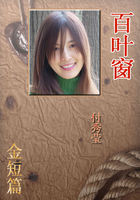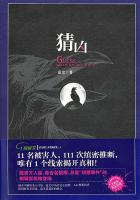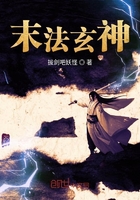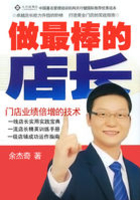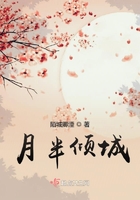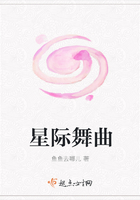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排行榜
她一生和文革期间整丈夫的人斗,和厂领导斗,和小区物业斗,斗来斗去,终于成为“掌权者”。期待中的美丽新世界能否随着权力一起到来?成为“强者”后是否还需捍卫权力,战斗能否就此停止?
我和苗秀华这个人的缘分,大概是从1997年开始的。
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厂当技术员。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厂子的主要产品是半导体二极管,所以被周围的老百姓称为“管儿厂”。作为一个兴趣集中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年轻人,这个工作自然让我提不起兴趣来。而且单位的状况半死不活的,待遇也很一般。说得赤裸点儿,我之所以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进京指标而已。我的计划是,好歹混上两年,等到户口办完,立刻就辞职,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一放,然后到中关村找工作去。
既然无心久留,我在厂子里的生活便相对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儿超然物外。那些仨瓜俩枣的好处我懒得去争,同事之间谁和谁抱团儿或者成了对头,也都和我没关系。这种生活态度的优点是省心,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电脑知识;缺点呢,就是没交上什么朋友。除了科室里那几张熟脸以外,厂子里的其他人我几乎都不认识。
饶是如此,还是早就听说了苗秀华的大名。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我到行政部门办完手续,扛着被褥到宿舍去安家,一位管后勤的老师傅向我介绍了各种注意事项,又专门说了一句:“在管儿厂上班,三样东西不能惹。第一自然是厂领导,第二是保安队的那条黑背狼狗,第三就是苗秀华。”
“特别能战斗”,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全厂同事对苗秀华的评价。她有多能战斗呢?后来大家又对我讲了很多事例,因为年代久远而又往往事不关己,便像是在讲一些喜剧色彩浓郁的奇闻了。
待了几年后,我离开了厂子,此后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差强人意”来形容。虽然想一想年轻时对自己夸下的海口,总有壮志未酬之感,但是通过付出比那些“有门路”的人多几倍的努力,我的收入总算有了不小的提高,貌似能够混进体面人的堆儿里去了。在中关村那块地方,我先后又跳了两次槽,终于从本土小公司进入了一家跨国集团;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关系以后,我又痛下决心再次辞职,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网络工程公司,主营业务是给一些餐馆、写字楼铺设内部的局域网系统,还代理了几种后台管理软件的安装和维护。公司总共就七八个人,活儿紧的时候还得由我这个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亲自扛着机箱扯着电缆上阵。不过应了那句话,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我想我有权力活得腰杆硬一点儿,理直气壮一点儿。
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2007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北京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之后,我终于买下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几乎耗尽了我的积蓄,还让我背上了沉重的贷款,但是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了。都说砸锅卖铁买房的人叫作“房奴”,但签完购房合同的那一天,我心里反而有了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楼体还没有封顶呢,我就会三天两头地开上公司的那辆破捷达,到小区的工地外面转圈儿。看着那噪音隆隆、飞沙漫天的景象,我百感交集地憧憬着:啊,以后就要在这片热土上安居乐业、繁衍子嗣了——当然,眼下还缺一个年貌相当的女青年。
我们那个小区并不大,一共只有三栋楼,都是15层,两栋是板楼,一栋是塔楼。板楼南北通透,早晚都有充足的阳光,且建筑的利用率也更高,但以我的财力,却只能屈居在塔楼里的一套80平米的小两居里。小区的位置呢,在五环以外,南接立水桥,北邻天通苑。在当时,这儿并不能算是多么好的地段,如果不开车的话,到城里办点儿事得倒上两三趟车,路上就要消耗大半天。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贫乏得很,商场医院学校的影儿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售楼小姐承诺说,那一切都会有的。她还用激光笔在沙盘上傲然地画出一道红线:从这儿到这儿,将是北京最宽最长的绿化带——天然氧吧呀。而此时此刻,天然氧吧还是一片废弃厂房和城中村,几起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都是在那片区域里发生的。
在望眼欲穿中,又过了将近一年,三栋高楼终于建成竣工了。为了“回馈业主”,开发商在交钥匙之前还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一等奖是全套的家用电器,其余的奖项等而次之,从床上用品到微波炉电饭煲都有。因为中奖率是百分之百,抽奖那天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到齐了,大家本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精神,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我观察了一下与会者的年龄构成,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这种三十多岁的也有不少,其中的很多女性都带着孩子或者挺着大肚子。也就是说,我们的邻居将以“过日子的人”为主,我们的小区将来也会人气很旺——不像一些精装修的酒店公寓,住满了香艳无比身份可疑的大美妞儿,也不像那些动辄300平米的豪宅,房子倒是卖出去了,可是一年到头空着,业主都不知是什么来头的世外高人。
在一片闹哄哄之中,那个很可能是从婚庆公司雇来的司仪说了一套吉利的片儿汤话,然后便由礼仪小姐抬上来一个大纸箱子,再请地产公司老总从中抽出一个一等奖,五个二等奖,十个三等奖——剩下的就全是“鼓励奖”了。
公司老总是个白白嫩嫩的中年人,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身材在中国的有钱人里还算保持得不错的了,起码穿西服的时候能系上扣儿。他先恭喜大家即将乔迁新居,又感谢大家选择了他的项目,最后便是保证此次抽奖一定公开公平,诚信第一 ——这也是他们公司历来做事的宗旨。尽管废话居多,但是大家听的时候,还是专心致志,甚至有不少人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抽奖这种噱头,从来都有这种效果,其蕴含的悬念往往比奖品本身更能吸引人。我们看着公司老总颇为作秀地晃了晃手腕上的金表,像电影慢动作一样把胳膊往纸箱子里伸进去,伸进去。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发一声喊:“等等!”
不光是台上的老总和工作人员,就连在场的全体业主都愣了。众人一起往会场的边缘看过去,目光落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黄脸上堆积着不少褶子,梳着“革命老大姐”式的短发,穿一件灰蓝相间的棉布运动服,整个人显得朴素极了,两只眼睛却放射出炯炯的精光来。
还是老总反应快:“这位女士,您有什么疑问吗?”
“我对抽奖的方式有疑问。”那女人响亮地回答,“我觉得这里面有作弊的空间——你们可能把大奖分配给关系户。据我所知,那些关系户买房的时候就拿到了远比我们一般人大得多的折扣,这时候再把大奖都包了圆儿,那也太不公平了。”
她把话说得这么直接,自然很让人下不来台。老总的脸色登时僵了,口气也有了点儿抢白的意味:“您怎么能凭空这么说呢?给哪个顾客什么样的折扣,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政策,咱们在这儿先不说了,就说说抽奖吧。业主的房号都写在纸条上折好,箱子又不是透明的,我怎么可能作弊呢?退一步讲,我就是想作弊,怎么作呀?难道我有特异功能吗?”
女人的回答却毫不含糊:“你蒙傻子呀?要想作弊容易得很。比如,你们可以把想抽中的那些房号的纸条事先放到冰箱里冻一冻,这时候手伸进去,哪儿凉往哪儿摸不就行了吗?”
老总白嫩的脸已经涨红了,随即又发了青:“你、你这不是阴谋论吗?请您不要捣乱好不好。”
“阴谋论不阴谋论的,得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阴谋。”女人继续大声说,又扫了一眼旁边的业主,“也许我的确是冤枉你们了,可我也有权利讲出自己的怀疑,对吧?按照我的思路,你们确实不能避免弄虚作假的嫌疑。我认为,抽奖这事儿虽然不大,但也得给在座的诸位一个交代。如果这件事儿都不能安心,那么住进来之后还有什么事儿能安心呀?”
她这一搅局,会场里便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了。并且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竟然是支持她的。这一来是因为“冰冻作弊法”这个推测的确有一定的科学性;二来则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太太和贵气逼人的房地产公司老总之间,大家会下意识地支持前者。有钱、有权、有背景的人遭到迎头痛击,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大快人心的。进而,又有几个爱凑热闹的业主叫了起来:
“这位大姐说得对!”
“要杜绝作弊!”
“我们都是花钱买房的,我们要公平!”
一时间,很有一呼百应的气势。这样一来,房地产公司老总的脸面就真挂不住了,他气呼呼地退到一旁:“我不抽了!我避免嫌疑行了吧?那你说,这奖该怎么抽?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举办这个活动!”
那女人也真不含糊,她索性噔噔噔地走上前台去了。跨上台阶的时候,她的步伐甚至称得上矫健,那一瞬间很不像五十多岁的人。站在聚光灯下,她大声宣布:“奖还是要抽的,避免作弊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抽奖人是我们业主的自己人,不是开发商的人,那不就行了吗?我来在现场替大家选一个抽奖代表,你们说好不好!”
几个支持者立刻又说好。那女人的眼睛便在观众席上扫过来,又扫过去,脸上的表情极其严肃,仿佛在执行多么重大的使命。而这时候,我一直愣愣地看着她那瘦削的腮帮子、高高凸起的颧骨,回忆着什么又感怀着什么。相应地,当她的眼睛落在我身上的时候,居然停下了。
“那个小伙子,你替大家来抽奖好了!”
在周围人的掌声中,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往台上走去。和她近距离地打了个照面,我点了点头,本想说:苗姐,几年过去了,您还是这么能战斗啊。但苗秀华并没认出我来,她凑近身来,认真地叮嘱道:“摸仔细点儿,万一要是有几张纸条比其他纸条的温度低,那就千万别抽出来。作为业主,咱们得捍卫自己的权利对不对?”
说得我也有了神圣感,郑重地把手伸进箱子里抓挠起来。抽奖完毕,房地产公司的人怏怏离去,中了大奖的几个人则凑过来感谢我的手气,其中还有个老太太开玩笑说,要雇我到麻将桌上去替她摸牌。总算散了会,我却特意没走,拎着一套“纪念奖”的刀具,在会场门口等候苗秀华。北京这城市太大,除了几个至亲和熟人,大多数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擦肩而过。而重新见到这位故人,偏巧将来又要做邻居,让我感到既惊喜又奇妙。
没片刻,她也出来了,手里也拎着一套刀具。但此时我记得苗秀华,苗秀华却不记得我。我立马高呼,她横刀一愣,随即令我通名报姓。直到我说了管儿厂的那段同事之谊,她这才“啊啊啊”了几声:“好像有印象,好像有印象。”
又补充说:“我说看你有点儿面善呢……如果早点儿记起来你,我就不该推举你上去抽奖。那不成了任人唯亲了吗?”
然后,我们两人手持兵刃,全副武装地叙起旧来。说起各自的近况,以及原来单位的事情。管儿厂大致还是那副老样子,虽然换了一拨儿新领导,又上马了好几项新技术,但效益总是不咸不淡的,大伙儿越发磨洋工混日子。苗秀华年过五十五,已经退休,她和她老伴儿卖掉了城里的小房子,又把毕生的积蓄都添了进去,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140多平米的三居室,打算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可是她没本事把自己嫁出去,我也得给她预备着一间房对不对?”苗秀华抱怨说。
我恭维道:“就冲着您家那么大的房子,多少人倒插门儿也乐意啊。”
苗秀华得意地对我把眼一翻:“那你结婚了没有?要不你插吧。”
对于她这个略显突兀的玩笑,我的脸蓦然一红,不好搭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