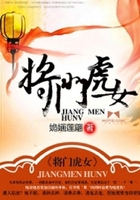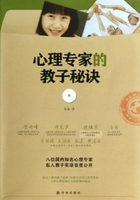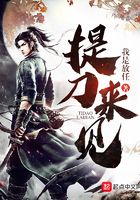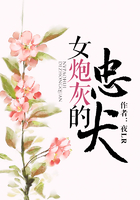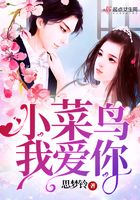黑头比我大一岁,虎墩墩的一个闷嘴葫芦,但他识数早,刚刚会讲话时就识数了,5岁时就会派账了,多少加上多少等于多少,多少减掉多少还剩下多少,他都知道。那时,我几乎还不识数。有好多比他大的,甚至是大人,算不过来的账拿给他,他都能帮你算得清清楚楚,一丝不差。村里人都说,黑头长大了,最孬熊也会超过他的太祖爷李举人。他的力气也很大,别的孩子搬不动的东西,他一伸手就拎了起来,别的孩子上不去的树,他一抬脚便上去了。那时村里人洗衣服用的皂角,多半都是黑头爬到树上打下来的,那皂角树上的刺可比刺茉苔的刺怕人多了——黑头不仅胆大,而且心细。
可是,黑头的手上老是拉着一个妹妹琼子,琼子就像是黑头的一个尾巴坠子。琼子比黑头小两岁,走起路来歪跶歪跶的,一笑两酒窝,虽然长得很好看,但除了黑头,我们都不喜欢她,嫌她累赘,喊她“大陀螺”,喊她“跟屁虫”。
琼子的羊角辫的辫根儿上老是戴着两朵花儿,要不是栀子花儿,要不是石榴花儿,要不是月季花儿……此刻,她的辫根上就插了两朵金黄色的茶苕菜的花儿——跟五十年后我在倒庄地看到的茶苕菜花儿一模一样。
黑头挨麻胜打的时候,琼子吓哭了,黑头却摸了摸头,闷闷地笑,还伸手去帮琼子抹眼泪。
在麻胜轰我们的时候,我心里想到了二姐教给我的一个谜语:
雨洒茔灰地
靴子蹅烂泥
园里虫吃菜
翻过来石榴皮
菊子是麻胜的堂妹,菊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得了痨病死了,过了三年,母亲也死了,是给奶奶活活逼死的。后来奶奶也死了,是菊子的姥姥家人上门来折磨死的。听说菊子姥姥家的惩罚方式是“点大麦”——在菊子奶奶屁股上用做鞋的长锥子扎上一个个窟窿眼儿,将炒熟的大麦一粒粒塞进去,再用鞋底子使劲地抽,直到菊子奶奶疼死为止。我们当年在听大人讲述菊子奶奶被菊子姥姥家用点大麦的刑罚折磨致死的故事时,并不感到有什么害怕,而老是觉得自己的屁股也像被点了大麦,胀胀的,痒痒的,很难受。
菊子自小是在叔叔家长大的,可不多久叔叔婶婶也都得病相继去世,村里人都说菊子命硬,爷爷和堂哥一点也不喜欢她,甚至还恨恶她。但菊子因为长相出众,却被邻村一个在外做事的年轻人相上,她就成了一个拿薪金人的家属了。
菊子化了妆,穿戴得周吴郑王的,从床上下来,被她堂哥麻胜背着,从房屋里出来,走到大门口时,麻胜停住了,让菊子用脚在装满米的斗里刮一下——这是风俗,那刮下来的米代表新娘子对娘家人的挂牵。
菊子一直在哭,嘤嘤的,很伤心,却又显得很平静很乐意的样子——我想她是应当高兴的,去了婆家,就用不着成天面对着那张长满黑狗屎麻子的脸了。
突然大风刮了菊子的盖头,我们被菊子那张好看的脸一下子惊呆了。
“妈啦!好——好看哟!”枣子竟然鬼惊神诧地叫了起来,他把两个“好”字喊成了蹿天的炮仗,瞿溜溜向上飙。
被风吹去盖头的菊子,像水葱白一样嫩生的脖子,腮红红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也是红红的,头上插了朵艳艳的红绒花——是那种摸上去软绵绵绒嘟嘟的花儿,这花红得耀眼,红得夺目,本来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盘在了脑后,发髻这么一堆一叠,一根带穗子的银簪子往中间这么一别,那头就好看得没法形容了——菊子真是太好看了!就像闹洞房时人们唱的那样:
照照新娘头好
乌云盖倒
照照新娘肩好
杨柳飘飘
照照新娘腰好
骑马带刀
照照新娘脚好
三寸尖椒
菊子除了没有三寸尖椒外,其余的都绰绰有余,菊子最好看的还是她额上的那粒红豆一样的小朱砂痣,书上叫它痦子。这个痦子正好长在菊子的眉心处,像是故意点上的美眉俏,整个一张脸,整个一个人儿,都像是从画子里出来的,难怪喜欢虚惊的枣子要那样打声煞嗓地叫好。
枣子比黑头还大一岁,但看上去比我还小。枣子妈妈的眼睛瞎了,爸爸得了咳嗽的毛病,老是咳不好,日子挺寡淡的,想必就是这样的日子才让枣子长不起来的。枣子还有一个姐姐,13岁了,名叫桃子,成天打马草拾马粪的。枣子的家是桃子在顶着。
菊子被大红花轿抬走了,我们先还跟着轿子拼命地撵,可撵着撵着,就跟不上了。哇哩呜哩的唢呐声一丝一丝地远去,一丝丝地远去,像风一样,飘飘悠悠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好听,我们的脖子都挺酸了,那风声里好像还有唢呐的响声……
养丫头,编笆斗
上南冲,点豌豆
豌豆发芽,丫头长大,
豌豆开花,丫头出嫁,
豌豆结籽,丫头有喜,
豌豆收进筐,丫头想亲娘……
村子又归于了宁静。
我们从新娘菊子花轿里摸出的花欢团儿,攥在手心里都捂化了,也舍不得吃。
记事越早,记事越多,它对于一个生命里充满苦难的人来说,恰恰是一桩不幸——有限的人生又能承受多少生命之重……
都道“计四——记事”,也就是说,孩子一般到了4岁(指虚岁)才开始记事,我却周岁还不到就开始记事了——这或许就是天赋吧,却是算不得什么本事,记事越早,记事越多,它对一个生命里充满苦难的人来说,恰恰是一桩不幸——有限的人生又能承受多少生命之重!
1954年的冬天,我刚满周岁。那天早上起来,母亲为我穿好了大袍子,把我抱放到堂屋门后一个烧得热乎乎的站桶里。这个站桶是木头箍成的,下方有个隔板,隔板的下面正好可放一只用火煤或粗糠烧就的火盆,冬天让小孩子站在火桶里面,非常暖和。母亲把我放下后去开门,她拔了插在木榫上笨重的门栓——当大门刚刚罅出一条缝隙时,就见一壁雪墙从外边突然倒进家来,我站着的火桶被打得直往后仰。
后来母亲说,这叫封门雪(1954年江淮地区的大雪灾在中国气象史上是有记载的),这段景象是那样清晰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同一年的春、夏两季(那时我更小,才几个月大),国内不少地区曾闹过“毛人水鬼”事件。突然间,中国大地上,特别是乡村,一下子冒出了数不清的鬼怪灵异,有人声称亲眼见过那些鬼怪,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浑身长毛,看见孩子就一口咬死,看见妇女就剥衣强奸,看见男人就扒心割蛋,还说这割掉的东西可以用作制造原子弹……
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政府下文破除迷信,说这是国民党潜遣特务和反动道会门在装神弄鬼,号召各村各社每到晚上将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男人轮班巡更。
史仓有一座被改成了生产队仓库的原史家小姐的绣楼,这绣楼虽是土坯垒就的,但非常坚固,临在壕沟边,三面都是水,只有一道窄门通着花园墙的拱门。村里的妇女孩子都集中在这绣楼里,虽然感觉安全了,但由于人多都挤在了一块,跟包肉饺子似的,令人喘息都觉困难,大家的心弦绷得更紧。
那绣楼有上下两层,每层只有一扇窗子,这时窗子也都被稻草捆子堵上了,不给点灯,黑咕隆咚的,眼睛睁着跟闭着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是那种非常非常可怕没有一点松动的板板实实的漆黑,这种漆黑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好像除了梦魇时遭际的那种扯不开推不掉的黑暗之外,再不曾遇到过。
人多,地点太小,大人们都只能坐着,背靠背地睡觉,孩子就躺在各自母亲的怀里。大人们不准说话,孩子们也不能哭,怕鬼怪们听到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不止一次用她的乳头塞进我只想大哭的嘴里,那种憋屈的感觉至今想起还是那么清晰。
这时男人们则拿了锄头钢叉围着村子转,他们经常被一只猫或一只蛤蟆吓得屁滚尿流。
一天夜里,我突然在一阵尖叫声里醒来,绣楼的大人们都在喊叫,孩子们都在哭闹,漆黑一片的楼桶像要炸开了一样。
后来听说造成这次震动的事件来得非常蹊跷,原本黑漆漆的夜空中,突然有一道约半里路宽的蓝莹莹的亮光,带着哗啦啦的响声,从龙穴山下飞扫过来,自南向北,速度像射箭一般,所过之处,草丛里掉的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按现在科学知识,我们可以为这种天象找到根据,但那时在尚不知道电为何物的乡下,发生了这样的奇异事情,确实令迷信的人们胆战心惊。
自此,在乡下孩子们的摇篮边,遇上哭闹的孩子,常会听到这样的摇篮曲:
红眼绿鼻子
四个毛蹄子
走路叭叭响
单咬哭孩子……
这种人为造成的恐惧和黑暗,开发了一个孩子的特殊记忆,它印在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的脑海中,一直伴随我从小到大、到老,直至今日,它仍然那样清晰,那样令我心颤。等到我会说话时,我把这些细节说给大人们听,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是我自己看见是我自己记得的,但母亲相信,因为我说的细节跟她当时所看到所经受的完全一样。母亲相信我还不到周岁就有记忆了。
母亲一辈子生了九个孩子,两个哥哥都在四岁之前夭折,七个女孩子中,有一个姐姐刚生下地时被姥姥扔在尿桶里溺死了(那时乡下溺女婴之事很普遍),其余的都活了下来。
我是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按存留下来的姐妹顺序算,我是老五,五子也就成了我的小名。我与大姐胡传荣之间相差17岁,与二姐胡传芝之间相差12岁,三姐李益缘和四姐王运生后来抱养给了人家,随了别人家的姓。我还有一个妹妹,叫胡传勇——我叫胡传永,这是方言的失误。我的“永”在方言里念“yun”,与“匀”同音,而妹妹的“勇”就念“yong”,一直到二姐上初中时有老师会讲普通话才知道“永”、“勇”二字是同一种读音,于是她把妹妹的名字改成了胡风琼,但我还是乐意叫妹妹为勇子,直至她50岁的今天。
1957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们去看菊子出嫁的时候,大姐的女儿远铃也有三岁了,因为胎带兔唇,讲起话来除了家人别人都很难听得懂。孩子们都喊她豁子,不愿带她玩,天生好性格的远铃也从不为自己受到冷落、受到屈辱而生气,总是乐呵呵地跟在我们的后面东跑西颠。我虽然只比远铃大一岁,却以“五姨”自尊,在保护她的同时,有时也拿她的强,譬如把本属于她的玩具据为己有,譬如让她替我搪罚挡灾,代我在大人面前受过。妹妹勇子还小,躺在摇篮里,不到一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多少关于父亲的印象。父亲是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就被椿树乡政府提到镇合作社当会计去了。有这份不要下农田干活的工作,不仅是由于父亲过去当过私塾先生,又当过米行的朝奉,在龙穴山下除了黑头的父亲李彦祯,就算他是一个最有文化的人了,同时还因为我有一个比菊子更漂亮更能干的大姐。大姐胡传荣年轻时的姣好长相以及她的勤劳,她的灵巧,至今在龙穴山下仍然是老辈人的一个美谈。当时乡政府里有一个名叫鲍敏的青年干部,他作为工作队的一名成员,来史仓曾见过我的大姐。他向大姐求婚的方法是先将老丈人收买。大姐答应比她大上十多岁的鲍敏的亲事,也多半是为了不会农活的文弱书生般的父亲和一大阵“萝卜丁当”(大姐语)的妹妹们。那时三姐已经被母亲的一个堂哥抱走,四姐还在家中,大姐的下面还有四个妹妹。我们家从椿树镇下放到史仓参加土改,没有男劳力的家有多么艰难,我大姐是一本清册的。
父亲非常热爱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一年到头很难回家一次,偶而回来,都是赶在晚上我们都睡了以后,到他早上走的时候,我们又都还没从早晨的酣睡里醒来,因此,父亲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只是母亲嘴里的一个名词和家中的一个影子。
答应鲍敏求婚,母亲的唯一条件是要即将成为我姐夫的鲍敏必须把一字不识的大姐送到正规的学校里念书。我母亲一生最看重的事莫过于女儿们都能念书识字。于是,已经结过婚的17岁的大姐上了西皋小学,和10岁的二姐胡传芝同读一所学校。大姐从一年级开始读起,这时二姐却是三年级了。大姐在小学一年级只读了一学期,便跳级到了三年级,与二姐同读一班。大姐在三年级又只读了一学期,又跳到了五年级。大姐读小学的时间只有三个学期,但她将小学的所有课程都掌握了,而且各门成绩都始终名列前茅。大姐的优秀,又几乎成了西皋小学的一个传奇。
大姐和二姐都有一副好嗓子,西皋小学的文艺演出《十大姐采茶》,她们同台演出,大姐扮的是大姐,二姐扮的却是最小的十妹。二姐的个子不高,在我们姐妹六人中,只有我俩的个头在1米60上下,其余的全在1米65以上。大姐和二姐同台演出时,我已经出世,远铃也揣在大姐的肚子里了,母亲和村里其他的学生家长被邀去看演出。母亲在大姐扭腰翻身时看出了大姐的不方便。放学后,母亲将看到的情况说给了大姐,自此,大姐不再上学了。
小喜鹊,尾巴长
叽叽喳喳到宝庄
衔来一个绣花囊
宝庄大姐好梳妆
这么梳,那么梳
一下梳个燕子窝
燕子来生蛋
宝庄大姐真好看
大姐胡传荣虽然长得异常美貌,聪明绝顶,生下的女儿却是兔唇,大姐为此很伤心。但姐夫鲍敏却很高兴,为女儿起名远铃。解释说:远方的铃声总是很好听的——没想到他一语成谶,这个他心爱的女儿最后真的只能是他一缕远方的铃声了。自他作为右派被捕之后,与女儿时空相隔近40年,再见面时,一个是白发苍苍劳改释放分子,另一个则是已过中年几乎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