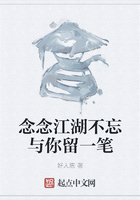其他人家,尤其那些经常不来往,很少去串门子的人家,他们搬走的时候,她也去了,也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往车上捆东西,最后她站在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看着他们走远。她的心里一直很平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诧过,至多,也就是心底微微泛上那么一点儿感伤,很快就会随风飘散。因为那些被主人扔下的院子,房屋,窑洞,对于她来说是陌生的,她就没觉出什么异样,走了就走了吧,扔下就扔下吧,人是需要奔好日子的,这黄土的院子,墙,房屋,窑洞,土地,都是带不走的。只能扔下。再说,也值不了几个钱。凡是值钱的,能变卖的,主人都会想方设法变卖了,或者带走。
马回元家一样,也带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卖掉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
她注意到,马回元女人很细心,老屋子墙上一幅克尔拜的图,早就被尘烟熏染得变黄了,褪色了,她还是仔细剥下来,卷成卷儿,塞进细软里带走。土墙上一个蜂窝里,扔着几双烂鞋子,这女人把帮子扯掉,把胶皮底子拿走了。就是一个柴禾棍儿也不能丢的。谁没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呢,不管走到哪儿,穷日子还是那个过法,还得掐着过,抠着过。不能因为说要去奔好日子了,就把这里的东西都给丢了。一样也不能丢的,也舍不得。
但是,有些东西却是必须留下的,因为根本就带不走。比如黄土筑成的土墙,土院子,土房子,老窑洞,还有锅台,锅台上那几个盆盆罐罐。
房子的顶,当然被揭掉了,瓦片砖头,椽子檩子,都是可以带走的。锅灶上的碗筷啊铁锅啊塑料的盆子罩儿啊,比较轻巧,都可以带走。
大多数人家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粗泥瓦罐。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么几个家什,置放在锅巷里,案板下,水缸的旮旯里,装的是一把陈年的谷米啊,粗盐疙瘩啊,腌制了好几年的韭菜啊,或者一点土蜂蜜。总之是不怎么值钱又耐放的东西,就搁置在了样式古旧,做工粗糙的瓦罐里,放在不起眼的地方。那些勤快的女人,在洗锅抹灶的时候,也许会抹抹这几个坛坛罐罐,要是遇上个好吃懒做的婆娘,这瓦罐简直就进了冷宫,孤零零被人遗忘在阴暗的角落,身上落满了岁月的积尘。
要不是这两年猛然兴起的大迁徙,大搬家,彻底的清理家产,说不定那些粗糙的泥家伙会一直那么呆头呆脑地待在阴暗里,没人注意,再过上个几十年几百年也不可知。
但是,世上的事是难以说清的。这几年山里的人纷纷搬迁,搬到距离黄河近一点的平川地方去了。果子梁在深山沟里,自然被搬迁的潮流携裹在其中。就像来了一场飓风,所过之处,大家纷纷跟着风向走,某几家人这样一做,其他的人跟着仿效起来。最后,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风向走了。
女人一家也在其中。其实,他们家甚至走在果子梁人们的前头。早在九年前,刚刚兴起搬迁的风,她男人就跟上响应,跑出去了。现在,他们在吊庄的那个家拾掇得有模有样了。房子是新盖的,一砖到顶,房顶是红灿灿的瓦,男人说过几年日子宽裕了,还想换成琉璃瓦,那才叫一灿明呢。
大家都是奔好日子去的。每一张被西北风吹得紫红的脸上,映出朴素的渴盼的笑。一面说舍不得老家啊,一面乐呵呵爬上卡车,在咣哩咣当的颠簸声中驶出果子梁,走远了。
马回元女人抱着最后清理出的一包东西,慌慌往车上扔,司机不耐烦了,催促快点走,赶天黑前得到达柏油路上,这样接着走夜路才安全些。
女人看见马回元家那头红牛被卡在一堆粮食袋子的缝隙间,牛直直站着,瞅着地面上蚂蚁虫子一样忙乱的人,大眼睛眨巴眨巴着,也不看任何人,眼里是冷漠的神色。仿佛这样的搬家与它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而它本该在地面上生活的,陡然被人弄在这么高的车上,还要经历一番剧烈的颠簸,被带到遥远的川道地方去,而这一切,在它看来还是漠然的,不值得深究。它就一直错动着阔大的嘴巴,投入地做着反刍。隔了几个间隙,又是两只羊。羊呆在车上一点也不老实,大声叫着,蹄子乱捣,幸好头顶上有绳子密密麻麻地揽着,它们不至于挣脱出来。马回元的小女儿嘟着嘴出来,眼睛红红的,怀里抱着一个红胶泥做的火炉,央求大人也给带上出门。
看看东西都装好了,捆绑妥当,司机开着车,突突走了,马回元一家就坐了辆蹦蹦车,去十里外搭乘班车。
临走,马回元女人挥着手说那些罐罐子坛坛子就留给你了,你拾掇了拿去!克里木母亲冲她笑笑,说我这就去拿。
那只泥火炉终究被扔下了,马回元女人一巴掌扇过去,女儿松开手,火炉啪地掉下,摔成了碎片。马回元的小女儿呜呜哭了,看着一堆碎片,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跺跺脚,跟上大人走了。
克里木母亲才把远送的目光收回来,缓缓进了马回元的家。
一只狗颓然地夹着一条脏乎乎的尾巴,也进了马回元的破家。
每次去送别,她都是这样,主人在,她不会着急进人家的家门,看着他们拾掇,起身走了,扔下空荡荡的院落,挖掉大门后,像掏去了眼仁的瞎眼眶那样的门洞。主人一走,家就成了废墟。立马就变成废墟了。她就在这废墟前站立一会儿。遥想过去几十年里,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家的悲欢离合的事情。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伤痛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