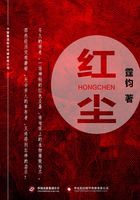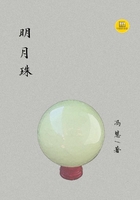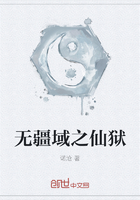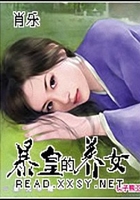夜,静极了,三里湾的青石路面闪着蓝幽幽的光。月牙儿弯在天边,在蓝光的衬映下,越发显得苍白,显得清冷。整整一条街似乎沉沉欲睡,只有街头老虎灶前的灯,还在闪着微弱的黄黄的光。
转过老虎灶,顺着三里湾的后街走到头,有一条清亮清亮的小河。像这小街无不受到教会的影响一佯,这条小河被叫作圣母河。穿过小桥,再拐个弯,便有两间低矮的干房。从圣母河边的石阶走上来,一条碎砖铺成的小路一直通到这平房的后门。
平房的年代看来也是久远了。它那与众不同的,用各种图案拼成的窗格子便是有力的证明。窗格里镶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更给这两问房子增添了不少宗教的色彩。此刻,这窗格子正半开着,晚风从这儿吹进去,吹拂着一个半躺在床上的已经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这老妇人脸色苍白,显然是长久不见阳光的缘故。皱纹堆在她的眼角上,似乎怎么抚也抚不平。
老妇人五官端正,慈眉善眼,使人一眼便可以想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十分美貌的少女。
她此刻半躺着,眼盯着墙上的那个铜质十字架出神。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得那铜十字架“哐当哐当”地响。
她叫陈秀芬,算起来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她出身于大家闺秀,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法国的一个教会学校。在朋友的帮助和介绍下,她带着一颗善良的心来到这个小城市,在三里湾尽头的教会学校里当了一名圣经教师。在这里,她研究圣经,讲解教义,像生命的航船到了终点,她的锚终于死死地抛在这里了。她结了婚。丈夫是入了法国籍的传教士。一九四九年,当她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陈奇的时候,丈夫坐在她的身边,对她说:
“我们去法国吧,这里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她看了看怀中的孩子,犹豫了又犹豫,终于摇摇头。
“那,孩子我带走!”丈夫说。
“不,”她紧紧地搂着儿子。“孩子不能没有母亲!”
“秀芬!”丈夫的眼里充满了企求。
这一刹那,她的心软了:“你也别走,留下来,我们一起,还有儿子,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丈夫叹了一口气:“可我入了法国籍,共产党怕不会容忍我这样的传教士。”
“那怕什么,共产党也讲宗教自由!”
丈夫苦笑笑,给了她最后一个吻。
这以后,陈秀芬便和儿子相依为命。岁月的长河给她磨难,给她坎坷,也给她幸福。共产党并不像她丈夫讲的那样,他们不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十分重视《圣经》的文学价值。教会学校改成教堂后,她到市九中当了名普通的语文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不幸因心脏病瘫痪在床,反而因祸得福,躲掉了那场空前的浩劫。那时候,方姑娘的母亲是她的挚友。教堂有时候不能去了,她们就会在家里做礼拜,对着轻盈的圣母河哼一曲低低的圣歌。
她瘫痪在床,儿子陈奇却并没有因为这而避掉上山下乡的命运。儿子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几乎都是灰暗的。他的父亲生了他,却给了他一个“狗崽子”的雅号。他是第一个去农村的。他用这种行动,换回了一枚闪亮的团徽。
一切像是梦,儿子走后,方姑娘的母亲常来照顾她。方姑娘的母亲死后,她流着泪用自己的方式为方姑娘的母亲做了一次宗教式的祭奠。再接着,便是方姑娘每天来了。儿子陈奇呢,也终于从农村回来了。回城的人太多,儿子一时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去运输队找了个拉板车的临时工干。自从她瘫痪后,仅仅靠学校的病保工资,儿子不工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儿子不在乎拉板车,他成天闷声不响,干完活回来后,便在写字台前读呀写的。她觉得,儿子经过上山下乡,突然有了思想,这不能不使她欣慰。
陈秀芬终于听见门响了。她立刻听出了这个脚步声是谁的:
“是方姑娘呀,快来,快进来!”陈秀芬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方姑娘走近床边,大眼睛红红的:“陈姨,你还没吃吧?我给你先做点吃的。”
“不忙,不忙。”陈秀芬把方姑娘拉到身边,爱抚地摸摸她的发辫:“怎么,又和你爹生气了?”
方姑娘摇摇头:“不,是爹的心里不好受。”
陈秀芬叹了一口气。
屋里静悄悄的。铜十字架在墙壁上“叮当”作响。好一会,方姑娘问:“陈奇哥还没回来么?”
“快了吧。”
“那,我先去开炉子吧。”
方姑娘走进陈奇的小屋。小屋的桌子上摊着各种书籍。她识字不多,但却能看出那些书和《圣经》、《福音》不一样。但有一本书她却认得,那是一本教会发的小册子《荒漠甘泉》。
“呀!”她在中心叫道:“陈奇哥竟也读这书啦。”
方姑娘捅炉子,烧开水,手脚麻利。等她下好面条,陈奇还没回来。
“陈姨,讲个故事吧。”
“讲什么呢?”陈秀芬的兴致很好。
“圣经故事!”方姑娘有点撒娇。
“好,就讲个犹太美人的故事吧。”陈秀芬调整了一下坐姿。
“砰!”门被撞开了,儿子陈奇穿着背心,握着板车的绊绳站在门口:
“妈,你们还讲!罪没受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