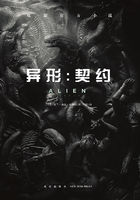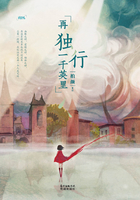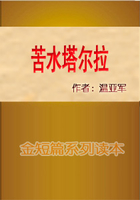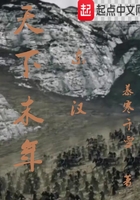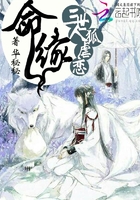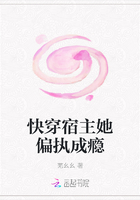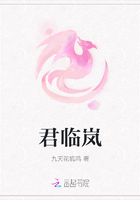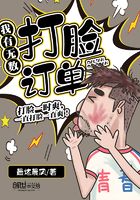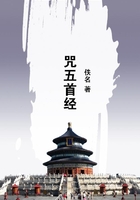来源:《天涯》2006年第03期
栏目:文学
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书上有一篇课文,叫《我的叔叔于勒》,写这篇文章的人叫“莫泊桑”,我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叫《项链》的小说。我怎么在这么多年以后,突然想起一篇课文了呢?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叔叔。莫泊桑的“叔叔”叫于勒,我的叔叔叫余乐。有意思吧?听起来差不多呢。于勒在游轮上做下等事,潦倒到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愿意上前相认。我的叔叔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虽然叫余乐,可是他的一生一点都不快乐。他不快乐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他娶了一个美女做老婆。——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不,绝对不是。听了我的这个故事后,请所有想娶美女做老婆的人,事先都掂量清楚了,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胃口,一个消受得起美女的好胃口。
那当然也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之所以将叔叔的不快乐归结于他的美女老婆身上,是因为我的叔叔余乐在结婚前是个特别快乐的人。那时候,他是一家国营机床厂手艺最好的八级工,跟机床有关的任何技术活儿,他干起来都是一把好手。他那时候还是快乐的单身汉,节假日就爱往我家跑。
一阵自行车的铃声响起之后,我大叫一声,飞奔到门口,打开门,只见余乐骑一辆半新的28寸大“永久”停在我家的门前。他朝我笑笑,粗声大气地说:小豆子,叔叔又到你家来蹭饭了。叔叔长得没有什么特色,跟大多数样貌普通的人一样,个子不高不矮,人不胖不瘦,眼睛不大不小,相貌不丑不帅。但不知为什么,他整个人给人一种非常聪明的印象,好像他的脑子里一天24小时都开着一扇天窗、拉着一根天线似的。他的眼睛清亮得像一碧如洗的蓝天,走起路来脚底下仿佛安了弹簧。他穿一套蓝色的帆布工作服,立领,袖口和裤脚都有金黄色的铜扣锁着,露出一双大脚丫,42码的白色回力鞋。
我迎上去,从叔叔的车龙头上卸下一只帆布包,那只包很大,很沉。我饿狼扑羊似的翻起来。果然,这个星期,叔叔又给我们买了一只卤鸭子,是“美香斋”的,那香味让我咽了一下口水。包里还有几只苹果,几只梨,一包山楂片。
母亲也迎出来。她扫了一眼我手上提的鼓鼓的帆布包,就生气地对余乐说:你又买东西来!你又乱花钱!下次你要是再买东西来,我就不开门了!一家人还客气什么?
余乐冲我伸伸舌头,还像个调皮的男生那样,在头上不好意思地挠了几下。
那时,在我的眼里,叔叔余乐就是个“最可爱的人”。他不仅有钱,而且出手阔绰。过春节的时候,母亲能给我五元钱的压岁钱。拜访其他长辈亲戚时,收到的都是二角、五角的红包,最惊喜的也不过是个一元钱的红包,而叔叔余乐给我的红包,打开来是张大团结。要知道,当时的十元钱可以是有些人家半个月的伙食费了。
我不清楚叔叔余乐为什么那么有钱。我父亲,也就是余乐的亲哥哥,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可是他活得完全没有余乐潇洒,他的口袋也比余乐羞涩不少。父亲在上海交大造船系读了五年,毕业后又被保送到北京某研究所学了两年的冶金——那时候,全民炼钢热,听说农民连吃饭的铁锅都砸了,真正的破釜沉舟,就是一心要炼出社会主义的钢铁大厦来。结果钢没炼出来,无数的铁锅倒成了无用的铁疙瘩,人,更是饿死了一大片。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于是,我的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自己一生的梦想——乘着自己设计的大轮船在大海上远航的浪漫美梦,改学与钢铁有关的专业,学成后被分配到某大型钢铁厂,成了一名技术人员。但知识再重要,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每次运动一来,我的父亲都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一顿批判。好在父亲书呆子一个,人又老实得像木头,所以倒没遇到太大的灾难,只是到农村下放过一段日子,后来又调回工厂,继续当他的“反动权威”了。
在我的印象里,虽然父亲和叔叔都在工厂上班,但他们的地位、境遇不可同日而语。父亲见人是低头哈腰、满脸陪笑的模样,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又戴一副深度眼镜,猥琐得像墙角边的苔藓。而叔叔余乐则沐浴着社会主义的新鲜阳光,开朗热情,自信十足,别说蚂蚁了,好像他要把全世界都踩在自己的脚底下。虽然他念到了高中毕业,但轮到他读书时,课本的扉页上都印着这样的一段又黑又大的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余乐的精力都用在了“学工;学农、学军”上去了,书是没有正经读过一本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招工进了工厂后,成了一名最出色的车工。只要车床一开,钢花就会像苹果皮那样地翻卷起来,铁屑就会像雪片那样地堆积起来,余乐的手就变成了一双魔术师的神奇的手。他做的活儿,干净利落,纹丝不差,技术很快就超过了带他的老师傅。学徒期没满,他就出了师,甚至也带上了一个小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