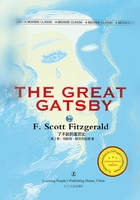来源:《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栏目:好看小说
“我大吃一惊,抓住了我妈妈的手问,她到底怎么样了?我妈妈说,她……她后来不知怎么的染上了毒瘾,吸毒过多死了……”
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是如何离开了“我”,直至死去?从小便冷漠的父亲,是如何让“我”体会到深沉的爱的呢?小说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我”的成长,“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一切痛苦与欢乐,读来让人怦然心动、唏嘘不已。
我选择了一个冬天回我的故乡小镇。回去的那天我穿着军装,在小镇上非常显眼。小镇上也就那么几百来人,他们纷纷向我投来了惊异的目光。我发现,出去五年后回来,小镇还是当初的那种懒洋洋的样子,可已有许多人不认识我了。我于是站在小镇的学校前点着了一支烟,感觉到小镇在我眼里慢慢小了下去。
我一边抽烟一边也把烟发给过路的人们,他们接了,眼里盈满了疑问。后来,终于还是五大伯喊了一声,这不是小四吗?人们才纷纷小四小四地叫了起来,每个人都叫得很亲热。我听出这是真的亲热,心头也渐渐地暖起来。特别是我看到满头白发的五大伯用粗大的手擦眼泪,便觉得自己的鼻子也酸了。他伸出手来,很想把我搂在怀里,就像很久以前我还是一个顽童那样。但当他的手刚触及到我的身上,就迅速地缩了回去。
我这样会弄脏了你呢。五大伯说,边说他的双手搓着,不知该往哪里放才好。其他的人只是看着,脸上挂着高兴的笑,对我的军装发出感慨。
我正迟疑着不知该怎样回答他们,便看到我父亲从村子的那头走过来了。他低着头,看样子好像是在想着什么,但只有我知道,我父亲走路时是根本不会想问题的。他一直这样,走路低着头,像个哲学家的样子,可实质上,我知道过去某个阶段的运动把他整怕了,除了过去他经常爱对我实行专政外,在外却一直是非常老实的。像小镇上许多农民一样,他们的一生,都好像是在胆小怕事中小心翼翼地过的,脑子里根本就不爱想那些高深的学问。记得小时候,我总喜欢看着天空想什么,我父亲的耳光就上来了。他说,爱对着天空想什么的人,都是一些阴谋家。阴谋两个字,其实我父亲并不太理解它的意思,他不过只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上听来的而已。不过这话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已属非常难得。
我便站在那里亲切叫了他一声:爸。
我父亲的头抬也没抬。也许他根本没有听到。
五大伯说,你听到没有?你娃儿在喊你呢!
我父亲这才抬起头来,发现五大伯是在唤他。他看到了我后便张大了眼睛。我又叫了他一声爸。他还是没有吱声,只是一个劲地看着我。我这才想起过去我因为恨他而从来没有开口叫过他一声爸了,难怪他像没有听到一样。于是,我酸着鼻子说,爹,我回来了。
我父亲的眼里迅速挤满了泪水。他说,啊……娃儿……是你可回来了?
接着,我父亲热烈地拥抱了我。我之所以说他“热烈”,是因为多少年来,这是他第一回正儿八经地拥抱我,所以我开头还不太习惯。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还想:父亲其实是爱我的,不然他不会如此失态。这一想我的眼睛便湿润了。我的脑里突然想起了当兵走时的情景。那情景曾是我在新兵连一直想不通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日后努力拼搏想考上军校的原因之一。我当兵走的那天我父亲只是站在人群之外,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看着我妈妈一个劲地流泪。他抽着烟,坐在小镇的一间房前,看着送我的人群慢慢走远,看着载着我的车渐渐消失,激越的锣鼓声乱轰轰地消失在小镇那懒洋洋的空中……
于是我对着父亲的耳朵说,爹,我考上军校了。
我感觉到他拥抱我的双手颤抖起来,他哆嗦着问,你……考上了?我说,考上了。我原想我这样说,我父亲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但是他没有。他听后先是推开我,接着忽然蹲在地上,嗡嗡嗡地哭起来了。
看把他高兴的……五大伯说。五大伯一边说一边也擦泪了。
男人们一哭,我的心头便乱了起来。我没有想到自己在外面闯了多年心头还会有乱的时候。透过父亲的身躯,我看到故乡的冬日一片萧条,看到故乡的婆姨们仍然穿着臃肿的衣服,一扭一扭艰难地走在雨雪地上,我看到镇上的青砖黑瓦和墙头上的枯草,还是像我当初走时那样寥落……我的鼻子一酸,眼里痒痒的想流泪。于是我一手拉了父亲,向家中走去。
到家后,我妈妈高兴的样子自然是没得说了。她巴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全装在我的肚子里,好像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外面忍饥挨饿。
我问我妈妈,夏敏现在怎么样了?
我妈妈只是说,吃吧,吃吧。
我再问,我妈妈还是说,吃吧吃吧。
她始终没有提起夏敏的事,好像我根本没这样问她似的。看到妈妈不说,我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下去了。这样热热闹闹地过了好几天,那些天里,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去拜访一些熟人和同学。我妈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否则,人们会对我有看法。与其说是怕人们对我有看法,倒不如说是我不想再惹我妈妈生气。在外那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欠她的太多太多了。我明白我妈妈让我去看望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从前我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让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而现在,在我妈妈的眼里,我身上的那身军装好像说明是衣锦还乡了。她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洗刷一下她过去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