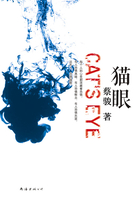山路不平,我们挤在车斗上,几次差点被颠簸下来。我们的手死死地抓住车斗,紧张得周身是汗。手扶拖拉机像一头不堪重负的老牛,哞叫、挣扎,好几次差点憋熄了火。但那喷出的滚滚浓烟,就像垂死之人终于吐出了堵在喉管的浓痰,呼吸陡然顺畅,人一下子又活了过来。
拖拉机终于出了山,把我们带到镇上。我们拦车到县城,在县城转车到新洲。下了车,再坐车到一个小镇,然后下车步行。肩上的铺盖越来越沉,广盛说,再坚持一会儿,很快就到了。我们总算在夕阳落山前,到达了武湖湖畔,在一家私人农场停下来。
我们是来湖里插秧的。透过老板家房后那一排排槐树,我看到了湖。湖真美,天水一色。我想起天才少年王勃的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现在虽不是秋天,但其旷美,是如此相似。遗憾的是,霞光照耀湖水时,也照耀着一大堆牛粪。广盛站在牛粪边,同老板讨价还价。我们站在霞光里,看广盛同老板讨价还价。
老板五短身材,摸了一下留着短须的下巴,神态傲慢,说,二十元一亩,再不能多了。广盛说,去年还二十二块呢。老板说,今年啥都涨价了。广盛说,啥都涨价了,我们的工钱也要涨嘛。老板说,化肥涨价了,种子涨价了,你们的工钱再涨,傻子才种田!
我心里一凉,远眺武湖,王勃诗中的美景,与孤鹜一起飞得无影无踪。
广盛望一眼我们,我们不吱声,他便显得很无奈,冲老板说,工钱不给涨,田的面积不能算计我们。你们这儿的面积太野,说是一亩田,实际一亩二还多。老板说,没有的事。老板说这话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他说,上这儿找活干的,像湖里的水,一波又一波,干就痛快点,不干你们走人。我远眺,一边是无垠湖水,一边是茫茫水田,视力所及,不见人烟,哪里有去处。打道回府,更是不可能。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每人花了三十多块钱的路费,我们又不是旅游来了。
广盛望一眼我们,我们还是不吱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是饿的。我们清晨出来时,各自在家吃了点面条面片汤之类的东西,之后,整天粒米未进。
广盛冲我们说,“干吧?不干谁给饭吃?”那语气听似征求我们的意见,其实就是决定。我们就把脚旁的蛇皮袋提起来,跟着广盛走。广盛跟着老板走。
我们沿着湖畔,走过一段黄泥小路,来到一排房子前。那房子简陋,更像是牛棚,我们在门口就闻到沤过的牛粪气味。见我们不断吸着鼻子,老板说,没有牛,牛都在茅草棚里,秋天凉了才牵进来。果然是牛棚,不过已经打扫过,里面用木板搭了一些床。我们就坐在木板床上,等着老板喊我们吃饭。没吃饭,一点劲都没有,懒得动弹。
天暗下来时,老板让人给我们挑来两桶面条,搁在牛棚门口。不远处是污泥和牛粪。面条清汤寡水。我们就在掺杂污泥和牛粪气味的空气里,将面条造了个桶底朝天。我们都没吃饱,老板不吱声,惊讶地看着两只空桶。他不知道,我们在家都是能造五六碗面条的劳动力。我望着老板阴沉沉的脸,故意打着嗝,装作吃饱了。第一餐,将就点,可别因为我们太能吃,吓着他,赶跑了我们挣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