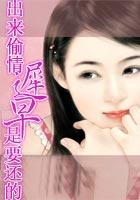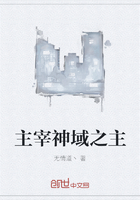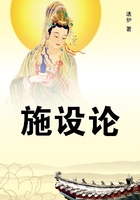来源:《小说林》2009年第01期
栏目:中篇小说
我和王老师的认识纯属偶然。当然,这么说也可以理解成是我和王老师的认识是必然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偶然,那我们就不会认识。有时候我们喜欢说什么事都是偶然,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相信它们是必然的罢了。因为如果真的世间的一切都已在必然性之中,那我们的生活将必然减少很多乐趣,所以,我不仅习惯于把生活中遇到的灾难看成是偶然的,即使是幸运也看成是偶然的。
总之,一切都是偶然。
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说,我和王老师的认识确实是出于偶然,而非出于我个人的这种信念。我相信,等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之后,你一定也会同意我的说法。我想,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应该是星期一,不可能有错,就是星期一。那天我实在是无聊之至,甚至无聊之至这个词都不能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总之,情绪不佳。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是我来美国四个多月后第一次去学校的东亚图书馆。
因为天气很好,星期六,我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拉霍亚小镇去了一趟。说天气好,好像这里的天气平时不好似的,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地处南加州,这里的天气每天都很好,如果仅仅说是蓝天白云还比较抽象,它已经好到了让人厌倦的程度,因为每天都是阳光灿烂,而且,已经足足有三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雨,甚至,连阴天都没有一个。这对来之于多雨的江南的我来说,显然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
还好,有天深夜终于下了一场雨,我不仅听见了窗外唰唰唰的响声,还闻到了那种雨滴砸到地上后所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息,因为担心是假的,所以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不过,尽管这样,这场雨还是我在梦中梦到的一场雨。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阳光就已经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射了进来,但幸好有了这场梦中的雨,我的情绪才舒缓了许多。
毕竟,梦中的雨也是雨。
但是,我的这种痛苦并不被人理解。有一次,我的一个住在洛杉矶的搞生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已经适应了加州时,我忍不住向他倾诉了一下我的苦闷,我对他说,我现在非常希望能下一场雨,因为圣地亚哥的天气实在好得太糟糕了,始终阳光灿烂,让人精神很紧张,如果有可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雨中,在上海那种潮湿阴暗的街头走一走。虽然他也是上海来的,但他听了我的牢骚居然在电话里笑出了声来。他告诉我,他在美国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国内来的抱怨加州的天气不好的。他问,是不是像我这种搞文学的人心里都比较阴暗,见不得阳光,或者说,只有心里阴暗躲在角落里才能写出东西来?
拉霍亚小镇靠着大海,风景很好,号称是艺术家小镇,有不少画廊。周六那天,为了消磨时间,我几乎把镇上的每一个画廊都逛了一遍。在一个画廊,我看到了有几幅中国画家画的油画,标价之高,让人几乎以为他们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我不由得在这些画前停留了一小会儿,想看出这些胡涂乱抹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值那么多钱,最后,我想,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些画家骗了这些画廊的老板,二是这些画廊的老板想骗来这里买画的人。而且,以我的感觉,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这么多画廊,一路看过来,就数这几幅中国画家画的最糟糕。
也许是我在这些画前待的时间太长,一直站在一边的画廊的工作人员向我打了个招呼走了过来,他个子又高又瘦,戴副金属边的眼镜,穿着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灰色的领带,显得文质彬彬。为了不让他误解我的意图,我立即告诉他我只是看看,我对他说,我是中国人。言下之意,我当然不会跑到这里来买这几幅中国油画了。他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说他明白,因为这些画太贵了。
我忍不住也笑了。“你去过中国?”
“是,我去过上海,北京。”他对我说。
“我就是从上海来的。”我说。
“是吗?”
“我很喜欢上海,上海很像纽约。”或许是怕我不理解,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是纽约人。”
“哦,那你怎么在这里工作?”我想想,从纽约到圣地亚哥之间的距离之远犹如从乌鲁木齐到深圳。当然,纽约不是乌鲁木齐,深圳也不是圣地亚哥。
“我一个月前才来这里,你知道,大家都说,这里有阳光,沙滩,天气好,还有美女,是的,美女,实际上,你知道,说加州女孩漂亮不过是说她们穿得很少而已,可是,不管怎样,这里除了这些有什么呢?”
他问,然后不等我回答,他就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你知道,在纽约有《纽约客》,可这里只有《读者》。”
尽管他说这些话时并不是为了幽默,而是愁眉苦脸,可我还是一下子笑出声来,《纽约客》(NEWYORKER)和(READER)《读者》的英文最后一个音节刚好是押韵的,《读者》是这里的一本免费赠送的杂志,尽管和纽约客一样,每周出一期,而且,开本比纽约客还大,页码也比《纽约客》厚的多,但上面基本上是各种商品的广告和折价券,只是在广告的缝隙里才有一些新闻,和几篇由本地的土著人士写的小文章。
“是,这里什么都有,阳光,沙滩,美女,可是,就是没有文化。”我不无同感地说,显然,这个小伙子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他摇了一下头,再次耸耸肩。“所以,我希望有一天能回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