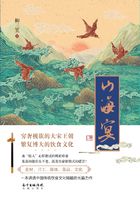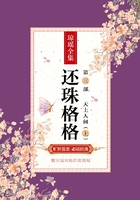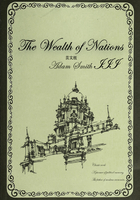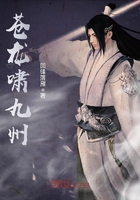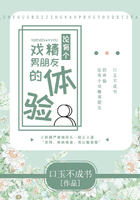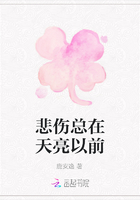可能是太孤独了,他把我当成了知音,特地把我带到库房里,让我看他觉得还有点意思的画。我比较喜欢一个俄罗斯画家的画,画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失去了重力,感觉就像是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样,漂浮在莫斯科红场的那个洋葱头教堂的尖顶上空。
“像梦一样,”我说,“很不真实。”
“对,”听到我的话后,他手扶画框,又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点头表示理解。看得出,遇到我这个知音,他非常感动,当我向他告辞时,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并且,让我留下我的EMAIL地址,说希望以后和我保持联系。我当然也欣然同意。后来,果然,我回去后没过几天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以为他有什么私房话对我说,不料却是那天我看到的那几幅中国画家的油画的照片和价钱,并热情欢迎我去选购。
看来,他说得对,他确实生活在梦中。
星期天,我睡了个懒觉,起来后吃了点东西,然后像平时一样,到附近的一个书店里去看最新一期的《纽约客》。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看这本似乎很有品位和文化的杂志,而只是因为在书店里能看到不少人,可以多多少少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孤独。
所以,当我星期一第一次踏进学校图书馆四楼的东亚图书馆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不仅有很多我熟悉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很多国内的杂志,再而且,在杂志阅览区,我发现,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亚裔的中年男人,坐在宽大的桌子旁,正一手拿着自己的近视眼镜,低头专心致志的翻阅一本杂志。
但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甚至不会讲一句中文的美国人,杂志阅览区摆放的杂志和书籍一样,同样有好几种文字的,除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文杂志外,还有日文的和韩文的。所以,我很想看看他手里拿的究竟是哪种文字的杂志。这样我就可以大约判断一下他的国籍。我把我的背包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然后慢慢走到他身边的摆放报刊的书架旁,拿起一本杂志假装翻阅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回头扫了一眼他正在埋头看的那份杂志。因为他的头几乎是贴在杂志上的,所以,我无法看清楚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但杂志是中文的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看样子,我估计他很可能是学校的老师,因为他就像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授一样,穿得很正式,他身材胖胖的,上身穿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西裤和棕色的皮鞋,头发梳的也很整齐。不像那些年青教师一样,穿着比学生还随便。我认识的一个文学系的年轻男老师,每次来学校上课,打扮的都比学生还像学生,他不仅像学生一样,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大短裤和一件破旧的圆领衫,而且还总是穿着人字拖鞋,拿着滑板车走进教室。
这几个月来,我实在是太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我在拉霍亚小镇的画廊里碰到的那个可怜的纽约小伙子,实在是太孤独了。而且,他比我好的是,他好歹还是个美国人。
可我却一下子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向他打个招呼。阅览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显得十分安静,在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台供检索的电脑的显示器正在闪烁,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按树,上面的细碎的树叶正在阳光下抖动,我想,外面也许正在刮风。
这时,我听到我的身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和书页合上的声音,这个人似乎要准备离去,我终于不再犹豫,赶紧转过身来,果然,他已经戴上眼镜,正拿着那本杂志从桌子旁站起来,我忙用英语对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直接问他是不是中国人。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他对我的唐突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点点头说是的。
我立即改用中文,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上海交大的,在这里的文学系做访问学者。
“哦,刚才我看到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南大的呢。”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笑着对我说。
我马上反应了过来,这可能是因为他看见我身上穿的那件印有南大字样的圆领衫的缘故。
“我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交大工作。”我解释了一下。
“那我们是校友啊,不,应该说,我们还是系友,我也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笑着说,转身准备把那本杂志放到书架上。我看了一眼,是一本很专业的学术杂志《中国语言学研究》。
“是吗?那你应该比我高多了,你们那届同学里有人留校吗?”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南大中文系的系友,我的确很高兴。
“有,我们因为是比较早的研究生,所以留校的人也比较多。”接着,他说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搞语言学的,现在都已经是博导了。
“你是学语言学的?”我又看了一眼他拿在手上的那本杂志。
“对,以前读大学时,曾经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很喜欢,所以后来可以考研究生了,就考了语言学专业的。”
“你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他可是语言学大师啊,”我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好像最早就是他介绍过来的。”
“是啊,是啊,当时他就是给我们讲索绪尔的语言学,还用象棋给我们举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
“是不是说马走日,像飞田,车走直线,炮打翻山,这套规则是语言,而具体每一步棋是言语?”我打断他问。
“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