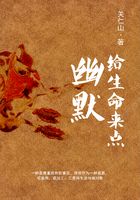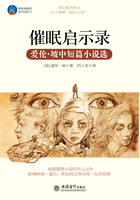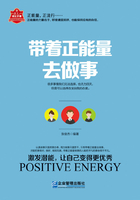何太婆是余福里的居委会老主任,按官本位的行政编制排序,该是我们余福里第一号人物。
何太婆是正称。
何太婆的别称是“何书记”。
何太婆一直没有正式参加过工作,从年轻时就干居委会,是四十年一贯制的老主任了。那年有部电影流行了一段时间,中年以上的人恐怕都还会记得其中这样一句台词:“何书记——吃汤元哟——”那时候时兴抓阶级斗争,街政府组织全体居委会干部看这部电影。电影散场时不知谁起的头,朝年轻的何太婆喊起了“何书记”,何太婆本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愣怔一下,也就哈哈地应了,于是“何书记”的别称一下子就喊开了。以后,无论是街道干部或其他居委会的主任开玩笑地喊,还是余福里哪位居民因为什么不称心的事而别有讥刺之意地喊,何太婆全都一笑受之。
何太婆的居委会工作抓得很好。那时候的人对上级布置的大事小事都十分认真,不像现在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瞎糊弄。比如防火,家家户户的炉台旁都是要摆放一溜砂袋的。检查砂袋数量和质量时,何太婆是一家一户全部走到,不仅亲自过目亲自点数,而且随手提着一个装了砂子的小桶,另一只手拎着把大铁勺,谁家砂袋份量不足,她一定要批评两句,再给添上一勺半勺。就冲这个认真劲儿,我们余福里四十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火情。再比如逢年过节防火防盗的值班,何太婆总是让其他干部值白天或者上半夜的班,她自己戴着个大袖章亲自值下半夜的班,无论是雨是雪,隔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她就要出来转一下,披着老伴老蓝布的劳保棉大衣,拿着一支三节电池的长电筒,这里照照,那里照照,从余福里巷子头一直照到巷子尾。碰巧有小两口为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半夜里闹别扭时,何太婆一定要进去劝和,一定要把枕头给他们摆到一头才出来。咱们国家大,这儿那儿的时时有些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淹了。支援灾区人民时,余福里捐的钱、粮票和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衣服总是全街第一。何太婆会弄来几辆三轮车,敲锣打鼓地把东西送到街党委去。至于平常的卫生工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何太婆本身就是一个干净利索人——有什么样的一把手,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单位。综上所述可知,余福里年年都是优秀居委会,何太婆年年都是先进模范。
然而这几年不行了。
这几年居委会的工作也讲起了经济效益,而且像咱们国家所有的单位一样把经济效益的考核放在了第一位。不管政治学习水平多高,不管治安情况多么良好,不管墙上地下多么整洁干净,抓不住“经济效益”这只大老鼠便全都不管用,便一切都是零。新的街道领导对何太婆很关心,有一次开罢一个大会后特意把何太婆留下来谈了一次话。领导沿用大家的叫法笑着说:“何书记,您老人家要抓一抓第三产业哇!”
余福里本来是条南通北畅的巷子,可房产公司一开发,一座洋洋气气的证券交易大厦把巷子尾切去了一大块,余福里成了条死巷子,这第三产业又怎么抓呢?何太婆愁眉不展。这年年终,余福里居委会四十年来第一次从先进单位的名单里消失了。街道居民科的干部都觉得这对何太婆太不公平,一致要求至少要给何太婆本人保留住先进个人称号,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定了。但征求意见时何太婆却坚决不同意,何太婆说:“我的居委会给评了下去,我还好意思要这个先进?”
表彰大会还得参加,不过何太婆坐在后边了,一生要强的何太婆默默无言地垂着眼睛,直想在那光堂堂的水泥地上找条缝钻下去。
何太婆终于“退居二线”。
“退居二线”的何太婆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屋里,无语地望着门口的世界,偶尔有老邻居进来闲坐,何太婆便会念念叨叨:“如今这是么样搞呢?如今这是么样搞呢?”
儿子媳妇见老娘失落感太重,就劝她学气功,何太婆只是摇头。
又过了半年,何太婆终于大彻大悟了。觉悟了的何太婆在证券交易大厦门前摆上一个小煤炉,支起一个小铁锅,卖起了茶叶蛋。股市走牛的时候何太婆的生意便十分红火,老熟人碰到何太婆便打趣道:“何书记——您家的汤元好大哟!”
何太婆这时便会满面红光地哈哈一笑。
不明内情的人则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