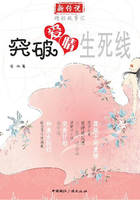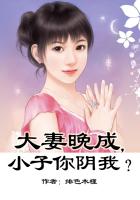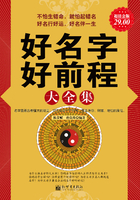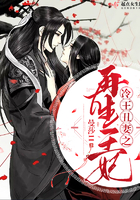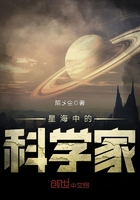杨奶奶是“文革”开始那年搬进余福里的。那一年杨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那面相顶多也就五十出头。杨奶奶被人剪了个阴阳头,胸前挂着块大牌子,上边歪歪斜斜写着墨黑墨黑的几个大字——“资本家的臭小老婆”。杨奶奶被一些戴红袖章的娃娃推拥着,在一个也戴着红袖章的、各个部位都干干瘪瘪的中年女人的指挥下,杨奶奶低头喊着“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和打倒自己的口号,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进了我们余福里。
杨奶奶的老头子是一家小酱园的老板,那酱园一解放就被公私合营了,老板也就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家人。按规定可以拿点定息,但那老头子和杨奶奶都表示不要了,说国家给的工资够用了。没想到后来这便成了他们的十大罪状之一,罪名是“居心叵测”。该拿的钱你不要,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呢?不用说,肯定是想要我们红色万年的整个社会主义江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七十多岁的杨老板很快就“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不久,杨奶奶也被扫地出门到了我们这平民小巷余福里。
杨奶奶默默无言地在余福里出出进进,如同一个哑巴、一个聋子、一个瞎子。
余福里人可怜杨奶奶孤苦伶仃,日常生活上都不约而同尽力相助,你帮买个煤,他帮拿个菜,全然不把她当反革命。那个干瘪女人知道了这些情况便很生气,跑到余福里叫何太婆提高对杨奶奶的革命警惕性,不要丧失阶级立场。何太婆那时候是余福里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这位小组长不以为然地说:“六十多岁的人了,再反革命还能反到哪里去?”何太婆出身好,又受余福里人尊重,那个干瘪女人最后悻悻地走了。
终于到了那一天,来了两个微胖的干部,说是落实政策,请杨奶奶搬回自己的那幢两层小楼,并告诉她那个干瘪女人已经搬走了。
杨奶奶盯着两个干部看了一会儿,轻轻说她哪里都不去了,就住余福里。
后来又来了两个更胖点儿的干部,劝杨奶奶“朝前看”,还是搬回去吧!
杨奶奶不再说什么,只摇摇头。
以后余福里人发现杨奶奶慢慢开朗起来了,常常也主动和邻居搭个话了。
再后来人们发现杨奶奶往家里买了好多好多小的和不大不小的坛坛罐罐,有年轻人便问杨奶奶你买这么多坛坛罐罐干什么呀?杨奶奶笑而不答。
人们又发现杨奶奶常常午睡起来以后去菜市场,买回好多很便宜的处理菜,有不会说话的年轻人便直楞楞地说:“杨奶奶,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吃点儿好的?又没儿没女,给谁节约呢?”杨奶奶并不生气,依然笑而不答。
到了夏天,杨奶奶的坛坛罐罐打开,哇——满余福里人顿时都流出了口水。那个夏天的傍晚,余福里每户人家的饭桌上都多了一只色香味俱佳的酸菜碟子,上边是生姜、辣椒、洋葱头、扁豆、蒜苔、萝卜条、小黄瓜头、大白菜帮……那些毫不起眼的家常小菜,竟被杨奶奶泡制得如此精致精美,让余福里人一扫闷热烦燥,食欲大开。从此,杨奶奶的腌酸菜成了余福里人夏日餐桌上的“保留节目”。
开放搞活以后,有人劝杨奶奶摆个酸菜摊,生意一定红火。杨奶奶看那人一眼,笑笑地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杨奶奶照样午睡后去菜场,照样每开坛腌酸菜就叫几个孩子挨家挨户送过去品尝,直到那小坛子见了底空空地拿回来。
杨奶奶活到八十四岁,无疾而终。
杨奶奶去世的前两个月曾把一个小布包托何太婆保管,何太婆一层层打开那布包,才知道包着的是几百块钱。何太婆叹道:“这杨奶奶,真是……”
余福里人圆圆满满送走了杨奶奶。火化那天,余福里人家家户户都去了至少一个代表,殡仪馆的人都莫名其妙这老太婆到底是什么人物?花圈只有一个,可为她送行的人却那么多?便问操办这事的老高头。老高头说:“什么人?苦善人。”
杨奶奶留下的坛坛罐罐,由何太婆作主,让一家拿一个回去作纪念。拿了坛坛罐罐的人家便也学着杨奶奶做腌酸菜,但开坛时没有一家是成功的。大家都问何太婆这是怎么回事?何太婆长叹一声道:“只怕这些泥捏火烧的坛儿罐儿也是有魂灵的,早跟着杨奶奶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