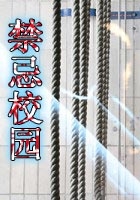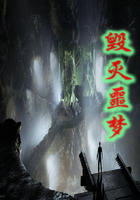来源:《清明》2017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门楣上方的牌子上写着“周乐无极限”,乍看以为是个娱乐场所。从一面后墙上开出来的一扇门,以前是小镇税务所的一排办公室,税务所和法庭联合盖了一幢办公楼,就把屁股临街的平房全给租了出去。四家租户全开了商店,周乐最初也卖百货,但周乐有天在杂货中间创意性地摆上了药品。
周乐是医院看门人周爷的儿子,周乐上过两年卫校,什么病都敢给人看,不过,至今倒也没出过什么乱子,一旦有什么不妙,医院就在药店正对面,跨上几大步就穿越过去了。你也知道,如今到医院看病一定要把你浑身的器官给查个遍,小街上的人宁愿先到周乐这来碰碰运气,治着试,试着治,不好了再上医院。来买包盐的,“呀”一下想起还要买几片头疼药,周乐这时会说,把这几样配上一起吃效果好。主要是,周乐卖的什么都便宜。
门里,饮料和啤酒箱子堆得高高的,两排柜台,左边是百货,右边是药品,周乐大大方方地出售,有人偶尔来查,周乐往药盒子上放一层膨化食品,花花绿绿,盖个严实。人们没事都爱往药店跑。药店的音乐跟放亮的天光会同时叫醒小街上的人,周乐往房顶上放了两只音箱,再僻静的巷子里也能听得到那震荡的音乐,杨沉舟走到那一截,总要进来说两句:
“周总啊,音量放小点,樱花村张老实那头怀孕的驴都给你震流产了。”
在一家小药店里弄出一个舞场来,你肯定没听说过吧。晚上,周乐把柜台挪靠到墙跟前,箱子、椅子搬到门外去。房顶上的电子音乐震荡起来时,小街上的人就都来看热闹了。
小棉下了晚自习,老远看见药店门前那片灯火,感觉沉闷的生活猛地出现了一线生机。一伙年轻人陶醉地跳着,舞场里只容得下三四对舞伴,在玻璃柜台和货物之间兴高采烈地贴来晃去。小棉一走进去,周乐一下就把她裹挟到音乐中了,周乐是为了小棉才想的这个主意。我母亲和荷姨有时也会进去跳几曲,小街上可供娱乐的场所几乎再没有了。
有小棉在药店里转的那一圈又一圈,周乐整天都很快乐。
“小棉,给老子回家!”
听到这个尖细的嗓门儿,周乐猛一下拔了音响的电源,舞会便散了。
周乐走到门口去,靠在门框上,看小棉快速消失在巷子口。半弯儿月亮,悬在幽蓝的夜空。
小棉母女走起路来,天生的杨柳摆,母亲比女儿的姿势更撩人。荷姨的脸在夏天时像淡淡的红糖色,冬季里又会变得温和,像牛奶慢慢浸入了她的皮肤。我母亲说起一个人巨大的变化来,就拿荷姨比画:
“真是判若两人,小棉她妈,是这两年才有点女人样的。”
一旦跟我父亲谈论起荷姨,我母亲会换一种口吻:“一只山鸡完全是可以变成凤凰的。”
我母亲很快就没有时机刻薄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就调到城里去了。照我母亲暗示给我的意思,我父亲是个鬼影,是不能把他存在记忆里的。
荷姨坐在门槛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我把我母亲的话学给她。荷姨说,我母亲剥夺了我父亲作为一个男人的权力。
我母亲站在宿舍门前的台阶上洗手,大声地回敬道,一个女人太硬气了只能自己受苦。我母亲习惯用肥皂,一盆肥皂水哗啦啦飞溅,我将一瓢温水缓缓地浇到那双常年被肥皂腐蚀的手指上,我母亲才算洗干净了一双手。
两个女人从不面对面交谈,她们会对着我和小棉发表对彼此的不满,有时,也站在周乐的店里互不相干似地说对方,非常不屑的样子。人们很早就把周乐的杂货店叫药店,后来周乐真开了家正规的药店。
“有工作闲,还不是跟老子一样,自己靠自己。谁让你有一副牛脾气。”荷姨后来变得特别爱说话,就像喝水一样,成了她生命的必需。我母亲听到荷姨称自己“老子”,一愣之后什么也不再说了。
我母亲是在县城里生的我,我父亲是双子镇中学的校长,没工夫管我。他们的朋友给我母亲介绍了秋菊,她只有十三岁,秋菊每天把我抱到太阳下,由着我在楼下的空地上爬来滚去。我母亲有轻微的洁癖,每天都要亲自为我换四遍衣裳,一边换一边还有空在电话里诅咒双子镇上一个人享清闲的我爸,我爸说,你就忍一忍吧,条件就这样。我母亲故意让我大声地哭。那你到镇上来吧。我父亲那时正在镇中学里干劲十足,连续三年高考成绩居全县第二。秋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给我讲很多故事,而每当秋菊拿起一本书神情激昂地念起来时,我总能表现出像是能听懂她故事的样子,就为这个,我母亲容忍秋菊直到她也调到了双子镇上。那时,我已经四岁了。
荷姨来医院看病,我母亲跟她对视两眼,当即决定把我交给这个女人照管。
我母亲认为自己能从一个人的眼睛里看清她内在的一切,她认为荷姨不是个简单的农妇,但我母亲给我父亲说的是:
“这个女人看着干净利索。”
小棉带着我在周乐的药店里玩耍,有人看着我说:
“茉莉呵,你母亲是个聪明的女人。”
我五岁半上了一年级。我父亲又调到城里去了。我母亲再想往城里调,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双子镇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我和已上高中的小棉每天一起去上学。学校举办了一场联欢会。我父亲喜欢拉小提琴,学校的文艺活动一直很多,但这将是最后一场,不久的将来,学校的文艺团体基本上就全解散了。这场联欢会欢送我父亲,同时迎接方校长的到来。
我父亲把布置会议室的任务交给了小棉,小棉从花园子里采了鲜花,大清早就带到学校。我偷拿了我母亲的三只花瓶。她晓得了会把荷姨骂个半死。
联欢会上,我父亲拉了几首帕格尼尼的曲子,小棉和方校长带头起劲鼓掌。荷姨也来了,我父亲给她安排了前排中间的位置。方校长本来坐在第一排的,不知怎么的,后来他和荷姨坐一块儿了。
我父亲拉小提琴时,像一头孤独忧伤的狮子。我母亲爱打扮,她认为小提琴发出的声音太让人悲伤了,人活着,不应该太悲伤。倒是荷姨听得像是魂飞魄散,连方校长问话都没听见,方校长不得不碰了下她的衣裳,引得所有人都看他们。
“你喜欢古典乐?”
“小时候学过一点,多少年没碰过了。”荷姨说这个时,两眼茫空。“小时候”荷姨重复了几遍。
我父亲的小提琴曾经吸引着荷姨,她有几次走到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去。
几排平房围在一个巨大的花坛四周,到了花开时节,整个校园里流窜着一股猛烈的气息。荷姨在这气息里走得悄然恍惚。整条街都在午睡。荷姨出了巷子,低头走在寂空的小街。荷姨穿了件月白色的裙子,式样老旧,但这件裙子让荷姨走得风生水起,仿佛是从古老的时光里来,往不曾被打断过的时光里延续而去。烈日晒得整个世界都变空旷了,花坛里杂树繁花,从围栏里探伸而出,荷姨从花坛右边的小径拐过去,一排大房子挡住了她,她走进最中间那道门里。
“来了。”我父亲轻声说,他一直站在门后往花坛里望着。他戴着一个圆框眼镜,白衬衫的领子直立着,两只袖子卷得高高的,他的眼神却如孩童,在看见荷姨的瞬间,有刹那的迷茫。
两个手足无措的成年人,在一个个花开的午后,像做着梦一样,发现了他们从不曾知晓的隐藏得很深的另一个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遇见,他们的某部分自我将永远沉睡。
荷姨感觉身体里有泉,我父亲的眼神让它涌流。我父亲拿出他名贵的琴来,递到荷姨的手里:
“只要你曾经喜欢过,就一定会找到那种感觉。”
荷姨有种小姑娘的冲动,当她第四次拿起那把小提琴的时候,阳光铺满了花坛,整个世界都很静,他们从彼此的眼睛里艰难地辨认着。我父亲的手按在荷姨的肩膀上,没法把目光从荷姨脸上给撕扯下来。
一阵熟悉的香水味,隔开了空气里弥漫的那阵花的香气。我母亲走进那道门里去,长裙拖过门槛,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我母亲看了两眼那把琴,转身走了出去。空气里猛烈的气息让我母亲眩晕。
“这要命的夏天啊。”我母亲叹了口气。
那段日子,她们在我和小棉跟前再不说一个字的彼此。
我父亲要调走时,我母亲打发我去叫荷姨:“就说我请她来。”她们合作做了一桌菜,那天来了很多人,我们的晚餐桌上,一直有客人进出,他们一来,我就溜出去找小棉。
餐桌上挤不下我和小棉,我们把吃的装在一只袋子里,拎到院子里的那截城墙上去吃。
好多事似乎是在那天的晚餐桌上发生变化的。我母亲追着人家方校长碰了许多杯酒。
我父亲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走时,我母亲还醉生梦死在床上,后来我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彻底住到了小棉家。我母亲醉了一个礼拜,如果我记得没错,那是她头一次醉酒。
方校长一来便大兴土木扩建学校,方校长爱踢球,学校的操场还是个土操场,方校长看中了操场旁边的几块地。
荷姨那天正在麦地里锄草,方校长的影子忽然罩住了她。她没回头,继续锄草。
“你这个女人,不晓得生活里不止有种地这件事吗?”
“人总得靠什么活着。”
“别种地了,再种,你就老了,还没来得及享受呢。”
荷姨站起来,抓着一把灰灰草,看了眼方校长。这是个喜欢单刀直入的男人。那天的联欢会上,荷姨就已经领教过了。
“把你的地卖给我,我会给你最合适的价钱。”
“你去要别人的地,跟别人商讨价钱去吧。”
“我就看上这一块了。”方校长走到荷姨跟前,鼻子触到荷姨的草帽。
“你要我把麦子毁了?”荷姨往麦地中间走了几步,麦子绿油油一片,像燃烧着的绿色的小火苗。
方校长的眼睛里有股东西,最终放倒了荷姨的坚持。
“你要拿这块地做什么?”
“这你就别管了,你只要明白,机会不是一直有。”
麦子在燃烧,这一点也不奇怪。她的眼帘在那一片海洋似的色泽中扑闪,她想到自己是应该休息下了。丈夫死得早,她自己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就靠着在土里劳作,养大了郑成明和小棉,尽管,她并不怎么爱他们。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从未年轻过,她的一生,直接从一个孩子过渡到了老年。她取下草帽,想到自己乱发如草,作为一个女人活着的样子,一直潦潦草草。在那条小街上,她经历了很多事。唯独,没有爱情。
她是被拐骗来的。像无法让她的血液停止流动一样,她永远无法遗忘这一点。
在方校长的注目下,她放肆地打量自己的人生。
有多少时候,她望着两个孩子,想着抛下他们,一个人逃掉。她也一直在想,能逃多远,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对他们遗传了所憎恨之人的特点而有的恼怒和厌恶大过了对他们的爱。他们一定晓得的,郑成明早早选择了逃离。小棉一直跟她对着干。小街上的人都认为她变态,包括我母亲。他们是用刀子一样的目光看她。
“事实上,我只要那块地就够了,你瞧,”方校长指着麦地旁边那块地说,“那块洋芋地,是直接连着学校现在的操场的。”
那块洋芋地是周爷家的。
绿油油的麦田里一阵阵波浪似的翻涌。
几个月后,人们看见方校长在那个有着最新设施的体育场上踢足球,方校长的身影像在一片麦子地里奔跑。
人们站在药店里议论纷纷,争执荷姨今后会干什么,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女人。
这个女人总让小街上的人大吃一惊。周爷最该说点什么的,看看周乐,周爷什么也没说。
荷姨得到一大笔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