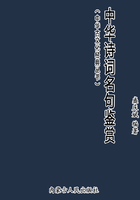从小胆怯,我不敢亲自撬开钟表的硬壳,掏取它精微的内脏……对秘密,我天然敬畏,但又饶有兴致和耐心,去观察修表匠如何擦洗金属零件中的油泥和积垢。
人类从伊甸园时代就受到警告,被驱出乐园,就是因窥破上帝秘密所遭受的惩戒。蛇加之好奇心的诱引,使夏娃摘取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其实智慧与文明的起源,往往与好奇心相关密切。但这种尝试是不被鼓励的,好奇回首的罗德之妻因此变成盐柱,没有逃离被巨力之手摧毁的索多玛城。夏娃和罗德之妻,《创世纪》上两个好奇心重而受到罚责的人物,恰巧都是女性;同样没有忍住好奇心折磨,从盒子里放出灾难的潘多拉,又是女性。也许这是男权话语背景下的书写,它们似乎在证明:女性缺乏足够的自控机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更强烈,她们想象旺盛,不轻易屈从神示的命运。
曾因好奇,童年的我目睹惊恐一幕。后院有棵病树,许多叶子镶了一圈枯卷的黄边儿,过早脱落在树基,也由此暴露原本树叶掩映中的鸟巢。那是只空巢吗?还是藏匿着沙砾图案的蛋卵?是否已有雏鸟啄破气室,闭合眼睑晾晒着潮湿打绺的毛羽?我向上攀爬,浅裂的粗糙树干磨破了表皮,我依然不放弃。巢离得不远了,阳光穿透孔隙使它镶嵌着诱人的光斑。突然听到弟弟的尖声警告:“姐,妈妈说不让咱们爬树。”我左臂拢住枝干,一边轻蔑俯视树下传达圣旨的胆小鬼,一边凭着感觉把右手搭向更高的树杈继续攀援。等炫耀中的我感觉异样,把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右手……恐怖景象令我头皮发麻、惊恐万状。右手恰巧按在一堆密集的毛毛虫之中,黑压压、毛茸茸、肉滚滚的虫体,有的被突然拍降的压力挤烂,有两条正试图穿过我的手背,然后我的视线花了,只剩下群虫拱动中微微变形的黑色团块。我忍不住凄厉惨叫,以最快速度逃离噩梦般的场景,我还没到触地的安全距离就离开了树干,重重摔到地面。我疯了般剧烈抖动手臂,尽管上面什么也没有,我还是一遍遍狂乱地拼命甩。周围伙伴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他们被我的失控举止吓坏了,飞速散开,把我当成沾染病菌的发病者。他们的离弃,伤害并提醒了我。我奇怪地开始追逐伙伴,好像碰触到谁,就可以把菌团传播出去,我的灾难就会被分担而减少似的。伙伴惊慌逃逸,我徒劳追赶,不知道自己怎么从疯狂中解脱。探究一棵树隐藏起来的鸟巢秘密,使我付出代价:由一个即将的先知转变为集体的弃儿,甚至成为众人的公敌。
世界被秘密支撑,也被秘密所诋毁。秘密如同人体微量的金属元素,多了或少了,都致病致命。每个人都习惯捍卫自己的秘密,它是易于被击伤的软肋;同时又热衷刺探他者的秘密,那是事半功倍的利刃。鳞片覆盖,裸露而脆弱的真相在甲胄保护下微微起伏。
我们会使用望远镜,我们会拆开不属于自己的信件——这是现代生活暗含的人际悲剧,通常情况下,除非偷窥,否则我们无法介入别人的生活。我继承着女性的本能——或者说是性别的局限,愿意猜测遮蔽和禁忌之下那个不希望被碰触的谜底。我的手慢慢伸进黑暗,究竟什么,将与指端相遇?小兽柔软的颈毛、植物错综的根系?还是另一只突然将我彻底拉入黑暗的暴力之手?
有时候秘密本身并无遮护,状若邪念和真理,从来袒露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具备承认和承担的勇气。所以,它才成为秘密。
所谓至交,是能与你创造或分担秘密的人。致你于万劫不复深渊的,那推动之手,往往也来自曾有资格与你共享秘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