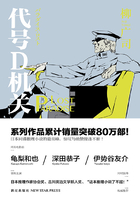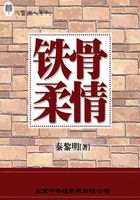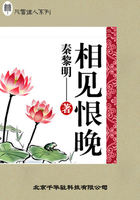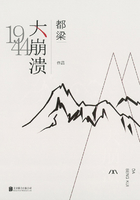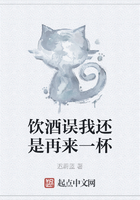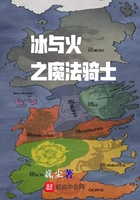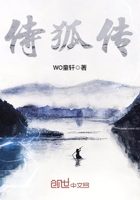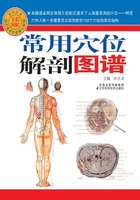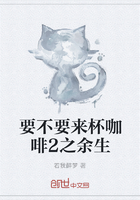来源:《湖南文学》2018年第05期
栏目:小说
黄昏时分的浏阳河第一湾,仿佛由一只硕大无朋的螺坨雾化而成,远山如田螺的翘臀,由浓渐淡的青黛,旋转着的姜黄色的泥土与夕阳,近处则像是挖掉了肉的田螺口,洁净清新。
公路和桥,河两旁的仿古建筑,这个离县城还有三十八公里的偏僻乡镇,呈现出一种对原始风貌的理解和尊重。他们只在桥的一侧修建了一排五百米长的低层商铺,而且是建在加高的河堤上,堤下的河床保持着原有的形态,泥沙卵石的岸滩,有人在古树下垂钓,或踩着野草散步。公路桥的下游五百米处的河堤上又修了一座人行天桥,其作用完全是为了体现古镇古色古香而悠闲的生活。
公路和桥是双车道,车辆川流不息。过了桥到了古镇的外边,沥青路面还是那样宽,两旁的水泥人行通道豁然开阔,可以竖着停下两台轿车。那人行通道亦是路边门面的前坪,而停在那里的车十有八九不是跟这些店做生意的,他们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跑到河堤上去吃唆螺。
一时间打电话的人无数,声音此起彼伏。
“到了吗?我到了。”
“哪一家的唆螺最好呷?”
可以想象的回答是,都好吃!快去抢位子吧!因为回答说第一家,进去的第一家,“一鲜唆螺”,已经毫无意义,要预定。
第一次去的一般还会打电话问,“我把车停在别人家的门口没事吧?”或者问,“我把车停在路边安全吗?”
回答肯定是“放心吧”。堤上禁止停车,人头攒动,摆满了桌椅。
夜幕降临,LED灯光开始闪烁,过往的车辆带着发光字体“官渡”“唆螺”的余晖,消失在漆黑深沉的四野,舌尖上的河畔,才刚刚飘起一丁点儿喧嚣和香气。
亮如白昼的“一鲜唆螺”制作间,原叔手脚不停地在那里忙活。立秋后最后一个秋老虎,过了今晚就意味着蒸笼般的炎热即将消散,气候将好得不能再好,这个时候的田螺肉美个大无籽,好吃得要让人飞起来。
“一鲜唆螺”跟别的店的唆螺吃起来不一样,厨房也是独树一帜,一圈一圈堆得有两米高的竹蒸笼,冒着热气,端起来有蛮吓人。因为原叔有要求,上菜要从最底下的一层上,蒸菜师傅把七八上十层的蒸笼从滚水大锅里移出来时,传菜员还必须搭把手,移开上面的蒸笼,只见那热气一喷,袅袅如七仙女指环间的祥云,蒸笼里面装满了一份一份的唆螺——那是原叔每天要敬的神。
厨房的一板墙上安装了超级方便好用的不锈钢蒸柜,做厨房设备的赵伢子曾一个劲地游说原叔把蒸笼扔掉。“老板,你看,”赵伢子边说边抽开蒸柜的一格抽屉,“多轻松多省事,只要多加几排咯样的格子,全世界的唆螺你都可以装得进去,多加格子就是。”
赵伢子说得对,店里的人也一边倒地支持蒸柜多加格,他们烦那蒸笼,要多点一炉火,每次取菜又重,但是,原叔不同意。就像谈恋爱,一方再优秀,另一方不点头,这恋爱就谈不下去。
“不是用竹蒸笼蒸的唆螺那不是咯个味。”原叔说。这也是他拒绝的理由。
那就巧,难道蒸柜蒸出来的东西带不锈钢味?蒸笼蒸出来的东西带竹子味?没这回事!他们都知道,原叔不晓得好固执,不晓得好霸蛮,店子是他的,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店里只有一名传菜员,手脚麻利,就是说话不怎么清澈。“十五号台,两份唆螺,一份卤鸭头,一份拍黄瓜一份花生米一份凉拌木耳,小炒黑山羊,酸菜炒苦瓜,清炒番薯叶,豆腐脑汤。”小伙子流利地报出菜单没问题,问题是他前面报得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到了中间嗓子又好像莫名其妙地破了。他的嗓子极容易破,譬如说被油烟辣味呛一下,譬如说被菜单上他不认得的字梗一下,或者吐气太猛,那嗓子瞬间就会变得嘶哑软塌。不过,他的嗓子要好起来也是飞快的,只要鼓一下眼睛,或者咽下点口水,那声音马上又震得锅响。
厨房里噪音本身就大,传菜员报菜名的声音又极不稳定,竖起耳朵都听不清,弄得炒菜的大厨直想拿勺子去敲他。
原叔摇了摇头,露出的笑容让炒菜的大厨也笑了。
店里的每一个人,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就没有喘息的时间,特别是厨房里的人,衣服都没干过,从打湿的上衣中拧出来的汗水差不多都有半杯。工作太累,性情就急躁,彼此间会为一点点小事发些莫名其妙的火。传菜员是他们的出气筒,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按他的传令来做,也只有他的岔子好找。
“十六号台……”传菜员流畅地报出所需菜品,最后一个桌子了,大家为店里的好生意由衷地感到高兴。别以为他们高兴是可以歇息了,才不是呢,一张桌子一晚翻四次台,很平常。人一高兴,做事就特别顺,传菜员菜名都要报得好些。当传菜员照单念到十六号台的最末一道菜,想都没有想就发出声音来,“清炒秋菜。”
“清炒秋菜。”炒菜的大师傅跟着传菜员咕哝了一句,表情像是快要被一只大包子噎死了。秋天里的菜都是秋菜,都要炒啊,这回他真的要拿他手里的长把勺子敲那细鳖了。
“清炒秋葵。”原叔说。原叔当然晓得,那个“葵”字点单里出现得少,跟“菜”字看着差不多,店里的正式菜谱上写的是“洋辣椒”,传菜员念错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