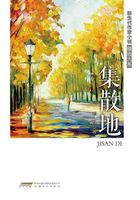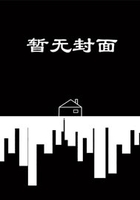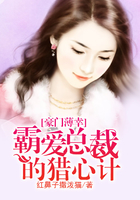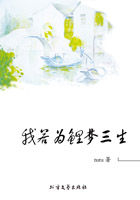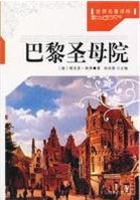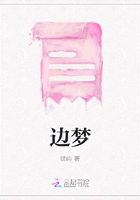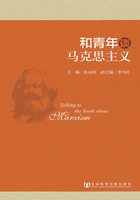雷达
有些小说无“魂”,有些小说有“魂”!这区别时常很神秘。无魂的小说表面上看不出,它也许显得精致而匀称,最新的技巧也能娴熟运用,唯因缺乏深刻的人生体验,终像一幅外表优美的人体画,没什么内涵,怎么也唤不起你倾诉点什么的欲望,它是外在于你的存在。有魂的小说不同,它可能过于素朴,也可能失之粗糙不文,却是个有生命的活物,血色旺盛,灵性跃动,似有股从内向外膨胀的力,这种小说读来让人怦然心动。我们常常困惑于有些拿情的不可理喻:为什么看来水平相近的作品,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记住其中的某一篇?为什么功力相近的作者中,有的人并未经过人为的大力宣传,自己也浑然不觉,却在一个早晨忽然为文学界默契地承认了?对这种无形的选择,人们了既慨叹造物主的不公,又怀疑是否有一种看不见的信息密码在起作用。后一点可能真的存在,它应该就是隐含在小说中的魂灵。
在我看来,尽管肖亦农的观念比较传统,他的写实有些朴拙,他的世界也不甚新鲜,但他是个有魂的作者,他的有些作品是有魂的作品,因而即使在小说读者锐减的今天,他还是被人们记住了。
在肖亦农的小说里,有一位无时、无处不在的主人公,她就叫黄河。在作者笔下,河套地区被称为“金色的弯弓”的黄河,确是千姿百态,气象不凡。他写“开河”的动地惊天,写“凌洪”的狂暴无忌,写“跌浪崖”的黄龙长啸,写“蹚冰道”的命如悬丝;又写夜的黄河,晨的黄河,黄昏的黄河;还写河上遮天蔽日的尘沙,万面大鼓齐擂似的雄风,时而柔情万斛,时而暴矂疯狂。这些,无疑是构成他的小说强悍恣肆外观的重要因素。然而,黄河在小说中决:不仅是外在的景观和陪衬,它像血液似的渗进每个人物的心胸,它是内在的魂魄,内在的精神,它是人格的对象,人是它的对象,“黄河怎样流,我就怎、样活”。肖亦农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是无法搬到别处和别的作品中的,它们和地域,和气候,和大自然是如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离开了黄河,它们将不复存在。二才老汉,火队长,瞎老明,小顺子这样的黄河船夫,河路汉子,水女子这样的黄河女儿,黄小光、“我”、“多米”这样的知青,不管他们有多少不同,共同的是作者都给他们赋予一种黄河性格。这就是在严酷生存条件下不屈不挠的生命韧牲,就是黄河一样开阔的胸襟,就是黄河一样的生命冲力。如果说,肖亦农确实侧重于依赖传统价值、传统道德和人伦精神来支撑他的世界,甚至没有注意到批判封闭的农业文化和国民惰性,那么,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决不抽象地歌颂抽象的“人民”,也不教条式地颂扬他的人物多么勤劳多么勇敢,他的笔开始深人到生命的隐秘层面,以自己真切的亲历亲闻,写出了河路汉子们的生存本相:写出他们在极端艰难的生存威胁下,在生与死的大灾痛面前,那承受苦难的惊人耐力,那抗拒自然的生命魄力。他并没有在肯定奴性的前提下来描写这一切,他只是没有把作品的主题转向政治或文化的批判,而是转向了对生命力的礼赞。这当然也是应该肯定的,并不意味着放弃批判。这种悲剧性的赞歌同样是深沉有力的,作者没有也不想削弱我们生存中的悲剧性因素,只是他更欣赏生命的强悍和野性的力量罢了。
肖亦农的小说不但有“魂”,而且有“情”。激情充沛是他的小说又一重要特点,他夫要不是靠哲理的启迪力,而是靠灵魂的剖白,生活中情感的波涛来撞击读者,感染读者。对于“情”是需要作些分析妁。我们的文学曾经充塞过大量虚假的、矫饰的、伪造的情惑,人们早已厌倦了,于是在新时期,一轴理性的、批判的、反思的情感出现了,那种浓烈的抒情性作品也棺对减少,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肖亦农似乎在接过传统中的抒情性加舉自己作品的力量,但已不复是传统的情感方式了,抒情的性质和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内蒙兵团的知青,他有着和《血色黄昏》的作者一致的渲泄情,感的欲望,只是,他更加文学化,在暴露真实的程度上也不及后者。在肖亦农的作品中,有个同样无处不在的人物一作家主体“我”。这个“我”是个平民子弟,对普通人的痛苦非常敏感,他恋涂,他孤独,他忧伤,他多情,他的胸中时时鼓动着愤世嫉俗的念头。在《红橄榄》里,这个平民子弟很容易贴近二才老汉和水女子们的心;在《孤岛》中,这个“我”是黄小光,他忍受了极大的孤独,才+七岁就品尝了人生的诸多阴暗和辛酸;在《丹丹》里,这个“我”又幻化为女接线员丹丹,与团长的“对骂”何尝不是这个“我”的自然流露,丹丹的恐惧感又何尝不是“我”的恐惧感呢?这个“我”缺少居高临下的哲人风采,他有浓厚的普通人的人情味。我们尽可指出这个“我”的锞点不高,从而决定了肖亦农整个作品的平民化风貌和平视角度,但也正因其平民精神,使得他的作品中的情感真挚,单纯,容易亲近,易于感人。短篇小说《同路人》戚开了肖亦农惯用的知青视角,也脱开了他以往的题材面,大胆而尖锐地揭露了改革中的某些腐败现象,曾引起相当的反响。它是肖亦农创作中的一个变调。但我以为那个“我”依然存在,他成熟起兹而且更关注社会新的变动,那种平民的批判精神依然强烈的存在,那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现实主义精神强化了。不过,这可能是偶尔为之的变调,真正的肖亦农是黄河波涛中的船夫,他捧给我们的大约还是一碗含有泥沙的甘甜的黄河水吧。
近年来,现实主义创作迅猛地向前推进了,开始展示出某些新的素质和风度。肖亦农是这股思潮中的一员。他们以更加原色化的笔墨,更加严酷的真实,向着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逼进,向着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民族炅魂的路途前进。肖亦农似乎是更靠近传统的一个,他很注重高潮的组织,很注重情节的力量,很注重在自然、社会、人的纠葛中展开强有力的冲突。这无可厚非,各种途径都能通向文学的圣地,也许肖亦农注定了是一位写实型的作家,那么,既然他以他生命休验的真切取得已有的成缋,他的新发展同样只能植根于此。黄河在呼唤她的船夫,我们也盼望肖亦农新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