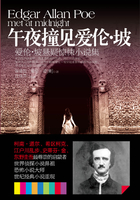其实细算起来,在那段时间,我已开始疏于回家了。
六年前的人工肾病房还刚刚设立,所以不像今天规模。那时总共只有四个医生,除去我,一个正在酝酿生孩子,另一个则刚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剩下的就是主任。
当时主任正忙于争取出国讲学的事。老太太一边痛哭流涕地找局里有关领导谈话,一边努力修改自己的学术论文,还要四处奔走去打听如何通融如何办理那些花花绿绿的出境手续。据说主任出国的理由,是准备去给外国人讲一讲中国的肾脏修复手术。主任很诚恳又很煽情地对几位副局长说,请相信一个老医学工作者的忠告吧,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人文状况,肾科临床亟待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肾脏疾患直接体现着中国婚姻的普遍形态,而且越是年轻的男性,患者就尤其多,据一个中医学术部门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患肾虚的成熟男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主任说,她之所以要力争出去讲学,就是想借助外部力量,在国内迅速掀起一个保护肾脏运动,以拯救我们的男性国人,改变中国的婚姻形态。主任又说,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尤其发达国家,人家无论什么东西,动辄就换新的,肾脏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肾移植手术比咱们要先进。可我们中国人习惯艰苦朴素,甭管什么都讲究新三年旧三年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我们的肾脏修复技术就比他们搞得要好。但令人遗憾的是,主任的这些话却并没有引起局长们的多大兴趣。那一次出国讲学任务,最终还是派到了一位对改善女性性冷淡有研究的妇科主任头上。
主任为此悲愤交加,对上班也就再无心思。
所以,在六年前的那个秋天里,我几乎是在连续值三十六小时的大连班。
那个叫江昊的八床病人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是在几天以后。
江吴的尿液越来越浓,血却像水一样稀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贫血会使病人的血液浓缩,而丧失肾功能尿液又会很清淡,江吴却都颠倒过来。我再次让人将他的血和尿样送去化验室化验,并在医嘱中加了安定,嘱咐护士小林让他多睡觉。医生治疗绝症患者,大都讨厌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有头脑,思想敏锐,多愁善感又懂科学知识,患了什么病自己比医生还明白,一般不好唬弄。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睡觉。
那是一个上午,病房又收进一个肾衰病人。
当时已经没有床位,我只好让他加在八床旁边。这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看上去气宇轩昂而且脑满肠肥。他被抬进来时已经深度。肾昏迷。我与患者家属商议之后,决定立刻为他做植管手术。我通知手术室,让立刻准备卫生包,又开了一系列手术用药让护士小林去药房取药。然后,就忙着为病人量血压做心电图和其他术前检查。
这时江昊已经醒来。他朝旁边的加床病人看了一阵,忽然问,他是什么病?
加床家属哭丧着脸说,慢性肾衰竭,大夫说……就是尿霉症。
江昊问,也做植管手术吗?
加床家属说,是啊,听说做了手术也……
我立刻抬头瞪了那家属一眼说,不要影响医生工作。江吴就翻过身去不再说话了。
加床病人的手术定在那天晚上。傍晚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鬼鬼祟祟来到医生办公室,他一进门就说,我是……八床加床的儿子。
然后又问,今天晚上,主刀是哪位医生?我问,你有什么事。
儿子就走上前来说,老爷子不能死,他是银行信贷处主任,对我们家很重要。我告诉他,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他就是银行的行长该死也得死。儿子立刻逢迎地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该死该死,不过……
他一边说着,就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到桌上。我笑了一下告诉他,医院不是法院,在这里花钱是买不了命的,疾病可不认人民币。
儿子诡谲地眨眨眼说,疾病不认,手术刀还不认吗?我说,手术刀要认人民币,可就不认识病了。
儿子立刻表示出对崇高的敬佩,感动了一下就又鬼鬼祟祟地出去了。
八床加床的病人躺到手术台上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这老男人的腹部备过皮之后和猪皮很相似,毛孔很大,又有一种恬不知耻的细嫩柔软。我用艾利斯夹起碘酒棉团在他的腹部擦过,又用酒精棉团脱碘。这老头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打上杜冷丁反而清醒过来,他先是无精打采又很矜持地眨眨眼,当发现自己正精赤条条地躺在一个女医生和一群女护士面前,似乎突然一下兴奋起来。
他身体躁动了一下问,大夫,局麻还是全麻?我随口说,局麻。
他哦了一声,像是松了口气。
我开始用手术刀切割他的皮肤。他的皮层很厚,脂肪层更厚,白花花的像动物油脂一样丰富。我一边切着心想,这可都是民脂民膏阿。
我对切割肌肉的声音历来很敏感。孩子肌肉切起来有一种清纯的咝咝声,很无辜,少女的肌肉声音就有些矫揉造作,听起来让人感到不舒服,也不自然。年轻男人的肌肉是一种虚伪又故作强大的吱吱声.,手术刀发涩。这种老男人的肌肉切起来声音最难听,像还没睁开眼的老鼠叫。
老男人的身体突然扭动了一下,呼吸开始粗重起来。我感觉操作有些碍事,于是抬起头问,感觉疼吗……也就在这时,我无意中朝他的下体瞟了一眼,突然感到胃里一翻。
小护士们的脸色也都开始难看起来。
我盯视着那张皱巴巴还恬不知耻的面孔。他这时已冲动得面色红润起来。
这时,麻醉师突然报告说,病人的血压正在下降,心率也出现异常。
我立刻停下来,准备在静脉推注急救药物。但是,麻醉师接着又说,不用了。
我看了看,就放下手术刀说,撤吧。
小护士们立刻用白布单将这老男人蒙起来。他那下体的地方仍在高高地支棱着,看上去像一顶小帐篷。
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我回到医生办公室仍感到一阵阵恶心。这时门外突然乱起来。我推开门一看,只见苹果山竹荔枝红毛丹飞得满楼道都是,一个六十来岁还修饰出许多妇性特征的丰满女人正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地号啕大哭。手术前那个自称儿子的男人正站在一旁慷慨激昂地大声吵嚷,说他父亲在没做手术之前还好好的,只在肚子上拉了那么一个小口人就断了气,这显然是一起医疗事故。周围还有一些男男女女大概是叔姨姑舅,也都在悲痛欲绝地群情激愤。他们一看见我,立刻就都冲上来说,你是主刀医生,你倒说说看,我们老爷子凭什么就这样死了?
我平静地说,死者就在手术台上,还没穿衣服,你们去撩开单子看一看就明白了。
我想了想又对她们说,女性家属就不要去了,当心吓着。
这件事以后,我在宿舍里休息了一天。
我再上班时,八床江昊的尿量就已很少,而且频繁出现恶性呕吐症状。
那天早晨我到病房查房,江吴刚又吐过。护士小林正在帮他收拾,一边嘟囔着抱怨说,已经病成这样了,家属也不来陪伴,我们当护士的要这样全方位伺候哪里伺候得过来。江昊的脸色很难看,像一摊熔化的蜡汁汪在床上。
他突然喘着粗气说,我……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弄!
他的声带像一块破布,说话时拉出一串褴褛的声音。
我掏出听诊器,开始为他检查。他的血压仍然很高,心脏也跳得一塌糊涂。
江吴突然问我,加床的病人呢,他做了手术怎么没回来?
我淡淡地说,他转到另一问病房去了。
江吴似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他和我……是一样的病吗?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告诉他,病是一样的病,但每一个人的具体病情是不一样的,身体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我一边说,就将听诊器缠起来装进白大褂的衣兜。江吴看着我,突然定定地说,我很快就能好。
我说,对,你很快就能好。
江吴又有几分骄横地说,我争取……下个月就出院。我说,好吧,你争取吧。
这类病人在这时大多会出现这种情绪,我甚至能猜出他们此时在想什么。他们已经感觉出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枯萎下去,却又不敢承认。当然,这多是男性病人。男人比女人更脆弱,也比女人更怕死。我曾经收治过一个很年轻的尿毒症病人,是个私营业主,二十多岁财大气粗,住院时三四个女人众星捧月一般送进来的。当时他告诉我,他有钱,只要是中国有的药就只管给他用,不要问价钱。我耐心告诉他,这种病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个银行也不行。他听了一口气摔烂病房里的十二只暖水瓶,然后以每只一百元的价格赔偿。他每天的医药费最高达到两千多元,一支复达新在当时是两百多元,他坚持要一天打两针,一支白蛋白六百多元,他一口气买了五百支。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医药费花掉几十万,人也双目失明了。直到最后几天,他仍然很骄横地眨着两只干枯的眼睛重复着一句话,下星期我就能出院,钱算个屁!
又过了一星期,他果然出院了,钱对他,也真的算个屁了。
我在那个查房的上午看着江昊想,他迟早也会失明的。凝血机制遭到破坏首先会导致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出血。但我还不想将预后结果告诉江吴。我知道他经受不住。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这样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其实非常可怜。然后又想,他的身架很好看,如果不是躺到这里,应该是个很矫健的男人。我曾在心里反复猜测,他在大学里究竟是教什么课的呢?我感到他有些神秘。
护士小林端来一盆热水,拧出毛巾要为江昊擦脸。我突然对小林这种过分的殷勤有些反感。
我瞥了她一眼说,让他自己洗,动一动是有好处的。护士小林立刻放下盆,红着脸委屈地出去了。
江吴忽然说,你这样说她,没有道理。
我轻蔑地笑笑,拿起血压计走了。
我走到门口时,听到江吴在身后说,你们的这个小林护士,挺可爱的。
也恰在这时护士小林一步迈进来,立刻被这句话撞得满面通红。
我突然有些愠怒,看着护士小林问,你又有什么事?护士小林说,八床……八床的家属来探视了。
护士小林说罢,就转身匆匆地走了。
江昊的脸色立刻难看起来,不安地瞟着病房门口。我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看他,临出病房时又回头提醒说,江老师,注意你的心脏。
在这个查房的上午,我从病房里出来,经过护理部时见护士小林正朝这边走过来。她远远看见我,连忙又转身走开了。那一天,我还是第一次反感护士小林。我觉得她有些虚伪,一边抱怨病人没有陪伴,一边又上赶着像伺候情人似的伺候人家。
我想,其实小林没必要这样。
我在那个查过房的上午回到办公室,又翻出八床江吴的病历。
八床江吴的病史很复杂,似乎与个人履历搅在了一起:上中学时患的。肾盂肾炎,下乡插队后转为慢性肾炎,上大学期间曾复发过几次,毕业留校后再度发作,并开始出现蛋白尿、恶心、贫血、口腔有异味和视力减退等一系列症状,先确诊为氮质血症,后发展为慢性肾衰竭。我又拿过刚回来的化验报告看了一下,心里考虑着,从江吴目前的临床症状和各项参数看,显然都已达到了手术指标。
护士小林走进来,低着头说,夏医生,你快去看看吧。
我立刻猜到又是八床江吴。
果然,小林说,八床家属正跟病人吵架,闹得很凶。
我立刻起身来到病房。只见八床江吴的床头正站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不过从她的装束看,显然不是江吴的同行。她正眯起一只眼冲着江昊微笑,那笑容里有些阴冷潮湿。她说,你说完了吗,如果有话还可以继续说。
江昊可怜巴巴地仰起脸,像个孩子。
那女人美丽的半边脸上拧起一丝冷笑,眼神像盯视着一只吞了耗子药的老鼠。就这样盯视了一阵,她突然恶声恶气地大声说,我就是不愿意来,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
我被吓了一跳。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从那样一只精致小巧的头颅里,竟然能爆发出这样大的声音。江吴嗫嚅着,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他说,我……并不是非要求你来,我只是说,我现在病得很重,生活已经基本不能自理,你哪怕……每天只抽出半小时,来帮我一下。
女人说,我忙,我忙你知道吗?你已经这份儿德性了,可我还要有我自己的生活!
她说这番话时弯下身,几乎是直冲着江吴的鼻子。江昊讷讷地说,是啊……你说得对。
我真不能理解,江吴竟然还说这女人说得对。
江昊飞快地瞟了那女人一眼,忽然又难为情地问,他……又去找过你吗?
那女人冷酷地笑笑,满足又很得意地说,当然找过,每天都来。
江昊的脸上顿时浮起一层死一样的微笑。那女人快乐地说,怎么样,你满意了吧?江吴说,那个人,靠不住的,你要小心。江吴说得很理亏,而且带有几分羞涩,似乎做出这些事情来的是他自己。
那女人一下笑起来,像用两块铁片磨出来的声音。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走进病房问她,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那女人后退了一步,上下看看我问,你是病人的什么人?
我扶了一下颈上的听诊器说,我这身衣服,还用解释吗?
那女人一撇嘴笑了,说,这可说不定,这年月,牵条狗来披上白大褂都能当大夫!
我觉得自己的脸立刻涨红起来,但随之也笑了笑,说,给狗披上白大褂能当大夫,可给你披上不一定行,你相信吗?
这女人被噎得哏儿喽一声。她吊起两根细眉冲我张口结舌了一阵,然后转脸对江昊说,你在这里可真幸福啊,有美丽的白衣天使给你撑腰啦!
说罢将胸脯一挺,转身踩着一溜碎步走了。我走过来,抓起江吴的手腕数了数脉搏。江昊忽然说,其实……她是个好人。
我没说话。在这个秋天的上午,我的心里充满对江吴的鄙视。
江昊沉默了一阵,忽然又说,她是我爱人,过去……我伤过她。
我想,直到这时他还在为那个女人开释,真难为他了。我只又说了一句,你血压不稳定,要注意控制情绪。然后就转身从病房里走出来。
六年前的那个秋天非常潮湿,而且闷热。
那一段我已连续值了十几个大连班,主任和另两个医生还没有来上班的意思。当时我想,这样也好,我宁愿在医院值班,也不想固家去呼吸那币争早已令我厌倦的空气。
同时在那些日子里,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讨厌江吴。我想,也许这讨厌里更多掺杂的是一种鄙视的情绪。我每天除去查房和必要的巡视,也常到病房看一看,我经常挑江吴的毛病,并当着全病室的病人训斥他,甚至用一些刻薄的字眼挖苦他,看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满面通红惴惴不安的样子,我就会从心底生出一丝恶狠狠的愉快。病人开始在背地里议论,说也难怪这个夏医生的脾气这样凶,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生孩子,性格自然不会正常,这就像不生蛋的母鸡,又肥又壮比公鸡还好斗。
我听了这些议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江吴很快患了失眠症,每到夜里就浮想联翩,给他吃药打针都无济于事,天一亮就又昏睡过去,一直到下午才肯醒来。这是危重病人的常见症状,整天躺在病床上与世隔绝,渐渐生物钟紊乱就失去了时间概念,久而久之,也就昼夜颠倒了。每到夜里,护士小林一去病房为他注射镇静剂或者撤液,他就会拉住她天南地北地神聊,有时聊高兴了还大声说笑,吵得四邻不安。这种情况后来被我撞见过一次。我狠狠将小林训斥了一顿。小林不敢正面顶撞,但还是不软不硬地辩白,说护理条例上有明文规定,护理人员有义务对患者的精神进行护理,她说她这也是按条例上办事,如果不准许这样,那她以后不这样就是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明白,小林是一个很出色的护士。
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却对小林越来越不满意,尤其看不惯她一系列的刻意修饰和打扮。我对她说,好端端的白大褂你怎么改得那样瘦,白大褂本来就是罩在外面穿的,肥大一些工作起来才方便,你改得不伦不类这像个什么样子?我还对她说,你把头发烫得像一团拆开的毛线,帽子那么顶着算怎么回事,想把自己打扮成三削、姐呀?
小林被我训得不知所措,整天惶惶不安。
一天中午,我到病房巡视,发现江吴的输液记录中没有氢氧化钠。我立刻把小林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小林说,护理部没有了,去药房取他们又说要一半天才能到。
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这几天病人的呕吐症状得以缓解,就是氢氧化钠的作用,没有我的医嘱你就擅自停药,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小林小声嘟囔说,不就停了一天药么。
我的火气腾一下就冒起来,我说,只停一天药?你说得倒轻巧!
小林立刻不敢再说话了。
我瞪着小林说,你知道病人呕吐是怎么回事吗?是酸中毒引起的,难道酸中毒是怎么回事你在护校没学过吗?一天停药就有可能出人命,你不知道吗?!
这时,江吴忽然在病床上说,夏医生,你们医学上的事我不太懂,不过药房里没有药,也不是小林护士的责任,你没必要这样训斥她。
我慢慢转过身,冲他笑了笑。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六年前那个中午的笑容一定极为难看。
我就这样笑着对江吴说,你对医学上的事情确实不懂,不懂就不要乱插嘴。
我又说,你知道氢氧化钠起的是什么作用吗?不知道?那就先让我们的小林护士给你讲一讲药理,然后再替她打抱不平吧!
我走到病房门口,又回过头说,氢氧化钠,对你很重要。
当天晚上,江吴突然提出想和我谈一谈。
当时我刚刚巡视完病房,正要回办公室去写医嘱,就对江昊说,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再说。我也是想故意拖延一下,我不想让他太神气。
待忙完手头的事,我才又来到病房。我对他说,你要谈什么,说吧。
江吴一反常态,他看了我一眼,又嗫嚅着把目光移开了。
我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说,你有什么话快说,我还很忙。
江吴好像下定决心,他问,那个加床病人……不是换病房了吧?
我想了一下,对他说,对。江吴立刻问,他,死了?我说,他死了。
江昊喃喃着说,死了……他果然是死了。接着,他又问,这种病……很麻烦吗?我想说,岂止是麻烦。但话到嘴边,还是说,所谓慢性肾衰竭,是指人的肾脏器官逐渐衰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初期患者并没有什么感觉,只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症状才会逐步显现出来,引起肾衰竭的病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最根本的原因是肾脏经过长时间的慢性炎症,比如肾盂肾炎,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肾动脉硬化等等,它使肾脏受到实质性损伤,导致肾功能的大部乃至全部丧失,使许多有害物质潴留在体内,血液中肌酐和尿素氮含量增高,进而随着全身血液循环系统破坏其他脏器……我像在宣读教科书,一句一句刻板地说着。
我有意用这种语气说话,因为这样可以隐隐地产生一种调侃意味,使这些话听起来蒙上一层半真半假的色彩。但如果是一个具有一定医学知识的人,听了这番话就会明白这种病有多么可怕了。慢性肾衰的确是一种比癌症还要可怕的疾病。
江吴笑了一下说,我想……做手术。
我感觉到了,他的笑里隐隐含着乞求,而且,带有几分讨好。
我说,这要等新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才能定,看够不够手术条件。
江昊一愣,做手术……也要看条件?
我一笑说,当然要看条件,手术成功与否和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那个加床病人,原本不符合条件,但他的家属坚决要求手术,所以才有那样的结果。
江昊把脸别转过去,沉吟了一下,又转过来问,这种手术,能彻底根治吗?
我明白,江吴问的是一个很专业而且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想了一下,还是把话题绕开了。
我说,这种手术叫腹膜透析治疗法,简单地说,也就是在腹部植一根乳胶管,定时将一种无机盐水注入腹腔,然后再定时排放出来,利用分子量和腹膜毛细血管的透析原理,将血液中本该随着尿液通过肾脏排泄出去的废物从透析液里排出来,如果说得更形象一点,也就是植入一只人工肾脏。
我说,所以,我们这里才叫人工。肾病房。
我说到这里,突然发现江昊的脸色像床单一样地惨白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与朱大可的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应该是从六年前一个早晨的瞬间开始的。就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对朱大可的感觉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这六年里,我经常会想起那个尴尬的早晨。
那好像是个星期一。前一天的下午,主任来到病房。
主任一进门就将一摞牛皮纸袋摊到桌上,然后对我说,你今天回家去住一晚吧,过个星期天,已经这么多天了,我替你顶一个班。
我立刻说不用,在这里挺好。
主任说,我可以在这里整理论文,反正哪干都是一样。我一听也就没再坚持,起身换衣服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好像是最后一次回家。从那以后,我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彻底安下身来。那个下午我没骑车,也没有乘公共汽车,就沿着街边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地往回走。在病房里一连闷了几十天,外面的天气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凉爽了。空气像水一样清澈透明,路边的杨树叶也变成了暗绿色,迎面吹来一阵轻微的秋风。
远处电报大楼的钟表敲了四下。
我想,朱大可现在还在他的焚尸炉前热火朝天地工作,脚下就加快了步子。
我想赶在朱大可下班之前到家。从医院出来时,我特意带了一袋血浆,这是一个危重病人留下的,还没来得及用人就死了。我准备把它带回家,当做肥料浇到朱大可的宝贝花里。朱大可有一盆变色木,据说是荷兰传过来的花卉品种,长得非常茂盛。我曾几次警告他,说这种花很危险,释放出的气体对人极为有害,可以致癌,但朱大可却始终置若罔闻。每当看到朱大可若无其事地摆弄那盆花,我就觉得他像把一条毒蛇当成宠物。我知道,朱大可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花,如果将这袋血浆浇在花盆里,我这一夜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自结婚以来,这种方法一直是我最有效的护身符。
那时候我并没有性冷淡,但一想起与朱大可做爱,心里就充满厌恶。许多事情细想起来似乎都有着某种荒诞的联系,比如像这袋人血,倘若它在医院里被装进一次性输液器,可能会救活一个病人,而如果浇在那盆变色木里,这天夜里就会将朱大可的那座炼人炉闷下去。同样是一袋人血,它能拯救一条生命,也能扼杀一条还没有形成的生命。我算着日子,这一天恰好是我两次例假的中间时间。那时我虽已年近四十岁,但生命力仍还旺盛,我很清楚,我受孕的概率仍然很大。
我始终没打算要孩子。我总在想,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家庭,毁就毁在孩子身上。一些深怀父爱或母爱的年轻父母本来彼此已毫无感情可言,他们完全可以各自重新建立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但看在孩子身上就硬在一起苟且地凑合下来。每当听到一句:唉,看孩子吧!我就会从心底里可怜那些善良的小父亲和小母亲们。其实我很清楚,朱大可非常想有一个孩子,每次和他一起出去,看见人家抱着孩子,他总是面露羡慕的神情。朱大可曾对我抱怨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他总还有一种非法同居的感觉。我很认真地对他说,有这种感觉就对了,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孩子,那就永远你是你,我是我,一起生活就像同居一样,而一旦有了孩子就不同了,孩子会将两个人缝合到一起,弄不好还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我明白,这些话朱大可是理解不了的。在那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一回家先把那袋人血浇到花盆里。黏稠的血浆渗进土壤,发出一阵咝咝的响声,令人听了有种舒适的感觉。我发现土壤对人血有一种热情的亲和力,就像母亲拥抱久别的儿子,相比之下,它对水的专横渗入就如同妻子对丈夫了,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我在这个傍晚洗澡时,忽然想起江吴。
我想,这几天,我是不是对他有些过分了?作为一个医生,尽管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向病人透露病情,但从医德的角度,从中国人心理特征的角度,还是不应该这样做,一个人突然面对死亡,这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这种怀疑早就有了,我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患,比如偏执?或者别的什么?
我在六年前的这个夜晚,果然睡得很安生。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竟然宪好无损。朱大可已经起来了,正站在床前,用一种从没有过的眼神盯视着我。
他冷冷地问,江昊是谁?
我愣了一下,有些奇怪,你怎么知道江吴?
朱大可忽然古怪地笑了,似乎眼睛的后面还有一双眼睛。
他说,你这一夜说梦话,一直在喊这个名字。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发现,朱大可与江昊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人。其实这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极为不同的人,不同得简直判若云泥,但没有比较时,却又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的不同。我想起一位先哲说过的话,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朱大可盯视了我一阵,又说,我昨天刚刚烧了一个姓江的,戴眼镜的小白脸儿。他说完,就晃晃悠悠地上班去了。
在那个星期一的上午,我来到医院已是九点多钟。
主任刚查过房,向我交代了一下就匆匆走了。
我翻看了一下夜班记录,心里突然呼地一沉。江昊夜里曾两次出现心衰先兆,血压也持续上升,并伴有水肿和阵发性抽搐。我连忙放下记录朝病房走来。
我在这个早晨走进病房时,不禁大吃一惊。江吴的脸像一只被水浸泡过的馒头,已经蓬松得有些走形,看上去凡是带孔的地方都已漫平了,涨成一张完整平坦的肉脸,如果不是床位号,我已经完全认不出他了。他的气质似乎也变了,像个老太太,或者更形象地说是像那种被阉过的男人,有一股丑俗的女人气。
小林正伏在床边,做着输液前的准备。一根头皮针在江昊又厚又亮的手背上探雷似的到处扎来扎去。我突然有些恼火,斥责她,病人都肿成这样了,还用什么头皮针?!
小林已经满头大汗,抬身捋了下头发,连忙又换了支大号针头。
我立刻又说,输液又不是输血,用得着那么粗的针头吗?!
小林手忙脚乱地又换了一支三号针,小心翼翼地扎了一下,没见回血,再扎,还是没有回血,她说,肿得太厉害了,血管条件实在又差……
我厉声说,你把胶管勒得这样松,血管条件再好也绷不起来!
小林突然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眼泪呼地一下就流出来,她说,夏医生,我……都是按照护理规范操作的,我不知……错在哪了?
我没再说话,拿过针头,在江吴的手背拍了拍,然后小心地探寻着。江吴由于输液太多,血管已变得又脆又硬,我终于找到一根小血管,总算扎了进去。
我直起身,轻轻舒出一口气。
小林转身走出病房,楼道里响起一串咯咯的脚步声。
我在医嘱里为江吴加了速尿和两支白蛋白。我认为江昊的水肿是由蛋白缺失引起的,而心衰又是水肿引起的,速尿和白蛋白可以同时缓解这两种症状。我将写好的医嘱送到护理部,见小林正坐在送药车上抹泪。我这才意识到,刚才对她确实有些过分了,于是放下医嘱,只淡淡地对她说了一句,先去取药吧,回来再哭。
然后就转身走了。
我开的药物起了作用。江吴就像一具拔掉气门的橡皮人,水肿很快消了下去。吃过晚饭,小林来问,说八床江吴的静脉药物都已走完了,液体撤不撤。小林说话越来越注意,每次提到江吴,总要在前面加上八床,这样听起来似乎更公事化一些。
我想想说,先不要撤吧,走葡萄糖保留针头,以防夜里再有什么意外。
小林听了并不走,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看看她问,还有事吗。小林支吾了一下,才说,八床江吴……想让我替他打个电话。
我问,给谁打?
小林说,一个叫苏爱萍的女人,八床江吴说,想叫她来。
我立刻想起上一次见过的那个漂亮女人,于是说,那你就帮他打吧。
小林飞快地瞟了我一眼,耷拉着眼皮说,夏医生,这个电话……还是你来打吧。
我并不太恶毒地说,这是人家托你办的事,可没有托付我啊。
小林说,我办这事……不太方便。
白小林的意思,也不想再难为她,于是说,那好吧,电话我去打。
小林听了如释重负,放下电话号码好看地一笑,就转身走了。
我很顺利地就给那个叫苏爱萍的女人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带着一股笨重的鼻音。他好像有些不大情愿接电话,咕哝着问,你找谁?
我说,请问,苏爱萍在吗?
对方似乎愣了一下,沉了沉才问,你是哪里?我说,医院。
对方又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活的?
我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说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无关,紧兽.个句话究竟是哪里我也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找一下苏爱萍,请她来听电话。
对方立刻说,苏爱萍不在这里,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然后就是一阵嘀嘀咕咕抱怨的声音,显然是在用手捂着话筒说话。
又过了一阵,话筒里就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喂,我是苏爱萍。
我立刻听出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声音。我说,江吴已经病危,他很想见一见你。
对方顿了一下说,哦……咱们好像见过面,你就是那位白衣天使吧?
我说,我是谁并不重要,现在江吴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我是在向你转达病人的意愿。
对方在电话里打了个哈欠。我说,你来一下吧。
对方说,我这两天很忙,脱不开身,过几天再抽时间过去吧,再说,医院有你们这样的白衣天使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我几乎是将话筒摔到电话机上的。
放电话之前,我已听出对方的声音有些痛苦忸怩,这是女人在忍受男人的抚摸和撩拨而又不得不做出些矜持时所发出的那种声音。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电话那一端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