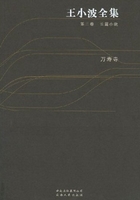诺安克岛是个小岛,离美国东海岸极近。1585年一批欧洲移民乘七艘船最先来到这里。他们留在岛上,并和船队约定第二年某时再在该地会合。一年以后,当船队如期返回时,他们却没有露面。原来约好他们要在一棵大树上刻下地图标明自己的去向,也一直没有找到那张地图。到后来对究竟是应该在哪棵树上刻下地图这一点也弄不清楚了,无法肯定是移民们自己没有刻呢,还是那棵树本身也和他们一起失踪了。作这样的揣度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船员们在另外一棵树上发现刻有一句话,只可惜那句话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足以说明移民们是有时间和条件留下信息的。既然现在什么也找不到,那就有可能是留下之后又不见了。船员们在岛上各处搜索多日,后来又把搜寻范围扩大到邻近地区,也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最后只好带着这个不幸而又神秘的消息回国。于是这个岛便被称为失踪了的移民地。两个多世纪之后,有位美国音乐家把这段历史写成一部歌剧,并命名为《失踪了的移民地》,于是诺安克岛的神秘色彩在艺术之光照耀下就更迷人了。如今到北卡罗来那州海滨来度假的人们,从导游书刊上看到对诺克安岛的介绍之后,尽管它在海滨南部,离他们的来处(多半是北方那些工商业城市)更远,也无不绕道到岛上来看看。在岛上海滩的一角搁着一艘老式帆船,它是完全依照400年前运送那批失踪者来此的船只图纸制造的。船身状如新月,长20米,重50吨,船舱深3米,有3座桅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条船当然不大,可是把它放在陆地上之后,人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它的甲板,于是就显得很是高大威严。一切船具完好如新,透过无色的油漆可以看到光洁的木质船舷,似乎它刚刚完成自己的首航,把那些移民平安地送来了。这一片海滩也正是当年他们登陆的地方。
这条船附近有一所博物馆——几间木头小屋,里面陈列的是从那些失踪者的故乡收集来的他们同时代人的遗物。那几间小屋也是仿照那个时候的民居式样修建的。从陈列品中可以看到一些那时人们生活的情形:男人使役牛马耕种搬运,女人烧柴做饭,在木盆里洗衣;男人用盔甲和长矛去制服敌人或者使自己一现骑士风采,女人戴厚而大的头巾上教堂,穿有钢丝撑架的长裙赴宴会……一个来自东方的参观者对其中的某些画面并不感到陌生,因为相似的场景他曾经历过,似乎这些人离开现在并不太久。但是那盔甲和长矛实在可笑,他想起吉诃德先生来,这才感到他们去得实在太远了。
今天在诺安克岛上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场面,甚至连一点微小的遗迹也没有了。现在这个岛的港湾里不再有那种木帆船,只有漂亮的机动游艇;不再有以谦卑自律的女子和崇尚蛮勇的男人,如今的女人醉心于将自己的全部公之于众,男人则以财富为荣;简陋住屋已被精致的住宅和豪华的商店取代;泥泞小道变成了平坦的公路;发动机代替了牛马。从博物馆里走出来的人仿佛成了神话人物,他刚才喝了仙人的酒,走出灵山才知道400年已经过去。他看到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从前的许多梦想都已成为现实,也看到人类自身也起了很大变化;
他首先注意到女人的变化,从前他只能看到女人的面庞,现在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机会看到几乎是女人的全身。在震惊之余他突然想道:如果穿着风尚自古如是,那大卫王就不用偷看民妇洗澡,许多凡夫俗子也不会因害相思病而夭折了。想看就让你看个够,这是现代女子的处世哲学。结果呢,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意郎君就自己登门前来拜倒于迷你裙下。从前的女人也明白,美是她们征服男人的武器,也把征服男人视为生活的最高目的,可是她们却将这武器束之高阁,对那个目的更是讳莫如深。今天,女人以全副武装的姿态出现在竞技场上。她们的姿态就是无声的宣言:主张依靠天赋和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克敌制胜,显然,400年之后女人不仅变得比从前勇敢,而且还把古代的淳朴民风发扬光大了,这个认识使他兴奋不已。
可惜当他循着这个思路去观察男人时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什么代替了长矛?无声手枪!什么代替了铠甲?防弹背心!难道说如今的男人争斗已经摒弃了光明正大的方式,而是不声不响偷偷摸摸地干了?如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克敌,又能有什么限制不把它引进别的生活领域里去呢?如是以往,世上哪里还有信义?没有信义又哪里会有公正和太平?难怪都说世风不古,看来这世风的污染源就在男人身上。
想到这里他又坠入了迷惘。
中国谚语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上山去的人中兴许有武松,但是武松几千年才出一个。大多数人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外国也是这样。继第一批人失踪之后,仍旧陆续有移民来到诺安克岛。这些人在岛上定居下来,开垦种植,繁衍后代,逐步造成了今日的文明。如今在他们从前的村落旧址上修建了一所公园,由国家管理。园中保存着这些开拓者的遗物,园里还有一所露天歌剧院,每年夏天都在里面上演前面提到的歌剧。这些人文景观既提高了旅游者的兴趣,又使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起源和民俗增加了了解,真可说是寓教于乐。
还有一个伊丽莎白花园也是游人常去之处。花园占地不广,然而历史悠久,里面有许多名贵罕见的花木。五月正是花繁时节,万紫千红,芬芳沁脾。园中的花坛和花圃都用大理石修砌,雕琢精细造型美观,其间还有一些与花卉有关的神话人物雕像。花园的布局也别出一格,由围墙和绿篱分隔为许多庭院,类属相近的品种自成一个群落。参观者只需浏览一下说明标牌,便能识别它们的一些植物学特征,他们对这些植物的印象也就更深刻了。除此之外,这种布局还减少了游人相互间的干扰,使花园变得更幽静,参观者也更乐于在其中盘桓悠游。在园内的许多绿篱中有一处生长得特别高大,它上面开有几个圆拱形的门洞,就像是一座挂满了常春藤的城堡。许多人满怀好奇心走进门去,城内自然又是一片新的花海。
游完花园恰好就来到位于大门内一侧的花店门前。店中陈列的鲜花、盆花、种子、园艺书籍和图片琳琅满目。在花园中见过的东西这儿都有实物或资料出售,真是应有尽有,花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古老的花园异化为植物商城,花圃异化为展销橱窗,这是这个花园的创建者和今天的游客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也是诺安克岛今昔的变化。
乘车在诺安克岛上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海滨的一个小镇,小镇外边有一座码头,很多游艇停在那儿。码头上边有一家酒店,几级木板架成的台阶把游客领到它的门前,门外是一片阳台,阳台的周边一圈凌空的靠椅,椅背正好充作护栏。坐在上面远望了无遮拦,让人感到心舒目畅。这个别出心裁的营造法式使今天这个旅游者的心情立刻开朗起来!这正是他从前见过而又不常有机会见到的东西。在他的家乡,当人们听到称赞某家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常常撇着嘴说:“哼!白毛猪儿家家有!”可是提起这种栏杆靠椅时敢于这样说的人却不多。因为只是住在楼房里的富户人家才有这种东西。从前每次遇到时他都想上去坐一坐,可是常常不能如愿,今天倒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了。靠椅前面那张方桌,是一只大木桶支起来的,那是从前装啤酒的桶。如今有了不锈钢桶,落伍者就被遣送到发挥余热的场所来了。方桌的桌面由两块木板拼成,不上油漆,颜色已经变为苍白,年轮的花纹却十分清晰,如同层层水浪朝座客涌来。踏上这码头以后,他就注意到这地方用木材造东西的习惯和他的家乡很相似,即造成的东西不上油漆。架码头的圆木、木板、酒店的台阶、靠椅、方桌、酒桶都是如此。他对这种造物曾有好感,觉得它们朴实无华,和他所喜欢的某些庄稼汉一样,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值得信任。现在这种温馨情感又回到心上来了。从前在他的家乡,不上油漆的木材叫白木。那时候也有漆,不过是大漆,从外地来的。上大漆的活路复杂,而且大漆的气味能使某些人生漆疮,脸和头都会肿大溃破,很痛苦又很难看。因此普通人家只使用白木器物。这些年他很少回乡,看惯了上漆的木器,早已忘记了白木的模样,没想到今天在这海角天涯与它又相逢了。刚才他觉得故乡就在前面不远,那靠椅栏杆便是一条路标,如同路边上的一棵双杈柏树或是一口古代的深孔墓葬,指引他走向那座一正两横的黄土墙瓦房,现在他已经坐在家里了!眼前这张方桌正是旧物。那年轮花纹曾经被他比喻为小河里的水浪。当他凫水的时候,把胸膛抬高了,又用力拍下去,砰的一声响,一层浪就起来了。击浪是少年有勇气有力量的见证,这使他感到得意。他还记得,如果仔细看那桌面,便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单纯的白色,而是由浅黄和灰白两种交织在一起的颜色。那浅黄的地方正是年轮纹比较光滑的地方。他曾经注意到家里那些干活的男人的缠头布也是这种颜色,而且当桌面和缠头布二者都是新的时候,它们的颜色也相同,说不清是白或是浅黄,很悦目,完全没有灰色的沉闷。可惜时间老人不让漂亮的造物长存,总要把它们弄脏弄丑,桌面和缠头布本该落得和塘泥一般污黑,只是亏了家里有女人细心洗濯,才挣来这么个折中结局。那桌面便是纪念主妇德行的一块碑。
骤然间,具有这种质朴面貌的旧相识——条凳(搁在方桌四周的)、锅盖(方桌旁边就是灶头)、水桶、风车、门槛、大门一一来到他眼前。最后他看见了那张大床,床架上挂着的夏布蚊帐被两边的铜钩挑起,床是空的。那个同他一起睡在这张床上的老人,那个灰白眉毛长如寿星的老人曾经是这个白木世界的顶梁柱。是他挑着水桶在田坎上闪悠闪悠地走路;是他把风车摇得吱溜吱溜响;是他永远轻言细语地排解兄弟妯娌的纠纷;是他翻山越岭把家里做的土纸挑到远乡去卖;也是他凭着当家人的权威,决定把辛苦积攒起来的一点钱用来送侄儿上中学;最后又是他替侄儿挑着行李走了一整天路把侄儿送到学校。现在他也来到他身边了,一双大眼睛跟从前一样黑白分明,长长的鼻毛曾经被他讥笑为可以当毛笔用的,照老样子伸到嘴唇边上。他高兴得要笑出声来,以为真的又和那个老人聚在一起了。可惜他立刻觉察出来,眼前的老人和伴随在他周围的那些器物都是飘摇不定的,似乎它们不是实体,而是由一些跳动不停的空气分子凝聚而成,是他的一片诚心把它们从天外召来,只要他的意念稍一松懈,它们便立即飞散远去。他极愿和它们在一起度过更多的时间,所以凝神敛息地看着它们。当他的心灵之光聚焦在那个老人身上时,他甚至能看清楚他身上那件土布长衫的布缕(很粗的蓝线,洗得泛白了),他的麻鞋、他的短旱烟管和他不苟言笑的神气。他就站在那张方桌对面!他兴奋万分,立刻就喊一声“三爸!”可是那声音却被堵在胸膛里,想起老人已经不在人间,鼻腔发酸,眼圈儿也湿了。
那个老人活了93岁,无疾而终。无疾又为何能终呢?能够的。他是在以白薯果腹的季节里去世的,赶上那年白薯全无收成。于是没有病的人也只得上天堂去过日子了。同样是那片土地,同样是那群把式,同样是下雨天晴的年景,为什么竟然没有收成呢?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还有凤阳花鼓的唱词,哪里没有少年郎在模仿?难道人们连这样的常识也忘记了?竟然会坐以待毙?答案是简单的:在正值收获的时节,所有的劳动力都被派到山上去伐木生火炼钢。稻谷、杂粮、白薯、土豆就全烂在地里了。
他想起来,有一年出差到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就回去了一趟,
给老人捎去一瓶五粮液酒,当时这种酒还不算太贵,又留下一点钱。钱老人收下了,酒呢他要侄儿带走自己喝,他说他喝惯了烧酒,别的酒再好他也品尝不出味道,岂不是浪费。酒当然仍是被留下了,却是不知道他究竟喝了没有。一个心性如此的人在生死关头自然不会有本事去和别人争夺救命之物,这是他应有的结局!想到这里的时候,他非常痛心,不断责问自己:为什么那时没有给老人多寄一点钱去呢?老人从不向他提自己的困难,可他是能想象到的。他虽然也遇上了困难,却是离生死关头还远着呢!他低下头,不敢再向前方看,觉得无颜面对那个依稀仍在的人儿,惭愧万分。
突然想到人们将在死后重逢,恩怨是非将如何陈说?正在十分着急的时候,如同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仍旧坐在那家酒店的门前。
越过码头和那些游艇可以看到外边的海湾,土黄色的水面细浪如鳞,海湾对面的海岬上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在那里又看见了那艘古船的化身。原来他绕到那个古老的诺安克世界的对面来了。在海岬背后,大西洋像一条蓝色纱巾在地平线上飘拂,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浩渺神秘。他仿佛来到了历史舞台跟前。由近及远看到世界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他仿佛听到先民们在海湾那边高声呼喊:请别误会,我们可不是到这里来探险的,我们对探险毫无兴趣。我们更不是到这儿来欣赏大自然美景的,那种浪漫情调对我们是太奢侈了,我们只是为了活命。有的人因为家乡闹灾荒,土豆没有收成;有的人因为宗教信仰受到迫害,最后实在活不下去才冒险到这里来的,哪知道到了这儿还是未能逃过劫难,我们实在太不幸了!这呼声使他怦然心动,土豆也和白薯一样能够造成悲剧。那时中国凤阳的女儿们在遇到荒年活不下去之时,就身背着花鼓走四方。毕竟神州地广人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卖唱也能活命,“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老祖先早已做出先例。只可惜400年过去以后地球上不再有一块新大陆任人自由进入,于是没有白薯就只能坐以待毙。在那远方的水连天景色正好象征着世界的未来,若虚若实,不知是一碧万顷或是惊涛骇浪。大西洋不会改变,自然界不会改变,它们是守恒的。变化难测者是人类。他们创造了文明,他们也可能毁灭文明乃至毁灭他们自身。这种感慨并非无病呻吟,是刚才比较400年前后人的变化问题引起来的,他的眼前一片迷茫。
几只海鸥从头上飞过,刺耳的叫声把他又唤回现实之中。
阳台的一角放着一只花盆,满盆的杂色小花朵开得正鲜艳。他觉得那花儿十分眼熟,便径直走到跟前去,细看一会儿之后不禁失声说道:就是她呀!复瓣的花,红色的茎,肉芽状的叶,每朵花都顶在茎尖上。不错!就是她!唉!你这卑微的死不了花儿怎么也会来到这万里之外的异乡?我又怎么会有缘和你在此相遇?他又陷入回忆中了。
狭窄的阳台刚好放得下那个破搪瓷面盆,每天清晨那儿能见着一会儿阳光。邻居有这种花,说是一切花卉当中最容易养的了。从他那里讨了几截掐断的茎来插在那个面盆里,那面盆刚好是漏的,就无须买花盆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子过得省俭,不论从事体力劳动者或是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上班穿有补丁的衣服都是常事,棉布衣服自己补一补就算了,要补毛料衣服一则难以找到相同的料子,二则大多数人家都没有缝纫机,就是补了,线缝得也不够整齐,只能求助专门的补衣店。那些年在北京最漂亮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上便有一家这样的商店。一条哔叽裤子补上三个大补丁工料费是两元钱,而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是56元。因为人人都靠工资生活,能制备毛料衣装者实在不多。不过谁如果有机会去外国出差一趟便能领到500元制装费。用这笔钱足以购置两套衣服和一袭大衣以及衣箱鞋袜等物,衣装必须是毛料的,以免在外有失国体。许多年之后这家商店更名为凤凰女子时装商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里一直是时髦女性驻足之地。从最保守一跃而为最激进。九州生气恃风雷,这风雷是在人心里聚积着,一旦迸发出来那景象是够叫人开眼的。
那花儿竟是活了。开始两天她一直躺在泥上,连根都没有,怎么能活呢?他心里犯愁。可是以后她就慢慢挺起身子来。又过了不多几天就顶起了骨朵儿。真是奇迹,一家人非常高兴,都用钦佩的眼光瞧他,他感到惭愧,因为他只是在碰运气,不过他也很高兴。
第一朵开的花是白色的,以后又有了紫红和杏黄的。虽然一共只有这三种颜色,却因发的杈儿多,开的花也多,所以绚烂悦目。花朵虽小,但是层次丰富,鲜艳含蓄,耐人玩味。这小花儿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品性,在快要凋谢前,她的花瓣就一片一片地卷裹起来,再干缩成一个小团,最后悄然入土,真的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可惜每朵花只有一天的生命。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年轻人清早醒来,冷水擦把脸,急匆匆吃过早饭就上班去了,下班后又要开会。有个主持开会的人曾对大家说:国民党税多,我们的会多,开会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一种武器,只有我们才会使用这种武器,大家要做好开会的准备。骑自行车的人每天上班前,都要检查一下车灯是否被淘气的儿子摘下玩去了,免得晚上回来摸黑。他不骑车,对路上缺少照明也没什么抱怨。却是在回家时有机会看到,不论春夏秋冬,那几座灯火通明的住宅楼远远耸立在黑暗的地平线上,像神话中的仙人宫殿一般奇妙辉煌。
星期天是洗衣服的日子,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洗衣粉。一个脚盆、一块搓板、一条肥皂和一只小板凳便是全部劳动资料,劳动力自然就是他这个有力气的男人了。当时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双职工家庭里,丈夫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如果问世界上何时何地有过男女真正平等的地方,就可以回答说: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在中国,搞婚外恋的人一旦被揭发出来,轻则小会检讨,大会批判,重则受到处分。这种人虽然还保留着人民的资格,但是已经声名狼藉,大家对他怀着戒心,异性更不敢和他接近,他的日子大约比今天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更不好过。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就会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忝列“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中的倒数第二),再被送到专政机关去改造。在这样的社会里,妻子就成了家里的北斗星了。天上众星朝北斗,这句话也许还可以斟酌,但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这样两句话恐怕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女人想小孩,男人想小孩他妈。住医院或是出差的男子常常这么互相嘲笑以示彼此彼此。归心似箭,靶上的红心自然就是女人的朱唇了。不过那时女人的嘴唇未必比男人更醒目,因为在公开场合没有人擦口红,在工厂或是大学的集体宿舍里有擦的,不过外出时就擦掉了,擦掉时不仅赔了口红,还有一串泪珠儿也一起赔掉了。
终于有那么一天,年轻人在家里觉得空闲,他看到阳台的门开着,面盆中的花儿光彩夺目,感到惊讶不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可爱的东西存在。那个扎着蜻蜓髻的小女孩蹲在花旁边,开心地笑着,她仰起脸儿来向屋里看。她的腮靠在花朵上。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心解冻了,温暖的风正在他心头吹过,这风是从小女孩那里来的。盆中的花隐退到一旁去了,它们是星星,现在月亮出来了,年轻人的心就像星空一样温柔,小女孩的脸儿便如满月那般光明,他满心欢喜与她同在,她是他的果实,她是他的未来;她是花,他是那着花的树;他对她的爱和他的脉搏一起跳动着,一下接一下牵动他的心。他感到他这一片深情像空气一样包围着她,护持着她,只是为了她的存在他才存在,他的意识澄明如同夕照中的天空,一切劳碌烦恼都化解于无形了。
扎蜻蜓髻的小女孩向屋子里看什么呢?她又是为了什么笑得那样甜呢?是因为她看见了那个年轻人;看见他注意到她在花盆旁边玩得高兴;是他的目光或是嘴角透露了这个信息?或是对她说了什么怜爱的话呢?他记不起来了。但是小女孩是为了他才那么高兴这一点他记得却是很清楚的。因为他知道:在小女孩的心目中,他脸上的笑容就像那盆中开的花儿一样稀罕。
当年的那个年轻人此时感到非常幸福,春风又吹过他的心田。自己还是从前的自己,家还是从前的家,他现在回到了那儿,和亲人们又聚在一起了。几十年追求和沉迷的一切他都愿意抛舍来换得这个重逢。他本是冰山上的雪,偶堕平川。千回百折,有幸化作浮云,飘回故乡,变成雨点儿又落到旧地上了。这儿才有晴朗的天空,这儿才有纯洁的知己,这儿才有永世的安宁,他再也不要离开了。
可惜这一丝幸福感情也像浮云一样不久就飘走了,他仍旧站在异乡小酒店的门前,他心头的明月——那个小女孩如今已没有福分陪伴花儿玩耍,蜻蜓早已从她头上飞走,地上的花儿也再不能靠着她的腮边了。他想起来,她在登机通道之外向他挥手,她笑着,那笑容依旧很甜,依旧让他感到温馨,他们相对站立了好一会儿,他觉得该走了。便转身推着行李挤进人流中,立刻就想起机票和护照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拿出来看一下,二者都在,于是便为没有出什么麻烦感到庆幸,女儿的形象就忘记了。现在他感到惆怅莫名,这岂不说明:他对她的爱和从前相比是淡了!这是为什么?是她的笑靥蒙上了生活的尘埃?或是他的心泉已经枯竭?难道真是好景不再来吗?
以这句话为主题的那首流行歌曲,他年轻时就听过,可是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以后有好多年听不到它。又过了好多年,当磁带录音机被带进国内以后,他有机会又听到那支歌,觉得优美缠绵,很受感动。放录音机的朋友把音量调到最低,把门窗关上,还嘱咐他不要告诉旁人。那时何曾想到,如今在大街上就可听到这支歌呢!是呀!岁月如流,岁月还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裹挟而去。有的形体虽还存在,神韵却已面目全非。
刚才停在路边一朵小白花上的那只大蝴蝶,橘黄色翅膀上的花纹极像重墨山水,寥寥几笔粗犷有侠气,却是一只翅膀缺掉了指甲那么大的一角。是受了鸟儿的攻击,还是在争夺爱情时负的伤?谁说人间迢迢相思路,不如天上比翼飞呢?人间天上都是风云瞬变。花落自有花开日,这是生命主宰者的胸怀。而一朵花、一个人或是世间任何一个生灵,它所能见到的就只有好景不再来了,这是何等令人惆怅。然而在惆怅之余却又明白,原来这惆怅之情正是为了过去的幸福而生;正是因思念过去的知音而起。这岂不又是说,好景虽逝旧情仍存?
问世间情为何物?情即是爱;就是付出过和得到过的爱;就是梦醒时分的笑颜和眼泪;人生如梦,当你最后离去之日,也就是大梦终觉之时,你能从这个世界上带走的东西,便只有它了。
诺安克岛的确是个神秘的地方,它在今天也还有这种魅力。借助遗物追溯过去自然不足为奇,然而它却能使人在红尘中蓦然回首,重睹昔日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