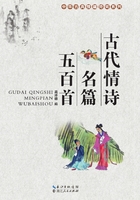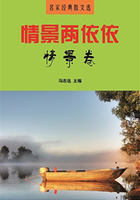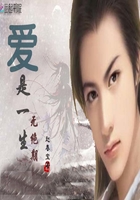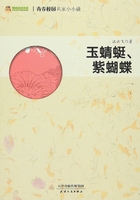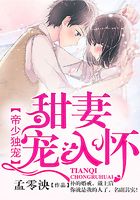耕夫
蒋九贞先生早期小说作品的又一个结集《乡村记忆》近期由大众文艺制版社出版了,笔者首先表示祝贺。
《乡村记忆》所选33篇作品,演绎的故事无不发生在微山湖西畔(俗称“二湖涯”),闭目静思,微湖风物纷至沓来:那芳草萋萋的滩涂地,那雄浑蜿蜒的苏北大堤,那纵横交错的沟渠,那河汊边的小码头,以及那火红的高粱,金黄的谷地,一望无垠的水稻田……真真切切都是此地风物。小说中那栩栩如生的人物,既淳厚朴实又透着机警干练,既豪侠仗义又私心颇重,既粗犷彪悍又不失温情,的的确确是此地人的模样;他们那质朴、硬正,率直、幽默而又土得掉渣的话语,实实在在是此地的乡音。
读《乡村记忆》,就像置身微山湖畔乡村的土场上,倾听乡亲们在讲述本乡本土的轶闻旧事,感到无比亲切、真实;细品滋味,就像湖边庄户人。爵菱角米儿、啃毛地梨儿那样香脆甜心,余味无穷。愚以为,文学作品的乡土气息愈浓烈,地方特色愈鲜明,就愈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愈能够产生震撼人心的感染力。试看诸多名家笔下的典型环境——沈从文的湘西山水,肖红的呼兰河,孙犁的白洋淀,刘绍棠的津门古运河,浩然的芳草地……哪一个不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村记忆》是一幅乡村风俗画,是发自微山畔的时代新声,“二湖涯”无疑是蒋先生笔下的典型环境。
其中的差不多30篇微篇小说,大都曾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报刊上,其篇幅短小,取材细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却以小指大,见微知著,对那个时期的乡村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扫描,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大潮初起时期的乡村社会风貌。作者高屋建瓴,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饱蘸激情的笔触颂扬了党的农村体制改革政策,反映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呼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讴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新风尚,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党的农村体制改革政策,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神州大地。广大农民锐敏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小说《听房》中的李木匠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这一回他知道世道真的变了,北京的官府已变了样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统治法,天变道就变,天不变道就不变,如今的天晴朗了,没有人再敢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怕啥?”这正是当时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
改革让农民富起来了,改革使家清嫂终于了却十几年的心愿,买上了缝纫机,走得起娘家(《喜鹊喳喳》)。改革使因贫穷而咫尺天涯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河汊上有个小码头》)。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啥,真叫十年河东转河西啊!”“四五年前还穷得叮当的”“长手爪”今天竟“肥得淌油”,过去的漏斗户,如今变成了村里首富(《茶香正浓时》)。总之,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洒遍了村村落落,家家户户,农民真的富起来了!
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广大农民的精神境界也大大提高了。如在城里正挣着大钱,心里想着队里有一大堆农具急待修理,就再也呆不下去了的“李木匠”(《听房》);从穷日子过来的人,因而,拒绝把猪秧子卖给猪贩儿,却主动赊给特困户老田叔的花芳嫂(《花芳嫂卖猪》;自动填界沟让宅基地促成两家言归于好的“二叔”(《填沟》;以及主动帮助职工家属收麦的众乡亲们(《收麦》)……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正是两个文明建设在乡村结下的丰硕成果。
作者在小说《请客》中写道:“是的,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大变化,人,也在变化着呀!”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涤荡着角角落落的污泥浊水。一些浑身毛病的“下梢子货”,也除污去垢,脱胎换骨,成了社会主义新人。小说中的冯化雨就是一个典型的见证。过去“队空社员穷”,“他家空荡荡,就连老鼠都不去他家打洞”,“没法子生活,他就学着偷”被人称作“长手爪”。跟他搁邻居“连睡觉也要睁只眼”,农村改革之后,他家一下子发了起来,成了村里的首富。彻底改掉了“好偷”的坏毛病,使得和他家地连边的刘希发老汉自动拆掉专门防他的看庄稼棚(《刘希发拆棚》)。经济地位提高了,他也能挺起腰杆做人了,在干部面前不卑不亢,还大大将了专等着他请吃的村支书吴其仁一军(《茶香正浓时》)。他富了不忘本不“烧包”,成天“为乡亲们操心费力”,成了乡村致富的带队人“新时期的先进分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化雨入党》。行文至此,作者挥毫盛赞:“好!到底是共产党,你支书不赞成,照样通得过,这是党心,民心所向啊!”
《乡村记忆》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农村体制改革后,干部工作作风发生了根本转变(《喇叭》)。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人际关系、社会风尚相应发生的可喜变化。微型小说于细微处见精神,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于群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姑嫂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简短而又生动的故事。在这里,过去盛行于世的“人整人、人防人、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人人互相理解、互相容让、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社会新风尚。《乡村记亿》全面深刻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的社会面貌,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就写作技巧、表现手法而言,《乡村己忆》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微型小说篇幅极短,容量有限,写作难度较大,这就要求作者剪裁得当,高度浓缩素材,少描摹,忌铺陈,擅用白描手法,抓住“题眼”寥寥数笔即勾勒出人物形象,提示出中心思想;语言力求简洁明快而又含蓄蕴藉,以少胜多,意在言外。蒋先生正是这方面的高手。《相亲》是一篇极富戏剧性的微型小说。说的是农村姑娘小柳、小桃陪伴女友小杏去相亲的故事。作者匠心独运,选取了非常特殊的环境(男方工作的开票口),采用了非同寻常的相亲方式(托男方“走后门”以测试其人的思想),最后含蓄地暗示了圆满的结局,其构思精妙,别具一格,不落窠臼。作者紧紧抓住双方隔窗相望的那一刹那,以短促精绝的对话,传神的动作以及不断变化着的表情神态,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歌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想、新风尚。作者惜墨如金,通篇只不过短短的五六百字,便完成了一篇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性强,语言精美的上乘佳作。
《乡村记忆》收入的两篇中篇小说(《神秘谷地》和《空屋前传》),较之前述微短小说不仅体裁不同,而且所反映的社会环境、时代风貌也迥然有异,其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大相径庭。《空屋前传》写的是微山湖西畔古镇“杂货西施”花妮儿坎坷悲惨的一生。这是一个古朴凄婉的故事:花妮儿生得既娇艳冷峻又妩媚迷人,而且颇为能干,镇上的男人们无不为之倾倒而垂涎三尺,她却一概不屑一顾,断然拒之。后来,一个军阀部下的小军官强暴了她,她竟然由此产生了畸形的恋情,甘心其霸占,任其玩弄。那个小军官最终遗弃了她,一去杳若黄鹤,她却情有独钟,矢志不移,天天痴迷地念着他,盼着他,做着花好月圆的美梦。后来,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本人也因相思成疾,病体支离,奄奄一息。故事的结局是“家败人散”,只有那间空屋在风雨飘摇之中发出令人心悸的悲音。作者讲述这个故事,好似乡下老人“摆龙门”,娓娓道来,扣人心弦。故事结束了,犹自空屋传响,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神秘谷地》写的是一个出生于微山湖畔的乡村少年张开心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张开心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他朴实、善良、清纯、重亲情,有正义感,而且才华横溢;另一方面,他幼稚、不谙世事、执拗还有点神经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文革”大风暴使得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关键时刻他总是优柔寡断,无所适从,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他怀着赤诚之心及“革命派”的狂热性,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南下北上“大串连”,还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但是最终还是屈从于父母的压力,离开了“斗争”的旋涡,回到家中,自我幽闭起来;他情窦初开,向往美好的爱情,追求婚姻自主,热恋着同学姚红梅,为她做着旖旎的梦,但最终还是做了亲情的俘虏,违心地与素不相识的农家女小荣订了婚;他心怀正义,憎恶邪恶,但又不得不与乡村势力虚与委蛇,以求自保。然而,“是祸躲不过”,他终于跌入陷阱,身遭灭顶之灾,他拼命反抗,挣扎也难逃厄运,惨遭围追堵截,几乎命丧谷地。张开心不是完美的“高大全”,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文革小丑”,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乡村少年。作者通过主人公张开心的所见所闻,身历心感,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那个非常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而揭露了“文革”时期“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丑恶现实,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神秘谷地》在表现手法上也别开生面,另辟蹊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作者将“进行时”的正序叙述与“过去时”的回忆(或插入“笔记”补叙)交替进行,在时空的转换中交待背景,充实故事内容,丰满人物形象。同时,又将眼前的景物描写、呓语般的内心独白和梦境中的幻觉,互相交织,互相渗透,错综纷繁,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作者运笔如风,酣畅淋漓,犹如“风到水上自然成文”,又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迂迥九曲,跌宕起伏,妙趣横生,读来令人击节三叹。
笔者与蒋九贞先生忝居同乡,又同为郑集中学校友,故而对于先生的人生经历略有所闻。九贞早年聪颖过人,尤为酷爱文艺,醉心经史;小学时期,即博览中外名著;进人中学后,便在报刊上发表诗文;七十年代跻身文坛,有大量文学作品问世,被誉为“实力派作家”。其小说格调高远,情节感人,语言凝炼、生动,文采斐然,艺术手法精妙,乡土气息浓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读者热爱。近年来,九贞致力于文艺批评和地方文史研究,卓然有成,著述颇丰。
《乡村记忆》的出版,实属作家蒋九贞先生的“朝花夕拾”,以展现其从事文艺工作的早期历程。诚如作者所曾说过的:“对以前的写作生涯作一个小结,目的在于争取以后有新的收获。”为此,我祝贺蒋九贞先生,并期待他“重返文坛”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飨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