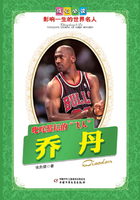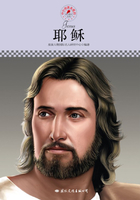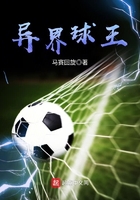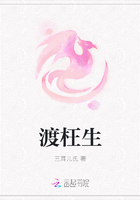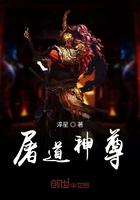如果说,在20世纪前期,人间佛教理念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建构与倡导阶段,那么,自20世纪后期至今,这一堪与西方宗教改革对社会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之推动相比的汉传佛教教理革新成果,已进入大规模实践领域。从世界宗教史的演化看,佛教革新是东方世界走向现代化,东方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成果在南传佛教区域与欧美表现为“参与佛教”,[2]在汉传佛教及华人社会中的主要体现就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理论的倡导者与深化者分别是太虚法师与印顺法师,这已被学术界与佛教界所公认。星云法师则是自觉实践人间佛教理论的最早成功者。在星云之前,太虚本人及其众多的追随者、弟子们也曾将理论付诸实践,但如太虚本人所坦认,他生前推动的佛教革新千头万绪,可试者如方案制订修改、小范围试点、群众运动、创建组织、建构理论,国际国内、教内教外,他已无不尽力。但“驯至今日,乃百千万亿中尚无一丝一毫成效可观也!”[3]在其追随者及弟子中有些人有一方面的个人成就,如法舫、法尊法师等,对他们来说,时代尚未提供社会实践方面成功的条件;更多的弟子们如太虚曾寄予希望的芝峰等,则首先是自己放弃,而后被严酷的历史所汰洗……当然,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大陆提倡人间佛教,证严法师、圣严法师的实践也都在70~90年代已展开。但星云领导佛光山的建设早在60年代已启动,70年代即取得了初步成功。所以说,星云是最早将人间佛教理念推向大规模成功的实践家并不夸张。
当下,推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深入展开的主要阻力,还在于有人误以为如其推广,必与固守明清佛教模式的寺院争地盘、争信众、争人才。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佛教“新派”与保守派之间还免不了这些争夺的话,那么,星云法师其实是为汉传佛教,为中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与复兴打开无限广阔空间的开拓者。
——佛光山虽然也接纳已维持不下去的旧寺院,但其90%以上的道场都是新建的,海外还有200多所,这恰在以前很少有佛教的区域,对固守明清佛教模式者几乎难以想象,但汉传佛教的许多优良道风却在这些道场里得以持守发扬。
——以往两岸社会对佛教的普遍认知大抵如李新桃(即慈庄法师)所说“佛教是阿公阿婆的迷信”[4],出家是因为在世俗生活中碰到挫折后才看破红尘,而寺院则是厌离社会避世修行的场所。如今有些出家人与佛教徒也仍然如此,但人间佛教的信众再也不被限于阿公阿婆,郭文般教授依据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社会变迁调查计划(1994~2004)”三波统计资料分析指出,在台湾与城市化进程相应,取代民间信仰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已是佛教。在佛教徒中,相对比重最高的是企业主和专业管理人员。这正是韦伯所谓“现代的合理的企业经营的体现者阶层”[5]。在大陆,佛教信众也开始涵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次。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许多人对佛教心存好感,过去他们来到寺院往往没人理,了解寺院内情后更失望,有的人就从此远离佛教。但当他们来到真正实践人间佛教的道场,获得的不但是帮助(方便),而且是希望、欢喜、信心。佛光山也包容曾经保守的佛教徒,但这些源源不断的新信众才是其基石。
——佛光山也吸引各寺院人才,但佛光山系统的主体、国际佛光会的多数会员以及构成佛光山骨干队伍的济济人才,几乎都是星云及其高徒一手培养的。其他人间佛教团体、道场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新人才,有大学毕业文凭,取得硕、博士学位的不计其数。
——人间佛教开辟的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大规模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遍布全球的佛教传播事业、深入社会的社区丰富多彩的活动、化解现代生活带来的烦恼的心灵指引等,相对于明清佛教模式的局限而言,都是新领域。这些,都与传统社会给佛教划定的疆域迥然有别。如星云亲口所说:
我还创造了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稚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纪念品、第一次出现万字项链……[6]
总有人问,佛光山事业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大?
首先,这来自星云的大愿心。星云发过多次大愿,最痛切的是在1949年夏天,由于某些人对大陆去的僧人的歧视,他饿了几天,好不容易才吃上稀饭,于是他暗暗发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不管什么身份、地位,还是有钱没钱,也不管什么时间,一定让来的人吃饱吃好。”[7]这就是菩萨发心!凡夫想的只是自己,菩萨想的是推己及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差别就在这一点点……当然,大愿心也来自大时代,不光是星云经历了抗战的艰难与胜利、内战与流亡两次天地翻覆,我们也正处于历史罕见的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大愿心也来自大秉承,星云深深得益于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当然,传统的负面也在发酵,关键就在于抉择。大愿心还来自于大召唤,对当今与未来社会的需要,你有洞察吗?打算有多少担当?
其次,有愿必行是星云的性格。然而大愿能否实现?这与星云的大器宇分不开,林清玄称之为“浩瀚”。有了大器宇,一能学,因为容量大。星云说,他自小并不聪明,他的丰富知识与逗机说法技巧都来自学、琢磨、练。二能忍,他有多篇心得专讲佛教“忍”的哲学,如忍辱负重、以退为进、“无生法忍”,等等。三能容,大包容就是虚己帮人,使人感恩不已。星云因此有大福报,即凝聚众心,依靠千百万人的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大包容还是笑对世界……
最后,大愿的实现在根本上依靠大智慧。把握了这一大智慧,就能化导万事与人心。所谓化,一指转化。曾经有人问星云,将一些很难化解的恩怨摆平妥帖,有什么秘诀?星云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向来觉得‘排难解纷非等闲之事’,所以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甚至为了让双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我不惜牺牲己利,以谋求大家的满意。”[8]这样把对立面转化为祥和,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其第二义,即弘化,但星云不仅仅是所谓通俗弘法,正如印顺的学养重在史学,星云重在文学,佛学则是他们的共同基点,把人间佛教解读为现代形式的通俗弘法更是褊狭理解。星云的大智慧还表现在其第三义摄化,如摄化民间信仰等多方面。这就牵涉“导”,所谓“导”,不仅解决当下存在的问题,而且指出未来的方向;不仅授鱼,而且授渔;不但是摄化也是摄导,需要大智慧,否则就会停留在低层次信仰上甚至退化;而且对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或转折的关键点而言,如升学、就业、婚姻、染病等,都需超越狭隘功利的大智慧引导,否则不是迷失,就是颠倒,如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颠倒、人我关系颠倒,造成人生路上的跌倒。凡开拓者,走的都非前人走惯的熟路,所以往往路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这一切,更需大智慧导航。所以一部近现代中华佛教史,也是几度濒临毁灭,而在沉沉黑暗中有几支慧炬引导新生的历史。在这几支慧炬中,与印顺导师的门下倾向于与传统决裂不同,星云大师的大智慧引导则更多地表现在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方面,表现在以情感之、以义结之、以慧摄之。这与不少领域至今仍是新瓶装陈酒不同,佛光山体现出的可用旧瓶新酒比喻,亦即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那么,大智慧来自哪里呢?
这一大智慧来自对佛法坚定不移的信仰,有信仰才能坚持,凡圣差别用星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遇到巨大困难也永不退票;就是勇于担当,挖掘每个人都有的但可能自己也觉察不到的潜力的强大力量,而许多事业的成功奥秘就在于坚持。
这一大智慧也来自对佛法中道的深刻领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所谓中道,是中观的般若智慧,有了这种智慧,遇到了事情就懂得事待理成,懂得把握其中的原则。遇到一切果,就知道果从因生,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不会随便怨天尤人,会去追查原因。“有”的现象,是由于“空”理,“不空”就什么都没有了。……“空”中才能生妙“有”。人间佛教是过着一种有物质,也有精神的生活,物质、精神的生活是同等的重要。[9]
这一大智慧还来自对现代人的心灵、现代人的宗教需求的洞察。星云对佛光山徒众提出的四个当下“给人”的要求,恰恰就是对传统社会对佛教误解的翻转,针对民众接触佛教时的畏惧心理与民俗信仰,信心是所谓空的翻转,欢喜是苦的翻转,希望是对现世绝望的翻转,方便是求神的翻转。方广锠教授认为这些在根本上完全契合佛理。
这一大智慧更来自修行定力深契内心,即使正在忙于别的事情,看似无心,其实星云已一下就认准旁人禀报的问题关键,说几个字就给出解决方法。
星云最大的智慧是靠良好的制度培养人、引导人,放手任用年青一代。2013年3月12日,第九任住持晋山升座法会暨临济宗第49代传法大典在佛光山举行,遵循着制度,心培法师将住持重任交给了心保法师,同时有五位法师任副住持,即慧传、慧昭、慧伦、慧峰、慧开,[10]他们都年富力强。这样星云就不用亲自操心小事,保证了对大问题、大方向的关注。
至于所有这些究竟如何?不妨随着作者笔触所到之处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