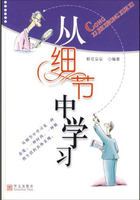浪漫樱花
2000级·周游
我现在常常做梦,梦到一片雪地,我在堆雪人,没有戴手套,双手冻得通红时,我就把僵硬的手指放在嘴里用力咬,一直到疼痛的感觉袭来,便觉得很温暖。
那时一直听齐秦的歌,他唱着,“梦太投入,痛太清楚,就让眼泪浇灌我们的幸福,因为眼泪也有温度。”我的眼泪是零度,冰水混合物。我酷爱在雪天流泪的感觉。也许一切仅仅因为我出生在雪天。冬季里唯一的暖日照亮了我的笑脸,随之而来的寒流击碎了一切美满和幸福。
我不想说我很孤独。孤独这个词同它本身一样只适合自己品尝,只是没有人和我说话。傍晚,我一个人在操场上不停地走。偶尔会有跑步的人把我赶出跑道。我没有学会奔跑这个复杂的动作,无论是奔向明天,抑或往昔。
我用一把古老的塔罗牌给自己算命。我的命牌是隐士。在塔楼上,一个穿黑衣的人用帽子遮住脸颊,手里举着昏黄的蜡烛,他低着头。我的命牌显示,我总是独自寻找生命的真相。我觉得我是个很乏味的人。
那一年樱花开得很美,学校的围墙边总是香盈盈的。在樱花盛开的某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
盛开的花朵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那天,我脱了鞋赤脚爬上了围墙,明亮的阳光让人目眩。我坐在围墙上,晃悠着双腿,眯着眼看太阳,嗅樱花的香气。风也是懒散的,我的脸上落下斑驳晃动的树影。我闭了眼,感受那些晃动的光斑。在想象中为它们涂上色彩,鹅黄或者湖绿。慢慢地流泪,感动于那一刻的云淡风轻。
樱花树长得很高大,我摇摇晃晃地站在了围墙上,想抓住一片樱花瓣。就在那时,我听到一声惊叫,一个男孩子仰着脸,焦急地看我。我想那时我的姿势一定古怪并且危险,像一只想飞的鸟。后来他宣称是他救了我,我还依稀记得他额头上因为焦急而渗出的汗珠,颗颗饱满。那个小男孩子。
他说我特立独行。其实这也是我无法把握的事。有时我会安静地坐在操场边,看他踢足球,当成享受。他毫不吝惜地挥洒他的汗水。踢完球,他笑着向我跑来,跳荡的头发里藏着阳光热朗的温度。我有时微笑,递给他一瓶水;有时递给他一瓶水,然后微笑。
他叫我老姐。
他说不懂我为什么会不快乐。
他讲他小时候,冬天教室里搭一个取暖的火炉,男孩子们带了土豆来,埋在炉子里烤,嗤嗤地响,还冒着烟。烤好了,大伙儿抢着吃,吃得满手满脸的黑灰,然后被老师骂到门外罚站。
我说我总是绕着花坛一圈圈地走。起点就是终点,轮回一周又回到原地,像是一只蒙眼的小毛驴。下雪的时候就看雪花,看出三维的效果,仿佛雪花是从地里钻出来的。
他响亮地笑,呵呵地,说老姐,真有意思。然后深深地看我一眼,低了头,神情里忽然添了一丝落寞,不讲话了。我的心底似乎有一块淤青在隐隐作痛,就什么也不说了。
我是个冷然而安静的人。语言是我驾驭不了的东西。世上有无数消散了的海誓山盟,守住一掬心泉,开始变得艰难。但是耳朵里经常灌满各种声音。高昂激越的,舒缓神秘的,不停地吟唱。
没有音乐的时候,我会虚脱,失去方向。
那个叫我老姐的小男孩子是君若。那天他站在围墙上,伸长手臂,为我摘那支樱花,有点儿摇摇欲坠的味道,我的心里惶惑不安。他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脸色绯红,稚气未脱,十足的小男孩样。清风拂来,樱花娇嫩的粉白花瓣微微颤抖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叫我老姐。
后来问他,他给我的理由是,那天我的眼睛里包含着无限的宽容和忧伤。其实我是个找不到位置的人,常常手足无措。我总是不知道如何扮演适合我的角色,比如一个学生。我自身的存在就像一道难题,突兀怪异,毫无主张。为了我,数学老师愁眉不展。他看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医生看一个濒死的病人,连连叹气,我就更加沉默。
君若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像身上的一个小痒处,又像生命里潜伏的编码。我对他说:“我想要一对翅膀。”他说:“是透明的吗?”我点头,“对,我想要一对透明的翅膀,我一直在等待这个奇迹。”
冬天第一场大雪的时候,我拉着他去堆雪人,没有戴手套,手冻得通红,他大呼小叫地说:“老姐,你又丢三落四的,你的手都要冻掉了,快戴我的手套——”雪人堆得像模像样,他还找了两个松塔当眼睛,然后说它像极了我。第二天,我去看雪人。阳光下,它显得笨拙臃肿,而且正在缓慢地消失。我解下围脖,给它围上。鲜红的围脖一直飘荡在风里,注视着我离开。我不敢想象雪人化了的样子,只能用围脖来陪葬。我似乎没哭。第三天,君若找到我,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围脖给我围上,他一字一顿地说:“珍爱自己,别做傻事。”他的眼里似乎有种莫名的愤怒,这种愤怒让我觉得陌生。我发现他的下巴上已经长出了细小的胡须,他已经不是我的那个上树、摘花、踢足球、堆雪人的小男孩子了。现在这个人告诫我,你要珍爱自己。
许多我刻意忽略的细节在黑色的记忆里浮现。比如他的品学兼优和远大理想。他的笑声响亮的、爽朗的、肆无忌惮的;他的眼神清润的、忧伤的、夹杂着疼痛的;他叫我老姐时的依恋,他软软的口气,他说我触摸不到你,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这个人告诫我,你要珍爱自己。
一夜之间,面目全非。
我忘了人总是要长大的。我不可能一辈子把他当成小孩子。他开始不原谅我的恣意任性,他想纠正我,回到他那个轨道。
有时心里涌动着的倾诉的欲望,让我在暗夜里寻找天堂的位置,我想用那对透明的翅膀飞翔,在那棵生长着欲望的树上写下我的名字。我不知道如何把握我和君若的距离,只能一退再退。语言无法拯救的黑洞里,沉默是御寒的外衣。如果一颗心抵达不了另一颗心,是不是也就没有了伤痛?只是,君若,你还能读懂我的眼睛吗?
我的头发很长了,我把它们松松地挽了两个麻花辫,搭在肩头。开始听各种奇怪的歌,比约克的声音空灵盈动,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可以给我安慰和力量。还有一直钟爱的王菲,她唱:“你打错了,我不是你的那个什么。”
独自在校园里行走,再看见君若的时候,已经度过了一个寒假。过年时,他打电话拜年,依旧清新的声音,说:“新年快乐。”“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停了十几秒,就各自挂了。
他看见我不再张扬不羁,不再拍我的右肩,出现在我左肩。我不想知道他的不快乐是否和我有关。某种程度上,我很自私,我不想被他唤醒,不想。许多问题就这样搁浅了、遮蔽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生活又像水一样继续流淌。可是世界上少了一个叫我老姐的人。我失去他了。有君若此。
你知道吗?君若,樱花的花瓣放在嘴里咀嚼是很苦很苦的。我怀念和你在一起的那些银色日子。
可是我无能为力。
樱花再次怒放的时候,我收到了君若的信。
老姐:
很想这样叫你老姐,可是我忽然发觉我叫不出口。告诉我,我真的曾经走进你的生活吗?那天看见你鲜红的围脖孤零零地围在雪人身上,而你萧瑟地走在风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我们可以再堆一个雪人的,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固执并且决绝呢?
不要掩饰你的无助和寂寞了,我想看到你的真性情,可你还是仓皇地逃走了。
老姐,老姐。
一片樱花瓣从他的信里飘落。我知道这封信他写得有多艰难,可我同样知道,我多么不愿看见他眼里纠缠的疼痛和哀伤。那些银色日子树叶一样飘落了,它们会在时间的荒原里熠熠生辉。君若是懂我的人,可我是会给别人带来阴影的人。我只是想在下雪的时候,找个人陪我堆雪人。我和君若在茫茫人海里互相寻找,相识相知,又走散了。仅此而已。
夜里失眠的时候,我趴在窗边张望黑色的星空。我看见一树一树的樱花绚烂地开放,瞬间,落英缤纷;我听见君若轻轻地呼唤着“老姐”。我含泪低头,看见手心里有一瓣小小的、颤抖的樱花。
点评:梦里落花知多少?一瓣樱花,不止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更有一种温馨而又略带感伤的情愫。人生难得相知,又难免离别。也许,永恒总是在我们的心底悄然留存,偶然碰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忧怨与遗憾。这也是成长必经的路途。(殷晶波评)
孩子的寓言
2001级·刘美多
心灵,你筑墙自囚,而你的那些仆人们劳碌地奴役自己。但整个世界和无限的空间都是为这孩子,为这新生而创造的。“那个孩子给你带来了什么呢?”“整个世界的希望和快乐。”
——泰戈尔
这是一个美丽得不着痕迹的村庄,此刻,秋天已经来临,夕阳即将离去。母亲梦见自己的手上开出一朵白色的栀子花,于是你来了。这朵花平安到达彼岸,注定要用经历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的命运。你有了名字,叫多余,是奶奶起的。你的出世是热闹的,一个金碧辉煌的男孩和你一起走向人间。那个叫结果的弟弟解放了全家人绵长的期盼,而你的名字就显得那么恰如其分。在荒凉的后园子里,生长着你荒凉的童年。时间拉着记忆飞快地跑,身体跟在记忆后面慢悠悠地长。你日渐粗壮的腿啊,我依旧纤细的胳膊。童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的皮肤?红萝卜不说话,白萝卜眯着眼。昨天那只小蜻蜓又飞来了,翅膀破碎而疲惫。蜻蜓蜻蜓落落,给我马莲垛垛。你伸出手,它便睡在你的小指上了。柔软的风小心地吹过,让它的翅膀微微颤动。那两只球状的大眼睛明亮而生动,永远也不会闭上,仿佛它并没有死,只是在天堂做了一个童话样的梦。你听,它在梦中轻声歌唱——我在天上飞翔,你在地上流浪,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呵,一样一样,你的眼泪轻盈地飞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化作天上新来的一颗星星……
多余,你实在是个爱上寂寞的孩子。看见汪汪叫的大黄狗和拉家常的母鸡们你都缄默了嘴角。你小小的身体靠着年老的墙根。白太阳的光落在血红的鸡冠花上撞得粉碎,惊心动魄。你咬住倔犟的嘴唇。任何一点儿声响都会让你的沉默受伤出血,多余,你为什么不喊疼?天黑黑,要落雨。后窗的三块玻璃蒙上了一层呵气,梦的边缘被侵蚀,斑驳而暧昧。你的心里莫名地难过。是谁把温暖的泪水蒸发在它们的心头?你用圆润的无名指点了个点儿,这个点儿里有雨季的神话和你欲歌的眼睛。多余,你看见了什么?三只鸭和五只鸡的毛都浇湿了,衣服湿了多难受。鸡的眼睛亮晶晶,双眼皮,鸭的眼睛闭着,呆呵呵。你还看见了什么,多余?屋檐上的稻草棍落下黄色的雨滴,一滴,两滴,三滴,四滴,打翻了我的小纸船,也打在呆鸭扁扁的嘴上,它们不躲。要滴到什么时候呢?它们回不了家了。还有,你还看见了什么,多余?还看见豆角把细细的藤缠在苞米的秆上,好紧好紧,好像缠在心上,没有人能扯断呐!哦,你终于看见了,那是豆角和苞米的原始爱情。古老的风里早就飘满了他们的誓言。秋天已经死去,苞米的面也不再英气逼人,豆角的果荚干瘪了耷拉在胸前。他们已经苍老得走不动道了,于是牵手站在出发时的地方,等待死别。不不不,别再看下去了,这是你今生最初的记忆,你怎么忍心让它过于忧伤,过于美丽?
你牵着你的影子,游荡在飘满灵魂的田野。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再走过去。一只黑色的大鸟正在不远处整理自己心爱的羽毛。你今天才知道,那个叫结果的弟弟在出生的第二天就死去了。他太早地死去了,你本应该摸摸他的脸的,可等完了上辈子还是来不及。你想,是我们前世的修行不够吧。你和他只有从一个女人平坦而崎岖的道路上走进今生的缘,却没有触摸彼此生命的份。就缘分而言,莫谈公道。你认真地注视田野里的每一根辛苦的草,每一只匆匆赶路的消瘦的老鼠,还有那模糊不清若有若无的脚印。你想,我每看它们一眼,察觉到它们的一点儿动静和气味,心里萌动了一点儿小小的念头,都是了却了一段无数个轮回才结下的尘缘啊。结了却,却了结,没完没了的缘。下一棵草在等着我……你随着风的方向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小小的坟。你困饿交加,淡淡地蜷着柔软的身体睡着了,不知在哪一家的祖坟上。
多余,你抬起沉重的眼神看看呐,身边的小姑娘小小子不都在大道上欢乐地疯着闹着吗,像一群单纯的小妖精,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游戏。呜哩啊啦的叫声笑声,是竹子开的花。蓝旗沟的小孩子都是在这条大道上响亮地长大。可你为什么不动声色却又如此慌张?你捧起大把大把黄色的叶子奋力扬撒,无数个世界在旋转!旋转!那是在重新演绎生命的凋零,还是在幻想蝶舞花飞的春天?一颗嘶哑的心灵在追问。我前世的魂,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旷野?这么寂寞,这么疼痛。头上升起一道蓝色的光。也许我的前世就是一个透明的存在,只是要我们知道的存在。那么,我知道好了。我的前世,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不用回答,我已经看见你清凉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