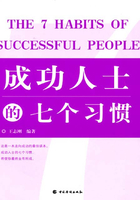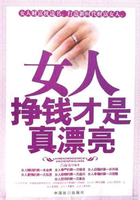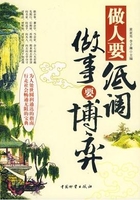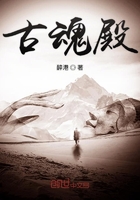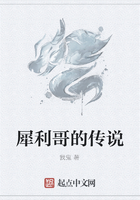偷换概念是形式逻辑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是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之一,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不确定,不同一。例如:“群众是有无穷智慧的;我是群众;所以,我是有无穷智慧的。”在上面的推理中,大前提的“群众”是集合概念,而小前提中的“群众”是非集合,这里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混淆起来,故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但借用到幽默中,即是指故意地将不同的概念混淆,不会当作一种错误被排斥,而是作为一种能产生幽默的妙方加以重视和利用。
偷换概念有时是借用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内涵,而故意将用于彼语境中的内涵偷换到此语境中,从而造成说话者双方在逻辑上的不统一。如:
这是俄罗斯钢琴家安·鲁宾施坦让座位的故事:
音乐会就要开始了,这时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闯进了演员休息室。
“啊,鲁宾施坦先生,见到你,我真是太幸福了。我没有票子,求您给我安排一个座位吧。”
“可是,太太,剧场可不属我管辖,这儿一共只给我一个座位……”
“把它让给我吧,您就行个好吧!”
“行,我把这个座位让给您,要是您不拒绝的话。”钢琴家微微一笑地说。
“我?拒绝?简直不可思议!领我去吧!座位在哪儿?”
“在钢琴旁边。”
那个女人只管闹着要“座位”,而“座位”是类概念,它包括“钢琴家的座位”和观众“座位”,既然她不说明要什么“座位”,那么钢琴家也有理由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鲁宾施坦故意混淆“座位”的不同概念,是讽刺那个女人不太明智的要求,言谈中充满幽默感。
偷换概念的另一种重要方法是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进行偷换,如:
①甲:“我们厂的领导光明磊落,有话总是喜欢在桌面上谈。”
乙:“在什么地方谈?”
甲:“饭店雅座。”
②甲:“听说你要跟表妹结婚了?”
乙:“是的。”
甲:“婚姻法上不是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吗?”
乙:“我们不近,我长在南方,表妹住在北方,相隔远着哩!”
③甲:“世界上哪一国人口最多?”
乙:“当然是联合国。”
例①中,“在桌面上谈”意指有话说在当前,不搞背后小动作,这与“饭店雅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例②中,婚姻法中的“近亲”系指“亲缘”关系,与“地缘”即距离相隔的远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例③中,“哪一国”是指某一个具体国家,而“联合国”是不属于同类范围的。将不同类的概念混淆,故构成了幽默。
从以上各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偷换概念并非无限制的乱偷乱换,用来偷换的概念与被偷换的概念之间多多少少总存在一些联系。或者有字面上的联系,或者有类属、字义上的联系。这种微妙的联系是“偷换”的前提,“偷换”是否自然,是否能水到渠成,关键就是看能否准确把握住这一点细微的联系,并从中将“文章做大”。
“偷换概念”一“偷”一“换”都得小心细致,胆大慎微,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大煞笑意。
有意避用语词的专门意义,取其字面意义,就会产生巨大的思维落差,给人出乎意料而又不悖情理的新奇感,幽默也就随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