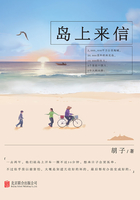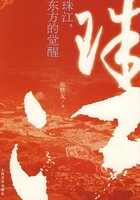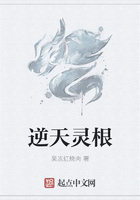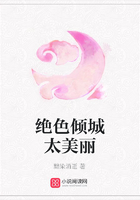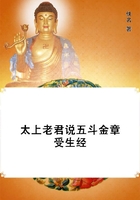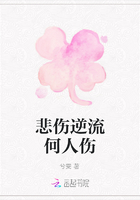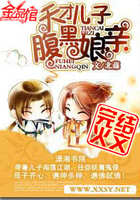我似乎在不断地强调日常生活,我似乎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我似乎总在用一些细节来触摸整体。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源头,只能是那句老话,人只能在生活里,可人活着,却常常忘掉自己在活着,尤其会忘掉那些细节。我珍视它们,因为我从那最平凡的事件里,看到了蕴藏着的诗意——不必是学术的诗和深奥的意,只要比所有的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多一点感触,多一点会心一笑,就足够我们抵御许多空虚和无聊了。
它们在广大的范围内,是连续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可在个体的人的眼里,却是偶发的,需要我们去捕捉,从最日常里往外打捞,沥尽泥沙和水藻,显露出闪光的珊瑚。它们是可回味的,如同可被心灵咀嚼的橄榄,含在我们的肉身中,一点一点品尝它的滋味,吮吸它的养分。
1.
2008年的春天,硕士毕业前夕,我在一家门户网站实习,也考虑将来在那儿工作。这是一个网络访谈节目,有时候要晚上加班。
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做了一个和奥运有关的节目,结束时很晚了,已是凌晨2点,同事说别回学校了,一起熬夜吧,明天倒休一下,何况一直在下着小雨呢。我想了想,觉得与其在办公楼里枯燥地上网熬一夜,还不如顶着细雨赶路呢,在春雨里,总比在电脑前好得多吧。
我出了楼,下了大半夜的雨不折不挠地持续。打伞,开车锁,用很小的一块纸巾抹掉坐垫上的水,院子里空无一人,身后的楼上几位同事继续熬着,那里太亮了,有点儿和整个黑夜格格不入。
春雨靡靡的黑夜真好,人车俱稀,马路湿湿的像条幽暗的蛇,我骑得不快,竟赶上一路绿灯。举伞的左手有些凉,坐垫上的屁股也有些凉。安静的北京,这个睡熟的婴孩,一呼一吸,让人短暂忘记白日的喧嚣,但我更关心的是:“那对夫妻还在不在?马上就要到金五星铁路那儿的一个路口,他们在不?”
实习的那段日子,每天上班路上,我到这儿时必有一辆火车通过,日日如此,有时候走得早了,也会停下来,等它轰隆隆开过去再继续行。这是日。夜的念想就是那间露天饺子店,说是店,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麻辣烫模样的小摊。夫妻二人,摆一座炉子,一张长桌用来和面,包饺子,两张小桌供食客用。妻子和馅包饺子,围着白围裙,不怎么干净,也看不出有多脏;丈夫生火,煮饺子,偶尔也帮着包。
只要晚上7点后下班,总能在这儿遇见他们,每次都极想停下来,坐下来,要二两饺子吃。还有啤酒,他们也卖啤酒,但是不负责兑奖。可是每次,我都感到自己太行色匆匆了,根本不配这安静的小摊。
“今天,下了这么久的雨,他们一定早早归了,或许根本没有来。”我在快到那儿的时候,脑子里不停地问自己。
过了金五星附近的铁路,不知道是哪座高楼的探照灯一闪,我看见一片蓝色的雨布下他们忙碌如常,四五个食客围坐着,眼巴巴望着冒白气的锅。啊,一个雨夜,深夜两点多,他们依然在这儿,我兴奋极了。今天一定要吃一碗饺子,我再也不能错过这夜晚的温暖了,何况他们是那么和善,满溢着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愿望。
我停车,要了饺子。雨还有,但足够细小,几乎就是一种湿润的风。我跟他们聊了起来。老板娘告诉我,他们每天凌晨3点多才收摊,一天要卖好多,有时几乎忙不过来。饺子是白菜和猪肉馅的,4块钱20个,一点儿都不贵。只可惜已经没有我坐的地方了,只好打包带走。
带着一盒水饺,我继续夜晚的骑行,想象着他们一天的生活:凌晨3点收摊,回到家怎么也4点了,天色初明,洗洗睡了。大概中午时分醒,望着屋顶几秒钟,起床收拾东西,面、馅、饭盒、蜂窝煤,一切要用的物什。这些得忙到晚饭时间,吃过晚饭,丈夫吸一支烟,妻子依然这儿那儿地拾掇。恍惚中天黑了,因为路灯亮起,屋子里模糊了,他们便将东西搬上小车,锁好门窗,开始新的营生。
我曾有一个人生梦想,做一个推土机司机,现在,我也梦想着自己是个饺子摊主,夜夜出门,雨天也不歇息。
在有限的30年生命里,没有哪个夜晚比今天更湿润,我仿佛在黑夜的缝隙里左突右冲,于这儿停下来,喘口气。这么拼命地向前跑,好像只为偶尔能遇到这样一个片段。尽管数日之后,我再也不敢确定是否发生,我还是庆幸它不是听来的,读来的,它曾经在。
第二天雨歇了,天地又是老样子,上班比平时晚,依然候到了路过金五星的火车,并不是往常的那一列。轨道、火车、雨夜或晴天、小吃摊、偶然路过的人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一首诗的词语、标点和韵脚,在某个特别的时刻,飘浮到一个特别的空间,把这首诗呈献给人们看。有的人读到了,有的人只是清清地呼吸到它的气息,然后飘然而去。然后所有的元素都会飞散开,有去往其他的时间和空间,凭借其他的机缘,同另一些元素构成全新的诗了。
2.
2009年8月末的一日,节气已是初秋了。
我和同学桑桑去朋友阿周的新家,在地安门的一个深胡同内。我坐地铁,转一次公交,下车后见阿周在路边等我。这儿离北海公园不远,热闹,车多人杂,十字路口和你所见的一样乱。东南角,是一堵高高的红墙,沿着墙边向南走几十米,红墙突现一个豁口,进去就是另一番天地了。走过水果摊,老板正光着膀子看武侠片,铁皮搭建的刻章小店窗关门锁,我趴在玻璃上看了看,隐约见到里面摆着几副毛笔字。一些老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些活泼的孩子四处跑着,这儿也并不宽敞,但与红墙之外完全不同。隔着院子,听见了某家人唠唠叨叨的说话声。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慢了下来。
阿周租的房子,是一个老宅,大概有100年了。可它不是古董,古老的青砖、木门和现代的红砖、水泥等混在一处,告诉我们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四进院,每进都有几户人家。路歪歪扭扭,地砖大概铺了太多的年纪,早已不平整;窄窄的走廊两边,堆满破铜烂铁类的杂物。
阿周住东厢房,房子是一个老太太的。为了增加收入,老太太又在门前建了小房子,把整个厢房的阳光都遮去了。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潮气,一进去,阿周便把电扇打开通风。我坐在用50块钱从前任房客那儿买来的大藤椅上,翻检他桌子上鬼怪样的茶杯、铜鼎形的烟灰缸、一套蛮新的刻章工具。我小心地怀疑,一到晚上,他就会化装成老头跑到胡同里的刻章小店去干活。
阿周到门口,和隔壁的女邻居谈起房东老太太。女邻居不避讳地穿着睡衣,吆喝着自己的宠物狗。
“老太太说这个房子要拆掉,到时候就有阳光了。”阿周说。
“是拆掉,可她是想再建房子,今天都带工人来了。”邻居说。
“啊?”阿周对一整面阳光的幻想破灭。建房子,只能把他的门外空间堵得越发逼仄。
然而一小会儿,我却被一缕阳光晃得眯起眼睛,它从我面前掠过,定格在北面的墙上,循着它的轨迹,我找到南面墙上折射的镜子;再转头,则看见更外一点的门口,竖着另一块镜子。夕阳,一天最后的阳光,终于曲曲折折地照进了阿周的房间里。
“是那么个意思吧?”阿周笑呵呵地问。
“挺好。”我说。
再过一会儿,太阳沉下去一点儿,他就到门口,把镜子的角度调整一下。
我们闲聊,等迟到的桑桑。
阿周不住念叨这儿的蚊子有多厉害,我仍未被侵犯,想来是蚊子喝惯了他的血,对我这新鲜血液尚无兴趣。但一刻钟后,他出去接桑桑,我的胳膊、大腿便连番遭到蚊子的攻击,不停抓挠,似乎是在反驳我刚才的想法。
他们回来,提醒桑桑同学马上防御,我还点燃一支潮湿的烟,企图熏走它们。但之后,再无蚊子。
“只有下午一会儿,晚上一点儿蚊子都没有。”阿周说。
我们总结,它们吃饱喝足,休息了。他要想晚上睡好,就必须下午时分把蚊子喂饱。
然后去院子,赞叹年久的老宅,隔壁高官森严的阁楼,某个人家厨房里飘来的香味。我们看见旧门廊上的芦苇草,草背面是夕阳。
太阳完全落下去后,我们又进到屋里。二人拿出吉他,开始谈论我所不熟悉的一些和旋、曲调。偶尔,刚刚临近30岁的我们,谈起更年轻时的事情:在刘和珍君等纪念碑前的草地上喝酒,也谈论诗歌。阿周的琴弦音似乎不准,两个人就找到调音器逐个调。桑桑对阿周捡来的琴,比她新买的琴要好而愤愤不平。“哎呀,你的琴竟然比我的好,”连说几次,又接着,“我的也不错,是新的。”
他们寻找拨片,但阿周并无拨片。“可以自己剪一个。”我拿出那张即将过期的麦当劳优惠卡,阿周用剪刀剪成拨片形状,桑桑试用一下,惊奇地说:“真的行啊。”那张卡,一共剪了6个拨片,最后一个最像。他们没有弹一首完整的曲子。
我可以想象到,阿周独自在家,摆好两块镜子,让傍晚的阳光漫长地照射过来,坐在他破败的沙发上,弹着吉他。我可以想象,桑桑独自在家,对着琴谱复习吉他课老师的指法。
这一刻,他们都是安宁的。
我遗憾自己此生与音乐无缘,但还好我可以写诗:把突然来临的诗句写在随手拿起的任何一种纸上、某本书、病例本,甚至是餐巾纸。写诗这件事本身,让我体会到一种幸福,即便某些诗句惨不忍睹,某些诗永远完不成。写诗与弹琴,本该是一件事,如同最早的行吟诗人,一边弹着自己的琴,一边把古老的史诗唱出来。我记起来,刚工作也在租房的那段时间,身居临路喧闹的23楼,常常站在阳台上想一些诗句。那是某个富人的一间大房子,被中介改造后,住了7户11个人。隔壁的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在学德语,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德国人,在刚刚度过18岁的生日后。另一个邻居是卖花的,常把卖不掉仍在开着的花拿回来,摆放在卫生间。更多的时间,是听到有人吵架,因为水龙头坏了,因为没人主动交电费,因为抢厨房。所以,我喜欢站在房间狭窄的阳台上,在那儿,阳光满满,但从来都被人忽略。
弹琴与写诗,都只是一件让人心安的事情,并不很关乎曲子多美、诗句多好,只是——我们弹琴,我们写诗。就像母亲在田野里,认真地对待着每一棵庄稼,而不单是把秋后的果实作为劳动的唯一。
三个人相聚时,吃吃饭,聊聊天,即使没能看到残缺的月亮、没有完整的琴声,也是好的。我结婚了,早已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每天下班,第一反应便是去接老婆;有人相约出去玩,也会立刻想到去和不去对另一个人的影响。作为这个大都市的穷人,疲于奔命中的快乐常常是做一顿饭,写几个敝帚自珍的句子,擦擦书架的玻璃,或者只是睡个懒觉而已。阿周和桑桑各自单身,独来独往。桑桑同学,永远有着自己的计划,每次见面,她似乎都在开始一件新事情,准备着另几件;阿周,则喜欢用他特有的世界观来丈量日常生活,经常偶发冲动,去考个导游证,或者跑到云南买辆自行车,骑一周,然后卖掉,步行。
我和桑桑,常有职业的倦怠、情绪的消沉。但阿周,似乎天生储蓄着一种无所谓式的淡然,不急不慢,随性自然。所以他在阴暗、潮湿,甚至有些破旧的房间里,开着空调,盖着厚棉被,自得其乐。
没错,我们都一样度过黑夜,无论弹琴还是写诗。我不知道,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是不是只有靠弹琴写诗(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事)才能度过黑夜。这两件事都很无用,但都很重要。只有它们,才能在我们内心生活里折射出巴掌大的光芒,不至陷入孤独和恐慌。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最近在从事什么工作,在弄什么东西,你能搞清楚他的生活吗?不,不能。但如果他真诚地讲到,他在弹琴,他在读书,他在写诗,在天桥上看车流,在逐个胡同闲逛,你一定能从心里感受到他的生活。
无论多广袤的土地,人可行走的路,无非那么几条,掩映在荒漠、尘埃中。我们都在自己的路上,如同成千上万漂泊在北京的外乡人。
生活就是这样吧?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吧?
3.
曾经看到一个笑话,说某犯人被押赴刑场,即将砍头,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没说的就马上行刑了。犯人不语,只是哈哈大笑数声。行刑官及一众人等都感到不解,问因何发笑,犯人答道:我听说每笑一次可以延长5秒钟寿命,果然不假。
小时候,在老家,讲故事不叫讲故事,都叫讲笑话,那时候没电灯,煤油灯的煤油也稀缺,一到晚上,听完了广播里的评书,只能上炕睡觉,可又睡不着。我就央求爷爷,说,爷爷,讲个笑话听听吧。爷爷年轻时当过兵,赶过大车,走南闯北许多年,听了不少古怪事,就讲给我听,这是个上瘾而入迷的事儿。
等我上大学,这时代已遍地是以笑为名的物件了,自从有了互联网,搞笑段子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读大学的时候,宿舍一闷骚男过生日,众人问他想求个什么礼物,他说:不求最贵,但求能让我每天看到都笑出声来。中不了百万大奖,也没有绝世美女给他,这礼物难了。但万事有因缘,没想到真被我在学校北门的小胡同里发现了。某夜10点左右,有人在那儿摆摊卖盗版书,随手抽起一本巴掌般大小的《网上夜笑话》,两块钱买了送给他。从此之后,常常半夜能听到此人从被窝里发出一阵怪笑。后来闷骚男在北大读了博士,整日研究西方巴赫金的狂欢化和笑的历史,大概是受了影响。那本小册子曾在各间宿舍里流传,渐渐不知所踪,而且市面上也成了绝版,世上再无此书。每次同学聚会,谈起来都唏嘘不已,年龄大些才知道,诸多感慨里,笑话事小,青春事大。
住在联想桥附近时,上班时要路过一条胡同,胡同口有家包子店,夫妻二人。我总在那儿买几个包子做早餐,一来二去混熟了,正当交易之外便有了闲谈。有天刚付了钱,拿了东西,老板娘说:“你上班这么早,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啊?”那几日正在编辑一本和古诗词有点关系的稿子,说话都陷在对偶、押韵里:“出来满天星,回去满街灯。”正忖度着这么说话太矫情、太装了,猛然间听老板娘回了一句:“Me Too~!”说完自己先笑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那包子自与别家不同。临近年关,我又去买包子,老板娘说:“明个别来了,关门了。”一问才知道,房租涨了近三分之一,为了撑到年关,近一个月几乎都在赔钱。“以后你得想别的辙吃早饭了。”老板娘说。
我默然无语,从不说话的老板,很沉重地叹了口气,地上砸了个不大不小的坑。我再没见过他们,也忘记了包子的味道,可他们的几句话,却永远留在脑海里。我仿佛看到他们夜晚的忙碌、清晨的辛苦,在这些劳作里,点缀着一点幽默感,一切就都不同了。
硕士第一年,我们被学校安排住在了大运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大运村和学校之间。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从师大北门出来,过天桥,然后从一个胡同穿过,绕到学知桥,再往西。师大北门外三环路上的天桥,对面直通北影厂。有天中午,我从天桥上过,看见一个年老的乞丐,衣衫破烂,面目黝黑,如打坐般席地而坐。老乞丐面无表情地挖着鼻屎,然后用指甲弹到天桥下的车流里,怡然自得。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的动作,过了他几步远,蓦然回首,看见老乞丐从怀里掏出一包面巾纸,从中抽出雪白的一张来,仔仔细细地擦了自己挖鼻屎的手指,然后安然地双手扶膝,闭目假寐了。
我同许多朋友讲这件事,他们都哈哈大笑,觉得好玩。这是个笑话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不管是与否,每念及这一场景,我总是会心一笑又心含暖意,仿佛天空中正经八百一个严肃的太阳,突然要打喷嚏,咧了咧嘴。
4.
在租住的小区里,每10天左右,就能看见一辆货车,拉着各种杂粮和干果,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摆开摊位,开始一天的售卖。有时候,也有卖布料和衣服的过来,小区里的居民,特别是那些退休后的女人,喜欢叽叽喳喳地围在那儿挑拣和议论,当然也心满意足地购买。在高楼林立、寸草成金的大城市,在对门不相识的陌生世界里,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集市,把生活的气息蔓延开,浸过小区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是多么好的事情。
每次遇到这小集市,我总会走得慢些、再慢些,只为了看看今天摆了些什么,听听大妈们又在议论哪样东西,在下班的那一刻,这短短一两分钟的路途,几乎洗去了整日劳作的疲惫。
有一天,是一个周末,正是北京最好的秋季,天蓝日光暖。我和老婆下楼,出去吃饭,又经过了那个小集市,这一次,这儿没有摆杂粮或布料,而是有人在售卖棉花、被单。我看见,一栋楼下,人们铺了张很大的席子,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坐在那儿,他们手里是针和线,面前是正在缝制的被子。那天的阳光,把一切都照出了光彩,可又不过于明亮,我的心被这画面击中。特别是那个男子,他几乎带着一丝女人的姿态,蜷着一条腿,向前探着身子,针脚细密地把被衬缝在被里上。他的针,尖锐而细,把秋日的阳光、微风,以及人们的慵懒,全都缝了进去。我简直无法想象,盖这床被子入睡的夜晚会是怎样的感觉。
这就是日常生活,这无数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和场景,相互连缀且渗透,密密地织就着我们生活的巨幅十字绣,远远地,固然可见到这巨幅的样貌,但要了解它的内里,就只能把手和心一起贴在上面,抚摸那些凸起和凹陷,辨别那些颜色各异的线的纹理,甚至嗅着绣针刺破手指留下的血和额头滴下的汗水的味道,更甚至体会了一针一线将它从空无变为繁花的刺绣人的心境。如果我不用“诗意”来描述这些细小和微不足道,还能用什么呢?所有值得爱的人,所有值得过的日子,也无非就是它们的集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