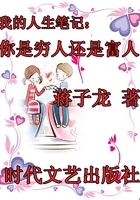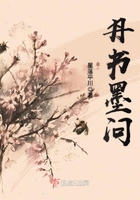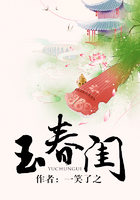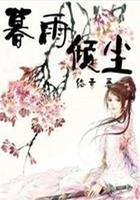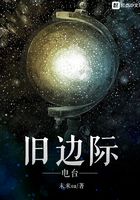未来你好。
这是人们写信不变的开头,我猜想,你应该收到过无数类似的信件。我这一封,不知是否有被你收到和翻阅的可能。好在最初我就了解,写信说到底不过是自我的倾诉和认识。我当然也清楚,你就在我之中,像是我的尾巴,跟着我从生到死,我却抓不到你。
现在,你仍然是不确定的存在,不,你永远是,因为一旦我来到你的刻度,你也就同时消失了。你始终比我走得更远。那为何还要写一封毫无新意的信给你,这无法抵达的收信人?我想,是因为我渐渐明白——不对,不只是明白,还是越来越体验到——通向你那儿的路途是从一个个现在累积而成的,每一分钟都像是一块砖、一粒石子,人们看似随意地摆放和抛掷,却不知它们纷纷落下后,就建成了风格各异的居所和建筑,铺就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的路。是时候,把我们的眼光,从过于阔大和宏观的地方,收回到生活里细小的事物上了,一花一叶固然难以是一个世界,但世界又岂能失去无数的花和叶呢?
1.
未来,你真的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吗?
你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不是一个可预期的结果,而是人们走向你的全部旅途,包括可能遭遇的风雪、洪流、花朵和陌生人。
当人们一提起你的名字,头脑里马上会跳出另两个共生的概念:现在和过去。对现代人来说,过去是被记录的一切,相片、QQ聊天记录、微博、邮件,等等,过去被物化成可以看见和触摸的东西以及能够复制、粘贴和无限保存的数据,记忆凝聚于载体中。而在更遥远的历史时间里,普通人对过去的记忆主要依靠自身的记忆和情感,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可是在这些数码记录之外,在人们每天许多次的自拍和被拍之外,你有多久没有在照镜子时盯着自己的眼睛认真看过了?又有多久没在无所事事的安静时刻想到人生或者别的玄虚的词了?
对普通人而言,未来难以像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那样具体,它是模糊的、难以捕捉的。
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手机上的时间,比实际的时间要快半个小时。这怪癖的来源,是我去年换的手机,时间调错了,之后便没改正。因为我慢慢发现,这被调快的时间,给我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结构,或者说,在一个单薄而细微的层面上,让我和未来有了一个虚拟的接入点,在快出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存在于30分钟的未来里。我每看一次时间,头脑里都会先后出现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手机所标示的,另一个是实际的,我会换算,然后假设自己确实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未来。我也就常常更多地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我等着日常的时间和稳固的世界抵达我所在的位置,但当它们抵达时,我又在前方不远处了。
这当然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但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时刻,我同其他人不在一个时间维度上,并非我早了半个小时,或晚了半个小时,这类时间不是线性的,它是一种立体的思维结构,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好比一个大房子,当大家都挤在某个方向的时候,我凭借它微微地移动和飘浮了一些,我感觉到了空隙。
在写《小镇简史》时,我试图用几段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一个北方小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当我把笔写到2013年时,却总感觉不完整,还缺少什么,直到一个月后,我终于想到了处理的办法,那就是我写到了2025年,它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从过去到未来,这才是历史的真正形体,历史不该单向度地指向过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亦应该是未来史,否则它还有何存在的意义?
接连几天早晨,在上班的地铁里,我都遇到了同一个女孩。她像是一个打工的孩子,应该不超过20岁,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在地铁车厢里抱着一本书在看,这本书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书不厚,里面的字还很大,我第一天看到她的时候,她读的是“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我不知道是哪一段,是什么意思。第二天见到,书页上的字是:“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仍然不知道是何意,只是记住了几个词,到了单位查到这些话。我注意到她,更多的是她专注地看这本经书的神态,仿佛满车厢的人都不存在,仿佛窗外冰凉的秋雨也不存在,我猜想,她是自己信了佛呢,还是依靠念经来祈愿呢?
未来,人人对你有期许,但并非人人都知晓你的心事,我们活在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里,我们的灵魂,也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以至于过重、过滞,和肉体几乎是不分了。在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转发有好运”“转发能发财”“转发保佑家人平安”“转发给你母亲七年好运气”之类的东西,而且,转发量惊人。人们是不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我心里知道这有点儿不靠谱,可一旦是真的呢?转发一下总没有坏处吧?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好的期待,可却把这期待变成了一种隐形的“交易”。这当然也不是有了网络才泛滥的事,在之前,我们已经被这种实利的思维浸润得太久了。中国的老百姓,但凡信点什么,总会把信的东西和自己的生活勾连起来,佛祖菩萨狐仙大神,都是用来保佑他们有个好未来的,发财、平安、生儿子、当官。细细算起来,我们有哪样事物,是不想从它那儿获取什么而信的呢?好像很少。
未来,如果你了解到这些,会怎么想?你可能会叹息着说,这一切都可理解,这一切都有缘由,但这一切又总显得不够,在正当的期许之下,总是缺少点让人心动的东西。
2.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做过许多种设想,然后便自嘲地告诉自己:哈,这不过是些幻想罢了,作为普通人,你只能在可见的未来里,比如成了房奴、当了父亲,每天奔波在上班、给孩子找学校、带父母去医院和自己独自沉默的路上。我知道这是最可能的路,但又总是不甘。
我总会想起,许多年前报纸上的一则报道,现在已然成了一个笑话了。这则报道说,记者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放羊,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放羊?孩子说:为了挣钱。记者又问:挣钱干吗呢?孩子说:娶媳妇。记者再问:然后呢?孩子说:生娃。记者还问:生娃做什么呢?孩子说:放羊。
这样的故事,看成是悲剧,或者看成是奇怪的喜剧,似乎都是对的。很多人以为这是孩子的天真,很多人感叹贫穷人的命运如此逼仄。可过去这么久之后,我们会惊愕地发现,记者一串疑问,已经把这个站在山野里放羊的孩子的所有未来都问尽了。在他能够想象的世界里,这大概已经是最好的未来了。因为放羊未必能赚到钱,赚到钱未必能娶到媳妇,娶到媳妇未必能生儿子,生了儿子又未必会有羊可以放。即便是如此简单的未来,也要靠前一步的实现来为后一步打开大门。
老婆在北京一所还不错的中学教书,常和我说起她的学生,有些孩子,我也见过。我知道,他们尽管课业很累,但有着丰富的课余生活,从小被父母拉着报各种兴趣班、特长班就不说了,即使在学校里,他们也能在生物课上用显微镜看草履虫、血细胞和头发细胞,被这些平常的东西所放大后显露出的面目吓一跳;他们在学校的电视台做新闻,招聘新成员;他们参加各种比赛,跑到大街上去做调查问卷。这真好,我想,他们的学生时代真好,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安排好了等着他们去做。
我会想到自己中学时,甚至是老家现在的中学,这一切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的只是上课而已,大概唯一能持平的,就是有一部分孩子有了手机吧。我忍不住比较两种中学时代,仅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在想,除了课堂上老师讲的那点知识,没有任何综合素质方面的训练,这种缺失,会不会一直延续到我的未来生活呢?又或者,正因为没有如此丰富的选择给我,在枯燥的山脚中学里,我才培养了自己的想象力?其实这是不可量化的比较。
大学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从小练小提琴,好像已经考过了十级,水平很高的。到了大学之后,还参加过几次演出,但后来他放下了琴弓,几乎再未拉琴。再后来,他读硕士读博士,毕业后成了某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者。当年对他,还有那些在各种晚会上展示才艺的人,我都是仰望的,那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某些层面、某些高度。
而我现在的疑惑是,他练了十几年的小提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造就了现在的他?是给了他坚强的意志,还是赋予了他艺术的敏感力?如果说意志,那这种意志,同在田野里辛苦劳作所培养的意志,是一样的吗?如果说是艺术敏感力,那这种敏感力,同其他人仅仅是在书中获得的敏感是一样的吗?或者说,对于普通人,不想成为某种艺术家的人来说,这些训练和培养,是不可替代且不可或缺的吗?我只能提出疑问,无法从现在所见所闻的自己和他人的人生里,归纳出可信的结论。
但我想这疑问也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因为我知道,有太多的人永远不会获得这种艺术性的训练、丰富的机会,他们只是在土地里生长,只是在小镇上徜徉,只是获得了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如果这些不可或缺,他们的未来,就将永远被这些缺失所局限。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是不公的愤懑和无奈。
我们的未来,不但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人生,更重要的或许是我们对这人生的认知。当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弹钢琴、不会画画、不会跳舞、不会唱歌,总之看似是一种才艺的东西也完全不会时,我该是什么样子。这种认知,帮助我找到在现实的位置。
3.
未来,你并不知道,不同的人,通向你的路是多么的不同,路途中不仅仅有风景,更有不为人知的痛苦遭际。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但最后不同路的故事。
童年时,有几个相对固定的伙伴。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凑到一起,弹珠子、用棍子和树疙瘩打农村高尔夫(俗称“放猪”)、滚铁圈等。暑假时,也一起放羊,或给马割草,寒假则一起去山上捡柴火,逮兔子。
有一个伙伴,叫阿龙,个头极小,面貌黝黑,但两条短腿跑起来真快。我们上小学时,他总是在班里蹿来蹿去,没个消停,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驴粪球子”。另一个伙伴,是我家东邻的东邻,姓孙,叫阿辉,个头也不高,有一双大脚,也极能跑。平日里不爱学习,但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阿辉就成了风光人物,他光脚板,挽裤腿,什么一百米、两百米以及各种接力赛,无不拿第一,得到的铅笔、橡皮、练习本等奖品,非常之多。这时候,许多孩子的父母都夸他:“看人家孙阿辉,真能跑,一年都不用买铅笔作业本了。”
阿龙和阿辉两个都能跑,大概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后天锻炼的因素。他们两个的父亲都养马,他们便常年要在黄昏时去野外把马赶回来。马自然很野,不可能乖乖就范,他们要追上个把时辰,才能把马圈回家。平时在山上玩,看见兔子,他们两个也是不知疲倦地追,直到把兔子累得废掉,彻底放弃逃跑被他们捉住。
小学毕业后,我读了初中,他们两个都辍学了,很少有机会再在一起玩。阿龙成了马倌,他和他父亲及弟弟阿海,轮流在山上放全村的马、驴。三个小个子,都是快腿,村里人都说,再没有比他们一家去放马更合适了。每天早晨,妇女们出来倒灶灰的时候,他们爷儿仨分别从东、西和北,吆喝着各家的驴、马要上山了。那两年,他们家是极令村人羡慕的,放马,不耽误种地,每年还能有五六千块钱的收入,在15年前,这在农村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很快,他们就在院子里盖起了砖瓦房,等着娶媳妇用。但世事总是无常,他们当马倌,有一年丢了几批牲口,赔钱赔得亏了本,就不愿干了。阿龙阿海兄弟俩,开始跟着村里其他跑外的人出副业,到城里打工。大二暑假,我回家,闲聊时母亲说打工好多年的兄弟俩回来了,而且老二从云南带回了一个媳妇,说的话村里没人能听懂。
阿龙和阿海的姐姐,嫁给了我家邻居的儿子秋生。每到腊月,秋生家的灯总是亮大半夜,屋子里传来喝酒划拳的声音和打牌的叫喊,基本上都是秋生、阿龙和阿海再加上另外一个人。可我在村里走,却从未碰到过他们。开了春,兄弟俩又扛着行李出去打工,还是一去一年。
我曾经以为,他们的生活,或许同类似的乡村人一样,打工、盖房子、娶妻生子、养孩子,然后老去。但故事并非如此简单,去年春节回乡,和母亲聊天,不知是什么由头,提起了我们前院的一家人。那家人姓孙,大儿子因为和妻子吵架,喝农药死掉了,小儿子娶了媳妇单过,二儿子成了年纪不小的光棍。这个老二,也曾经谈过恋爱,但因为和未婚妻在家里过于亲热,他母亲便瞧不起这姑娘,终于给拆散了,然后拖来拖去,拖成了光棍。大哥死后,老二和母亲一起抚养了大哥留下的儿子,直到给他供到大专。这时候,他已经四十几岁。给他娶媳妇,是他母亲的一块心病。后来,他家有了一个女人,我某次回乡从门前经过,应该是打过照面的,我以为他终于讨到了媳妇。这年春节,母亲跟我说起来,我才知道,他不是讨到了媳妇,而是买到了媳妇。他的妻子,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
我震惊于自己老家虽然远,但并不算绝对偏僻的地方,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买来的媳妇——这种事,在更穷的以前却是没有过的,更震惊的是,卖给他媳妇的人,就是我的儿时伙伴阿龙和阿海。我又打听才知道,他们一共从南方拐卖了四个女人到老家这边,一个卖给了附近村,一个在我们村,另外两个去了哪儿没有传言。前几年,我回乡的时候,还曾在路上碰到过他们哥俩,礼节性地互相问新年好,其中的一个还掏出烟来给我,我说自己不吸烟。我记得,当时的他们神色淡然,带着春节时喝酒、打牌、喧闹后的放松和疲惫,而那时,他们已经把那个女人卖到了村里。这个女人的家,就在他们姐姐家的前院,两家只隔了一条五六米的土路。我没有机会,大概也不可能去问明白,他们何以成了这样的人。我也不记得,在我们八九岁,一起去山上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过类似于未来的字眼。如果有,应该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吧?
另一个伙伴阿辉也出过副业,但很快就回来了,跟着他父亲开始制鞭炮。这纯属手工作坊,一切都在他们家的仓房里完成,鞭炮里的炸药自己炒,卷筒自己卷。阿辉经常到我家里去收一些旧书,回去用书纸来卷鞭炮。那两年,我们家过年放的鞭炮,都是从他们家买的。得这个便利,他家会自制一些比二踢脚稍小、比一般的挂鞭要大许多的鞭炮,在除夕夜,谁家的鞭炮也没有他家的响。有一年,他们在炒火药的时候,炸了锅,房子差一点儿被点着,万幸没有伤到人。公安局的来调查,似乎是罚了不少钱,告诫他们再也不能私自制造鞭炮了。这个营业就算歇了。
有人给阿辉介绍了个对象,就是村里前街一户人家的姑娘,好像也做过我们的同学。他结婚后,分家另过,搬到了我家前院他爷爷的老房子里,和我们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我夏天回去,看见他扛着锄或拿着镰刀在路上。他说:“啥时候回来的?”我说:“昨晚上的班车。”然后竟然两人都没话了,就告别了。冬天回去,他已经抱着一个娃娃,嘴角咧着,看起来很高兴,问:“啥时候回来的?”我说:“昨晚上的班车。”还是没有其他话,仍然告别。再一年夏天回去,他还抱着一个娃娃,大的那一个已经可以走路,抓着他的衣角,阿辉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这一年冬天,我没在路上碰到他,他却在某一天到我家里,原来是他家的洋井无论怎样也引不上水,到我家挑水。“这天可真冷呀。”他一边压水一边说,我附和着他,天真的很冷。叙述许多次几乎毫无差别、毫无意思的见面,是因为,这些时候我心里总会有个声音悄悄说:“这是小时候的伙伴呀。”我在极快的瞬间,回想起当年他光着脚板飞跑的情形,他举着奖品意气风发的样子。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像童年那样一起玩了。
然而等我工作后再回去,又碰见他的时候,竟可以平淡地谈上几句话了,虽不外乎一些家长里短,但终于找到了交流的方式。是的,我心里再也不会有个声音说:“这是小时候的伙伴呀。”我们不再是伙伴,他成了一个村里人,和其他村里人一样。我再不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十几岁时的样子,现在这张成熟的、粗糙的,甚至已经开始显出老态的脸,永远不会是那张红扑扑、圆滚滚的脸了。
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都走了类似的路,在家种地、出外打工、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他们也用上了山寨手机,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从村东小卖店里买上两箱蒙牛的牛奶,送给老人和亲戚,他们会和熟人一起赌点钱。而他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吃着气味奇特的零食,他们感慨自己的孩子真是有福,因为他们小时候什么也吃不到。我曾经幻想过,如果童年的伙伴们重聚,坐在炕头的酒桌上喝酒,会说些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到当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从回忆中再重走一遍这条通向各自未来的路。
所以未来,在每个人的人生里,你都并不知道自己在最初被想象时的样子吧?你从幼小的心里诞生,然后经历许多意料不到的改变,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如果真的重走一次的话,我们还会走到现在所在的地方吗?我们还会通向同样的未来吗?
4.
未来,你现在,躲在远处窃窃而笑,笑我这试图抵达你的徒劳,笑我连现在的生活也不过是奋力挣扎,竟还想着拥有你的美景。但我仍要不卑不亢地写给你,写出我此刻所能完成的认识,我的幻想是,也许有一天,你会回身来奔向我,给我以惊喜。
未来,在我30余年的人生里,这世界变化很大,而作为人,作为生活在其中的普普通通的人,我还是要和大家一样,对你怀着温柔而和美的期待。为什么不呢?既然有一个充满迷人可能性的未来,不妨就在那螺蛳壳里,演一场天宽地阔的大戏,无论它是悲剧还是喜剧。
未来,如果你有一双眼,并且睁开了,你就会看到,这世上的人都使尽浑身力气奔向你,或慢或急,也许有人搭了权力的便车,有人借了金钱的助力,有人献上了血肉之躯,但更多的,是默默工作,艰苦行走。
未来,我必须告诉你,这封信来自五个昏昏欲睡的中午,来自无数个早晨6点多钟的地铁车厢,来自许多午夜半睡半醒时的偶然想法,然后拿起手机在便签上记录,它更来自我在现实的路和象征的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是的,所有我想说给你的话,都来自这偶然与必然掺杂的机缘,它们自在自为,只是通过我来表现。而以上所罗列的这一切,也就是我所面对的世界,同时就是你所立身的针脚。
好了,在信的最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梦。
几年前的某个周末,我在家里午睡,在梦里,我惊骇地发现自己成了“独眼龙”,左眼瞎掉了,而且没有眼珠,黑洞洞的眼眶里,塞了一块磨得不甚圆的小砖头。因为棱角和砖末,这枚眼珠硌得我难受极了,我当时的心里,充满了它所带来的疼痛和悲伤。但是,有一部分意识在梦里苏醒,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我在梦里迅速回想起睡觉之前某些真实的事件:午餐时,我曾去一家面馆吃面。当我点餐和付钱的时候,服务员竟然没有用奇怪的眼光看我,这不可能。难道你看见一个用砖头做眼珠的人,不是至少面露惊讶之色吗?还有无数的路人,他们都看见过我的眼睛,但全部淡定……这些场景,让我开始意识到也许它只是幻觉,不是真的。很快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雪白的墙壁,伸手一摸,发现左眼是左眼,并无砖头掉落。
这是我多年来,唯一清清楚楚记得的梦,它用一种偶然的方式,开掘了我所不了解的那部分内心,而这一直期待被耕种和收获的地方,是和你有关的,未来,你是否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讲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