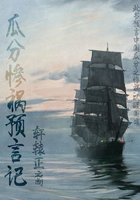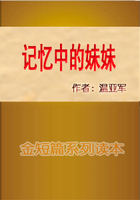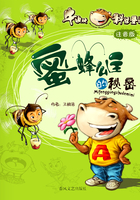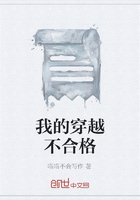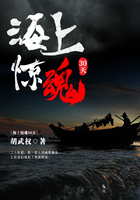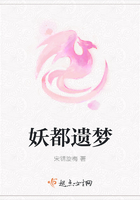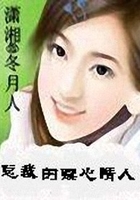和珅在一年之间由一名抬轿的小官,摇身一变当上了头戴一品朝冠,管理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并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特权的当朝重臣。凭什么?除了凭他投机取巧的伎俩,凭他巧舌如簧,善于拍马屁的独特本领以外,他也确实有真本事。
和珅刚到上虞备用处的时候,在所有侍卫中就属于特立独行的人。周围那些纨绔阔少、八旗子弟,都具有相当气魄的家庭背景,到这里来当差事,就是为了找个虚度光阴的场所,到了一定的时候,凭着在朝中的势力,一样能捐个大小官员。可是,和珅不同于他们。他自幼心有壮志,刻苦用功,一心想着成为人上之人。故此,在其他人当差、混日子、无所事事时,他却同样复习学过的文化知识,背诵过去那些古人的不朽之作,以备日后应用。皆因这点,和珅颇受人们的喜爱。也正是因为这点,大学士英廉方敢把自己的孙女下嫁与他。
和珅的艰辛努力,终于有了收获。这个收获,既是理应得到,也是出于一次偶然。
有一次,乾隆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外巡活动,宫中侍卫处的大部分侍卫都伴驾随行,时刻不离地围在皇上左右。而和珅他们这些虞备用处的侍卫,则是没有资格到跟前的,他们充其量也就是负责在外围做好保卫工作。
这次的巡幸活动,首先定在了河南,内容就是乾隆带领诸位臣子,视察当地的河务。
古时所说的河务,主要是指黄河的工程。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它的中游即从河南开封一直向东,所过之地尽属平原。由于此处没有峡谷峻岭的约束,一泻千里的黄河,经常出现河水决口泛滥的情况。
每逢黄河决口之时,河水自上而下横冲乱撞,使河道附近几个州县饱受水灾,尤其是黄河因水流不畅而形成倒流直入运河,使漕运受阻。
漕运,是当时最为主要的运输途径。如果漕运受到影响,就会直接威胁清政府国库。因为清政府每年需要通过漕运从东南运送400万石粮食到京城,用以养活人口众多的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对于黄河的治理。
乾隆巡幸的大队人马,一路浩浩荡荡来到河南地界,驾临开封。河南巡抚袁扬、河督萨载、开封知府苏绩等人,组织当地官员、百姓夹道欢迎。
此时,正是五月初期,微风轻拂,幽香阵阵,鸟鸣雀跃,一片祥和气象。乾隆所过之处,迎驾百姓跪于道旁,口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喊声惊天动地。
乾隆到达行宫后,稍事休息,即召见河南巡抚袁扬和河督萨载,询问河道治理、赈济灾民、天象变化等诸方面的情况。因为萨载专管河务,各个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乾隆的问话,都是由他逐一回答,袁扬则在旁边加以补充。
因为两个人回答得流利顺畅,圆满周到,乾隆听后甚为满意,不时露出一丝微笑。
正在此时,在外负责保卫事项的领侍卫内大臣阿桂进来面圣:“皇上,微臣方才接到一则边报,请您御览!”
乾隆马上停下问话,说道:“呈上来!”
一名侍卫从阿桂手中接过边报,走到乾隆眼前,恭恭敬敬地展开交由乾隆阅览。
乾隆接过,仔细阅读起来。边报上并无重要的军事情况,只是奏明了有一名朝廷要犯从拘禁地逃跑,至今未抓获归案。
乾隆看到此处,不禁皱起双眉,面现微怒之色,他将边报随手往侍卫手中一丢,目视前方,缓缓说道:“虎兕出于柙!”
乾隆说这句话时声音很轻,周围的大臣知道他说了一句话,但未听清具体说的是什么。阿桂、萨载、袁扬以及离乾隆最近的侍卫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不免心中紧张起来。他们担心乾隆刚才的话有什么旨意要传达,要是这么重要的事没有听清,罪过可就大了。
“虎兕出于柙!”乾隆的思绪好像仍停留在边报上,又缓缓地说了一遍,目光仍没有离开手中的边报。
周围的大臣和侍卫这次都听清了,但却没人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于是都不敢随便插话。而站在远处的和珅,不仅已听清,而且已明皇上之意了。
这是出自《论语》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是乾隆下了一道委婉的口谕,意思是要查办这位要犯典守者的过失罪。照理,领侍卫内大臣阿桂应对这道口谕做出反应,再通知军机处拟旨查办此事。然而,众人却毫无反应。和珅虽然明白皇上的意思,但碍于自己的身份,也不敢随便在诸位高官和皇帝的对话中插话。
这样一来,议事厅内显得十分寂静,大家猜不透皇上这句话的意思,不解皇上的心思,所以,包括阿桂在内的诸位大臣,都显得一脸茫然,连大气也不敢喘,生怕皇上发怒殃及自己。
“怎么,你们都哑巴了吗?为什么一声不吭?”乾隆见无人响应,方才的愉悦心情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他怒声问道。
阿桂见乾隆发怒了,当即跪倒在地,大胆说:“皇上,微臣素常疏于学习,孤陋寡闻,实不懂得您所说是何意,切盼皇上明示!”
乾隆一听,发怒的脸色顿时换成了笑脸,说道:“亏你们都是钦点的举人、进士,都曾自诩满腹经纶,如此看来,才学各个不实!”
听皇上这么一讲,大家马上一起跪下,口称:“皇上恕罪,臣等学识浅薄,着实不懂其意,望乞皇上指教!”
“看来,我朝实无读书之人了,除了你们以外,不知谁还懂得此话之意?”乾隆非常着急地问。
此时的和珅,见到阿桂冷汗直流,他开始担心起来。因为自己的太岳父英廉与阿桂素来亲密友好,“是亲三分相”,阿桂如果受到责罚,和珅总觉得于己不利。所以,他在后面斗胆一喊:“皇上,奴才知道!”
乾隆一抬头,又是那个侍卫,于是将和珅招致跟前,微笑着问:“朕问你,此话何意?”
和珅不紧不慢、沉着地回答:“圣上是说典守者不能推卸其责任!”他的声音并不大,一来是从未在如此多的高级官员面前说过话,二来是怕惊扰了皇帝的思绪。
“哦,你说说此话的原意和出处!”乾隆见这个并不起眼的侍卫有超出众大臣的才华,实感意外,所以高兴地让和珅继续说下去。
见皇上很高兴,和珅这才放心地走上来,跪在乾隆面前说:“此言出自《论语·季氏》,原文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可解释为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也就是说,看守的人有不可以推卸的责任。”
乾隆听完,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看你们,平常都是自诩为饱学之士,而今天,却让一个小小的侍卫占了上风,连朕都替你们脸红!”
从此以后,和珅被乾隆招到跟前,两个人经常彻夜长谈,感情越来越亲密。和珅这个没毛的凤凰,终于起飞了,飞到了乾隆朝代的顶层。
有了职务,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官威。有了官威的和珅,志向已遂,自己也就该露出峥嵘之像了。这个“峥嵘之像”,典型的表现,当属整治李侍尧的案子。
李侍尧,字钦斋,祖籍辽东铁岭,原为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家被纳入汉军镶黄旗。他是明末名将李如柏的后代。明末,其四世祖李永芳镇守抚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初,在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抚顺时投降。努尔哈赤念其有功,授予他三等副将官衔,并把自己的孙女下嫁给他,因此李永芳又叫“抚顺额驸”。李永芳此后屡立战功,及至李侍尧的父亲李元亮,更是做过户部尚书这样的高官。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李侍尧也是八旗旧臣的后裔。乾隆八年(1743年),李侍尧荫得印务章京一职。
李侍尧此人,个子虽然不算太高,长得却精明强悍,才智过人,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即被破格提升为副都统。当时曾有人提出这样提拔有违先例,乾隆却说:“他是李永芳之后,李永芳曾建立大功于我大清,如此安排,正是安当其用,有何不可?”皇上如此说,谁还敢再有异议?后来,李侍尧先后又转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等职,期间颇有政绩,建树较多。
及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侍尧升任代理两广总督,三年后正式实受。广州历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广州是中国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一切贸易均由洋行(俗称“十三行”)经营。而“十三行”商人若想保持其垄断地位,就必须向广州地方官行贿、献纳,否则难以得到官府的支持。所以,两广总督一职一向是个发财的肥缺。
此后,李侍尧又历任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他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干了15年,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与缅甸交涉事务繁多,始调任云贵总督。
从李侍尧的仕途履历可以看出,乾隆让他长期担任肩负对外交涉事务的两广总督一职,自然是承认李侍尧的才干。当然,还有一个人们不知的原因,就是李侍尧每年向朝廷进贡最多,花钱如流水的乾隆自然对他非常喜欢。乾隆曾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称赞李侍尧,说他“由将军至总督,历任各省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干练,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能让皇上当着众大臣的面夸奖的人,所受的礼遇自然不一般。
人们都爱犯一个毛病,那就是一旦受到上司的宠信,就容易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尽管李侍尧才高八斗,聪慧过人,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他认为,皇上如此看重于我,就是见我有功于朝廷,既然如此,我还怕谁?再说,自己已在两广经营了十几年,两广的地方官员、广州“十三行”的官员,都是经我一手提拔任命,各方关系通畅无阻,一切都可安全无虞。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想法,才导致他成了目空一切的高傲之人,在情面上伤了皇上的顶级红人和珅,险些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春节,在两广任职的李侍尧回京述职,进入皇宫,正好与刚升任乾清门侍卫、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的和珅相遇。和珅看到这个身穿绣龙图袍、头顶矢鸡翎的李侍尧,走路慢条斯理,一幅旁若无人的样子。
和珅见到他,马上像其他人一样上前问好。谁知这个李侍尧早就听说和珅是靠着巴结成了皇上的红人,心中非常瞧不起他。当和珅向他问好时,李侍尧只是轻蔑地看了和珅一眼,待答不理地“哼”了声,便扬长而去。直弄得猫着腰等着回话的和珅在众人面前满脸通红,十分尴尬。
李侍尧走后,和珅恨恨地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老头,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后来,和珅随着步步升迁,不论职务还是地位,都比李侍尧高了许多,以后见到李侍尧,和珅也都是脖颈高扬,视若不见。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云南粮储道并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被任命为沈阳奉天府尹,来京述职。按惯例,皇帝均要询问一下该省地方大吏的一些表现。
乾隆问道:“朕问你,你处的官员表现如何?”
站在下面的海宁俯首回答道:“回皇上话,大部分人员都很廉洁奉公,遵章守法!”
乾隆一听海宁话里有话,继续追问:“如此说来,还有部分官员就不是这样了?是谁这样违抗朕命,不守戒律?”
海宁知道,乾隆向来对贪赃枉法之人嫉恶如仇,现在一听皇上来了气,马上回答:“主要是总督李侍尧,居功自傲,收受贿银,营私结党,诸多官民多有不平之语!”
乾隆听完,把龙书案一拍,厉声又问:“海宁,所奏可是事实?朕一向待李侍尧不薄,他真的就敢违逆朕命,大搞贪赃枉法?”
海宁立即跪下,言之凿凿地说:“下官不敢欺骗皇上,我以性命担保,句句属实!”
“和珅,你身为吏部尚书,李侍尧如此胆大,违抗大清戒律,你是知情不举,还是根本不知?”乾隆真的生气了,他又把火气发到了和珅的身上。
和珅马下跪在地上,说道:“皇上息怒,奴才倒是听说过李侍尧贪赃不择手段。本想向您启奏,却又怕使您烦恼,龙体不安。奴才本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启奏,今日海大人提出,奴才明日就派人前去调查,弄清后……”
没等和珅说完,乾隆马上发话:“好啦,好啦!等你弄清什么都晚了。和珅,明日你带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去赴云南处理此案,如属实,立即将他带回,交由刑部审理。”接着,乾隆又令户部尚书英廉、军机大臣福隆安等在京查抄李侍尧在京的财产。
这时,正是正月十五,繁华的京城过年的气氛尚未退去,家家户户的门口张贴的福字与对联十分醒目。新挂起的大红的灯笼,随着“嗖嗖”刮来的西北风,不停地悠荡。别离了英娘的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带着八个侍卫,每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风驰电掣地向西南方奔去。
一路上,他们晓行夜宿,过黄河,穿长江,跨丛林,钻深山,尝尽了艰辛,走了一个月的路程后,终于到达了云南昆明。
来到昆明街上,和珅、喀宁阿等人并未直奔总督府,而是找了个驿站住下。因为李侍尧是这里的“土皇上”,又是乾隆的眼中红人,在发迹利益上又和皇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的行动必须谨慎周全,谋划一个好的方案,好将李侍尧顺利拿下。
喀宁阿问和珅:“和大人,您见多识广,胸中多有韬略,说说怎么进行吧!”
和珅坐在上首的椅子上,把戴在头上缀有矢鸡翎的官帽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盘在头顶的乌黑长辫立即耷拉到背后的绣龙官服上。他听完喀宁阿的问话,胸有成竹地说:“咱先不忙着接触李侍尧,先把情况掌握清楚了再下手也不迟!”
“和大人所言极是,李侍尧倚老卖老,如果没有十足把握,是难以将他制服的。”喀宁阿接着和珅的话说,“不过,咱人生地不熟的,找谁弄清情况呢?”
和珅“嘿嘿”一笑,说:“这个并不困难。李侍尧有个管家,听说是他的心腹,一切事情都由他去办,要是先把他制服,还愁拿不下李侍尧!”接着,和珅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第二天,和珅带着一个侍卫,二人全都打扮成普通人,来到了李侍尧的总督府附近溜达。过了一会儿,看见有个送菜的从大门里出来,和珅走上前,问道:“大哥,你去总督府作甚?”
送菜的乜斜着眼睛,见不认得和珅,就没有搭理。和珅见状,随手掏出一块银锭,在此人面前一晃说:“大哥,先别走,只要回我的问话,这锭银子就是你的!”
送菜的一看,这锭银子自己送一年菜也挣不到啊!于是忙说:“你问什么?”
和珅又把这锭银子在手里掂了一掂,问道:“你是做什么的?总督府的管家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想必你都知道!”
送菜的回答:“我是常年给这里送菜的,常年和这里的管家张永寿联系。这人心黑,买菜时,经常克扣我的菜钱。他的住处就是前边那个黑色大门处!”
“这个张永寿长什么模样?他都是什么时间出门?”和珅问。
“这人40多岁,高高的个子,前几天跌了一跤,把右腿跌伤了,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他当总督管家非常尽职,每天早晨就去,直到天黑才回家。”
这个送菜的,不知就是这么个嘴大舌长的人,还是为了那锭银子,竟然一口气就把和珅问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
和珅把送菜人的话全部记住,伸手把手里的这锭银子交付他手,临走时告诫他说:“今天这个事儿,不许在外面瞎说,如果说了,不仅你的银子没了,恐怕小命也难保!”
送菜人听后,挑起菜挑子快速离开了。
隔了一天,和珅派了两个侍卫,打扮成当地市民模样,在张永寿家附近仔细观察,准备待张永寿回家,立即抓来审问。
果然不出所料,这天晚上八点多钟,天黑如墨,只有挂在豪门大户门外的灯笼,照映出微弱的亮光。时间不长,张永寿坐着一乘两人小轿,在自家门前停下。只见他一瘸一拐,下得轿来,刚想敲门,忽然从黑处闪出两个人,手拿明晃晃的大刀,小声喝道:“不许喊,跟我们走!”
立时的惊变,把张永寿吓得魂不附体,没敢出声,乖乖地跟着两个侍卫来到了和珅所住的驿馆。
进到屋中,张永寿看到对面坐着两个身着朝服的官员,只听一个侍卫高喊:“跪下!”
和珅见张永寿惊慌失措地跪在了地上,严肃地说:“不用说了,你是张永寿吧!”
张永寿哆哆嗦嗦地回答:“是,小人张,张永寿。请问老爷们,你们是……”
旁边的喀宁阿一拍桌案,厉声道:“告诉你,张永寿,我们是朝廷派来的命官,前来清算李侍尧的贪赃罪行。现在有话问你,不许隐瞒!”
喀宁阿说完后,和珅又接着说:“张永寿,你是李侍尧的大管家,他的事情你都知道,刚才喀大人已经说了,你要实话实说!”
张永寿毕竟是豪门的管家,惊慌一阵子后,马上镇静下来,心想:谁知你们是干什么的?还喀大人,扯淡,百家姓上哪有姓喀的?想至此,他扯着公鸭嗓说:“我是李大人的管家,不假。可李大人是朝廷命官,我仅仅是个管家,他的事情我哪里知道?”
张永寿一边说,两只眼睛一边望着座上的人乱转。
见此情况,和珅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你这个奴才,不用嘴硬,隔一会儿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说完,朝下边的四个侍卫挥了挥手。四个侍卫见和珅发令,就一拥上前,将张永寿按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直疼得他杀猪般嚎叫:“老爷们,饶了我吧,我说,我什么都说!”
就这样,张永寿把李侍尧在任几年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事情,全部都交代了,并且在自己的交代记录上画押签了字。而后,和珅吩咐把这个张永寿暂押进一间闲屋,待明日再做处理。
第二天,和珅、喀宁阿穿戴整齐,在四个侍卫的簇拥下,直奔李侍尧的总督府。李侍尧立即率人隆重迎接,躬身说道:“和大人,喀大人,下官不知二位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进了府内,李侍尧刚想问话,和珅却突然高喊:“李侍尧接旨!”
李侍尧慌忙跪倒。只听得和珅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由吏部总务大臣和珅、刑部侍郎喀宁阿,奉朕旨命,至云南总督府,彻查李侍尧贪污受贿一事,务须查清事实,不得有误,钦此!”
圣旨读罢,李侍尧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双手接过,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侍尧毕竟是个老臣,长期以来自恃有功,从不把别人放在眼中。他感到此事来得非常匆忙,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问:“和大人,喀大人,这是怎么回事?贪污受贿,从何说起?下官实在不知!”
和珅微微一笑,说:“李大人若是不知,看见一个人就知道了!”说完,喊了一句:“带上来!”
随着话落,两个侍卫把垂头丧气的张永寿带了进来。张永寿来到李侍尧面前,喃喃地说:“大人,您就别扛着了,我都说了!”
李侍尧见状,脸色立即变得如同一张白纸,知道再想抵赖隐瞒,只能于己不利。于是,他慌忙地又跪倒在地,口称:“下官有罪!”紧接着,如同竹筒倒豆子一样,将所犯罪行,全都交代出来。
和珅带来的一个文书,立即把李侍尧交代的情况全部清清楚楚地记录在纸上。只见上面写道:前年收受迤南道庄肇白银2000两、收受鲁甸通判素尔方阿四笔白银总共8000两;去年收受东川知府张珑白银4000两、收云南按察使汪圻白银5000两;今年收取临安知府德起总共白银10000两,其他首饰字画一部分。
喀宁阿是管刑律的,他拿过这张交代材料,看完后,叫李侍尧在上面画了押,又交于文书收好,然后,高声命令:“李侍尧已成罪臣,摘去他的花翎顶戴,脱去身上的官服,穿上罪裙罪衣,打入囚车,明日回京复命!”
和珅听完,挥手制止:“不行,皇上等着此案落实,哪能再等一天?咱们马上起程,不可耽误!”
和珅的官职比喀宁阿高两级,他的话在这里就等于圣旨,谁敢不听?于是,和珅将这里的总督府事务交给一个武官代管后,一行人就押着李侍尧回京了。
一路上,又是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一个半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
和珅向乾隆讲述了办案,乾隆又怒又喜:怒的是李侍尧如此胆大,贪贿数额竟如此巨大;喜的是和珅办事有方,没费很大力气就把这个贪官扳倒了,也实在是个奇才。于是,乾隆下旨,将李侍尧带回刑部重新审理,而后定罪。鉴于和珅有功,又提升他为领事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兵、刑部及内务府。就这样,和珅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此时,和珅又执掌了刑部大权,给李侍尧定罪当然就得他先决断了。按大清律,李侍尧的罪行,满可以定个“斩立决”,也就是立即执行的死罪。这对和珅来说,既合法,又遂心。想当年李侍尧不可一世,那么看不起自己,弄死他也是活该。可是,仔细想来,和珅又觉得这个李侍尧不能死,原因就是他也曾是皇上的红人,每次进贡,都有奇特之物送给皇上。这次李侍尧触犯了国法,向来最恨贪赃枉法的乾隆,是没法子开口给予开脱的。如果当时处死,皇上虽然嘴上不会说,但心中也会不快,这样对自己也是不利的。想至此,他又去找皇上了。
到了乾隆面前,乾隆问他:“李侍尧案件审得怎样了?如何定的罪?”
和珅跪在地上,向乾隆回话道:“托圣上洪福,一切都已审完,只是在量刑上,奴才还拿不太准!”
乾隆看着和珅,说:“起来吧,你已经掌管了刑部,怎么还拿不准定什么罪?”
“是的”,和珅站起来说:“奴才虽然有些知识,但毕竟初次接触这份差事,实是难定其罪!”
“那就按你初步的认定,说一下子吧!”乾隆又说道。
和珅心想,皇上也真够奸猾的,非得把我逼到墙角不可。于是,他说:“若论戒律,理应定个‘斩立决’!”
乾隆听后,平静地说:“那就定吧!”
和珅马上又说:“可是,这个李侍尧终究曾给国家做过很大的贡献,虽罪行严重,但量刑可以从轻,定个‘斩监侯’,留条性命,这样也好给其他做过贡献的臣子们一个警示!”
“那就这样吧!”乾隆随口答道。
就这样,一个应该掉头的大贪污犯,在和珅的操作下,成了一个“缓期执行”的羁押之人。
过后,乾隆从京城查抄出来的李侍尧的房产中,挑了一处巨大的宅院奖给了和珅,作为对处理这件案子的酬劳。
和珅在办理李侍尧的案子上,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全面快捷,使得乾隆越发对他信任与青睐。
由于办理李侍尧的案子,和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他得到了乾隆的准许,在家闲待休息几天。这天,风和日丽,春风荡漾,和珅和夫人英娘带着儿子小宝,即后来的丰绅殷德,来到府中的花园欣赏景色。
别看和珅此时的年龄刚满30周岁,可是却是已经官居一品,成了朝内的“二皇帝”,这样的人物,府院自然非常豪华。后院的花园,阔绰美观,假山绿水,楼台亭榭,丛丛绿树,鸟雀啁啾,芳香花草,蝶舞蜂飞。进得里面,不亚于人间仙境。和珅和英娘边欣赏美景,边说说笑笑,身旁的儿子小宝,英俊可爱,活泼喜人。正玩耍间,刘全忽然匆匆而至,说声:“老爷,快快回去,皇上来了!”
刘全说话声音虽然不大,却把夫妻二人震得不啻听得一个响雷。和珅不敢相信,忙问:“你说什么?”
刘全马上重复一遍:“老爷,皇上来了!”
“啊!”这下,三人一起往前院走去。
乾隆真的来了。
这日,乾隆把政事处理完毕后,刚叫了声“和爱卿……”,马上又停下了。他想起,和珅今日请了假。往日,和珅在时,都一喊即到,一些话语,都是一拍即合。现在和珅不在,就像缺了什么似的,这让乾隆很不习惯。
乾隆走出大殿,抬头看看天气,晴空万里,和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总归现已无事,不如去看看和珅在家做什么,顺便闲聊一下。于是,他轻装简从,让两个太监引路,直奔和珅府而来。
到了和府,刘全及一众人等慌忙跪倒接驾,乾隆忙招手叫他们起来,问道:“和珅在哪里?怎么不出来见驾?”
刘全赶快回答:“回皇上,我家大人刚去了后花园,我马上去叫!”说完,一路快跑,将和珅唤回。
和珅还没进得门内,就在外面高喊:“皇上驾到,奴才不知,望乞恕罪!”话落人到,“咚”的一下跪在地上。
乾隆哈哈一笑说:“和爱卿好心情啊,快快起来!”
和珅迅速起来,不知皇上来此何意,故意说:“皇上屈尊来此,奴才实在诚惶诚恐,有事情何不令人来唤?”
乾隆又是一笑说:“爱卿不必惊慌,朕今日无事,总想看看你的宅邸,今日一见,真是与众不同!”
“皇上夸奖了,寒门陋室,您这么一来,真是蓬荜生辉了!”和珅一句话,又把皇上说得满心欢喜。
二人边说,和珅边把乾隆引进厅堂落座。刘全此时早把香茗沏好,二人各自一杯,慢慢地饮了起来。正说着话,和珅的儿子忽地跑了进来,和珅顿时严肃起来,说声:“刘全,快把少爷带走!”
“等等”,乾隆放下茶杯,打住和珅的话,问道:“娃娃,长这么可爱,芳龄多少?”
没容和珅回话,小孩痛快地答道:“我叫小宝,六岁!”说完,歪着个带着小辫的脑袋,毫无恐惧地看着乾隆。
乾隆毕竟是万乘之尊,一国之主,一个小孩竟敢随随便便地与皇上说话,太不像样子了!和珅惊得脸面突变,刚想训斥,不想乾隆将他制止住,说:“小宝聪明,这点非常像你!”而后,方挥手叫刘全将孩子带走。
和珅还在不安之时,这边乾隆又问话了:“小宝年已六岁,可有学名?”
和珅赶紧回答:“回皇上,因奴才事务繁杂,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
乾隆略一思索,说:“那好,朕给他取个如何?”
和珅一听,又是一恭到地,忙说:“承蒙皇上恩典,来给孩子赐名,实是我家祖上有德,家门大幸!”
“就叫丰绅殷德吧!前边那个‘珅’字,与你那个‘珅’字,意相近,形不同,有继承和丰富你的前程之意;后两个字,既喻大福大贵,又嵌福禄长存!”乾隆不愧为才华横溢的帝王,名字取得相当得体和贴切。
和珅听罢,慌得跪倒,口呼:“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不仅是小儿与奴才的大幸,就是地下有知的祖辈,也得感谢皇上的恩德!”
“起来,起来。”乾隆把和珅唤起来,接着说,“朕还有一意,朕宫中的最小的女儿固伦和孝年纪与你儿相仿,干脆就把她许与丰绅殷德为妻,待过几年将她敕封公主后再行完婚!”
乾隆此言一出,更把和珅说得又惊又喜,自己与皇上成了儿女亲家,今后权倾当朝,还能怕谁?于是,他又叩头拜谢。
腊月一过,转眼就到了正月。每年的正月,乾隆都要带着几个后妃与子女,到圆明园一带去逛街。当然,每次不可能缺少和珅相随。
这天,他们来到位于福海东岸同乐园附近的买卖街,这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擦肩摩踵,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都到这里参加交易活动,显得格外繁荣与兴旺。两旁的店铺,有卖古玩玉器的,有卖生熟药材的,有专卖西洋货的,还有酒楼茶肆,饭店旅舍,各个张灯结彩,靓丽辉煌,迎接着前来购物的客人。
工夫不大,乾隆一行人来到一家卖衣服的店。乾隆不爱逛衣服商店,可是刚想走开,跟在旁边的小公主不干了。她刚满10岁,正是爱好穿戴的年龄,见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彩色衣服,说什么也不走了。她拉住乾隆的衣服,嚷着说:“皇阿玛,我要买个花褂子!”
这时,后面跟着的一个老太监,伸手去拉她,说道:“小公主,你已经有许多衣服了,就别买了。”
“不嘛,你去,不要管我!”小公主撒娇地说。
老太监见她这个样子,无奈地站在一旁。这时候,和珅来到她的面前,拉起小公主的手说:“别急,你要买哪件?”
小公主见和珅来了,就说:“和胖子,你给我买一件吧,我要记你一辈子的!”
到底是个小孩,不仅任性,说话还这么难听。没办法,人家再小,也是个公主。和珅一笑,说道:“好了,记不记得都没什么,你挑一件,我来给钱!”
乾隆一听,笑一笑说:“朕的孩子买东西,哪能由你付钱?”
和珅一笑说:“皇上,公主买多少,我都应该出钱!”
最后,小公主挑了一件式样新颖、面料昂贵的褂子,和珅见了,就去问价钱。
掌柜的是个精明之人,见到有人主动巴结公主,就是要的银子再多,他也不会讲价。此时不黑他,更待何时?于是,他嬉笑着说:“公主买衣服,按说不应要钱,可这样怕有损皇家的名誉。今天和大人出钱,我更不能多说。这样吧,我折个半价,就给2000两银子吧!”
小公主才不管钱多钱少,听见和珅前来说话,马上吵闹起来:“我就要这件,这件最好,和胖子,你快拿钱嘛,我要买!”
见小公主如此态度,和珅想不买都不行了。他本想讲讲价钱,可是旁边有皇上,小公主又吵又闹,若真的与这个掌柜的争论起价钱来,反而显得自己身价太低了。
于是,和珅“哈哈”一笑说:“只要公主喜欢,还讲什么价钱,快把衣服拿来,给你钱!”说着,从长袍下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2000两银子的银票,递了过去。
小公主拿到衣服,高兴地跳了起来:“皇阿玛,和胖子给我买褂子了!”
乾隆看后,也高兴地说:“好啊,和珅花这点钱,好比九牛一毛,就是把这个店铺都买下来,也无关大碍!”
乾隆这句玩笑话,在其他人听来,都作耳旁之风,轻轻吹过。只有和珅自己听来,心中骤然形成一道阴影:我的家财积蓄情况,难道皇上心中有底?这几句话,皇上是无意之中的信口开河,还是有意为之?和珅的胸内,如有几只小兔子,扑腾扑腾地跳了起来。
为了让乾隆打消对自己的疑虑,更增加皇上对自己的好感,牢牢靠住皇家这棵大树,和珅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把兄弟和琳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的孙子锦庆。
这个锦庆是乾隆六子永瑢的儿子,小伙子相貌英俊,能文能武,比和珅的侄女虽大十来岁,但攀上皇亲国戚,对自己和家族来说总是一个保障。另外,因为自己的儿子已经娶了乾隆的女儿和孝公主为妻,现在把自己的侄女嫁过去,更是好事一宗。再说,两边已成了双重亲家,与皇上有了这么多的瓜葛,和珅在朝里还能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