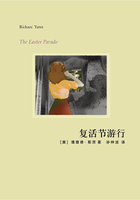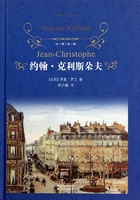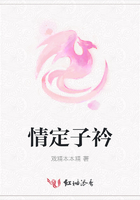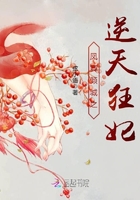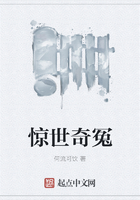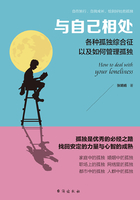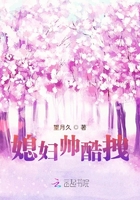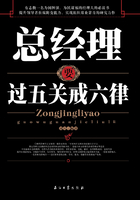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创作具有普遍影响,童年经验或构成作家重要的审美资源,或对他们的创作起着或显或隐的影响与局限。毕飞宇的文学创作与其童年经验是密不可分的。毕飞宇出于1964年,他的童年时期是从1967年开始到1979年的这段时间。文艺心理学认为:童年经验即“童年体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它包括童年时代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和意志等。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毕飞宇对童年经验的书写现象具有普遍与典型的意义。在毕飞宇的文学作品中,采取童年视角或是以童年经验为背景的作品占的比重很大,如作品《那个男孩是我》、《怀念妹妹小青》,而以“文革”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有《玉米》、《玉秀》、《玉秧》、《平原》等。总的来看,童年记忆对毕飞宇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种姓”问题,“祖坟”问题,“方言”问题和“文革”问题。
第一节 关于“种姓”
毕飞宇曾说,“我父亲的养父是1945年枪毙的。我的父亲其实是孤儿,除了我们的一家五口,我们一家四面不靠。我其实不姓毕,至少我的父亲不姓毕,他的原名叫陆承渊。1949年以后他姓毕了。”[1]
可以说,种姓的遗失,构成了毕飞宇童年生命经验中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感造成了自卑感,“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伴随着自卑感。”[2]“灵魂在自卑感的压力下,会使个体备受无助、痛苦等想法的折磨。”[3]自卑感与缺失性生命体验相遇,加剧了毕飞宇童年经验中的痛苦。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体验,也赋予了毕飞宇充盈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感受力。这种由于种姓的不确定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在毕飞宇文本中经常出现。《叙事》中有这样的语句:
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我的父亲,产生了我,产生了我们家族的。
一种生命种姓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死亡。
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突难。
《叙事》这一文本中的种姓屈辱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文化屈辱——坂本六郎是以侵略者的身份强占陆家,并奸淫了“我”的奶奶婉怡。所以“我”的父亲、“我”,还有“我”的妻子林康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都已被这种文化屈辱统摄,无所逃遁。第二重屈辱是“欲望”的屈辱。奶奶虽是被奸淫,但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性快感。这种来自生命本能的欲望,在文化侵略的语境中,便具有了非理性和非法性,这种屈辱也将统摄“陆”姓。毕飞宇将种姓问题加入了文化侵略因素,加深了种姓的屈辱感。这使得种姓屈辱有了更深层的意味。这种深层意味就体现在父亲曾经想杀死“我”,“父亲的存在只意味着家族生命的一件事:到此为止。”生儿育女是父亲不敢正视的事情。这意识也在“我”身上体现出来,当“我”了解到种姓的全部屈辱之后,“我”便和父亲一样,想终止如此“种姓”的延续——想毁灭林康腹中的生命。一代代的陆姓人,都难逃种姓与文化这种可怕错位带来的屈辱感,无可断绝,而唯一的断绝方法就是停止生命延续。毕飞宇因种姓缺失而产生自卑感等生命体验,由其充盈的文学想象来填补,在文本中,毕飞宇极力展示种姓的屈辱,继而选择决绝的态度与种姓断绝,但这种断绝往往归于枉然,除非死亡。
除了《叙事》这一文本外,种姓带来的屈辱感在毕飞宇其他文本中也被提及。但都没有《叙事》中传达得强烈,与种姓决裂的态度也没有《叙事》坚决。大多作品都是将屈辱感转嫁到作为种姓传递者的父亲身上,具体体现为子辈对父亲的不满、怨恨或嫌弃。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主人公耿东亮把对父亲的怨恨转移到猪的身上去了,他不愿意再吃猪肉不愿意再涉及有关猪的一切。耿东亮的父亲在肉联厂工作,在进城之前是个屠夫。父亲的父亲,也是屠夫出身。耿东亮对父亲以及一切有可能与种姓发生关系的事物,采取或回避或逃离的态度。在《睁大眼睛睡觉》中,“我”的父亲是打渔的,通身弥漫着咸鱼气味。这个咸鱼气味,是“我”始终想要摆脱的。“我”厌弃那股咸鱼味——“九年里头我的父母没有到釆石场看过我一次,谢天谢地,我再也不用闻他们身上的咸鱼味了”;“父亲把一身的咸鱼气味留给了我,这让我抬不起头来”。但是无论“我”无论如何努力出逃,“我”始终摆脱不掉咸鱼味的追捕——当“我”的脑袋被马钎提在手里时,“我睁大了眼睛,我看见我的咸太阳升起来了,它的光芒全是咸鱼的气味”,至死,“我”都无法摆脱咸鱼气味的追逐,这是种姓的传承,如影随形。这里,毕飞宇借父亲书写表现无法逃遁的种姓屈辱感。
在毕飞宇的另一些作品中,种姓的荣誉感被提及,荣誉感产生使命感。但种姓赋予的使命却与个体生命主体愿望相背离,在这种背离中,个体生命被扭曲,个体既不能实现种姓使命,也不能完成自己的愿望,在此扭结挣扎,个体生命逐渐衰落直至死亡。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有类似的意义表达。主人公红豆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英雄,英雄的称号赋予“家族”至高无上的荣誉,这种荣誉感衍生出“必须是这样”的使命感,父亲希望能够“龙门出虎子”,希望儿子能威风八面。但是红豆却令父亲生气,甚至是绝望。文本中这样表述,“红豆不喜欢父亲。红豆看不见悲壮与英勇,看见的只是凭空高出的背部和空空荡荡的袖管。”红豆并不因为英雄荣誉而对父亲产生敬仰之情,他不但不崇敬而且不喜欢,甚至不理解——他不理解父亲对战争的痴迷,不理解父亲对死亡的毫无畏惧,不理解他的“没有眼泪,没有胆怯,没有感伤,没有后退”。红豆说,“我不是人,要么他就不是”,父亲说,“你不是我的种,我没你这个儿!你不是烈士,你活着干什么”,这是父子间的分歧。小说中的红豆只爱二胡,他生命的全部意义都系在了那几根弦上,而与之相应的是他的性格,他自娘胎里带出的是善良、忧郁与柔弱。这样的性格在这样的“英雄”的家里,注定是悲剧,红豆能怎么办——唯有一死。
生命绝对不可能顺应某种旨意降临你。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样的生命却又由不得你。你只要是你了,你就只能是你,就一辈子被“你”所钳制、所固定、所追捕。交换或更改的方式只有一个:死亡。
在《雨天的棉花糖》末尾,红豆选择了“死亡”,他要杀死那个种姓赋予的“应当成为”的红豆,而他始终未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红豆。
对毕飞宇而言,父亲便是种姓家族的唯一象征。父亲在毕飞宇的童年记忆中是沉默的——“我的父亲特别寡言,除了逼着我学习,从不和我谈,他几乎不说话”。[4]日常生活中,父亲除了干点农活之外,便是教书。这样的父亲形象,作为一种原型形象,也进入了毕飞宇的文学书写中。但这父亲形象,“不是真实的、直接的反映,而是变形了的或曲折隐晦的表现”。[5]父亲形象在进入文学文本后发生了变化,他保留了沉默寡言的特征,也增添了理想化因素。在毕飞宇的小说中,父亲形象也演变为强悍的兄长形象:年龄偏大且长相与父亲酷似,性格彪悍,说一不二,能体现种姓权威。这类兄长形象弥补了毕飞宇文本中父亲形象在精神气质上的羸弱。在《叙事》中,父亲这样被书写,“父亲能和每一位老鼠悄然对视,长幼无欺。父亲一连几个小时望着他们,给他们读书读报,为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开斗争大会,批判毒蛇与黑猫”。这里的父亲是封闭的、沉默的、寂寞孤独的,也是忧愁的。与此对比,《白夜》中的父亲却有着“积极的”教育理想,他耗费心力劝乡里人把孩子送来读书。当被问及“上课时说的话哪一句比麻雀肉香”时,父亲的回答是,教育能使人不至于长成“浑身长毛的麻雀”。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有本事你让我浑身长毛,我现在就飞到田里去吃虫子”,父亲沉默了。即便没有教育,人也不可能变成麻雀,打麻雀只为不被饿死,教育不能立即转变为粮食用来果腹,这是教育的无奈。这里,父亲的沉默表现了他精神上的羸弱。《大热天》和《哥俩好》两个文本中都有对兄长形象的描绘——“光头怕大哥,这种惧怕刻骨铭心。大哥光头近二十岁,年纪与长相都像光头的父亲”;“他从来就不是图南的弟弟,而是儿子”,“大哥图南像父亲一样凝视他”。无论是光头的大哥,还是图北的大哥图南,都被种姓的使命感驱使,将这份使命不容置疑地传承性地强加在弟弟身上,他们实质上是父亲的另一种书写,是种姓权威象征的另一种代表。
在毕飞宇的童年经验中,父亲没有给予他生活上的关心与抚慰,更没有给予他成长过程中的解惑与引导。父亲似乎被一种无形的气场裹挟、压抑着,再也无心于周遭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唯一的儿子。于是,毕飞宇从童年经验中汲取的对于父亲这一形象的最初感受就是隔膜,无法走进,于是永久性地退却。这种深切的隔膜感进入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在文本中呈现出子辈对父辈的疏离感、陌生感。在《白夜》中,有这样的意思表述,“我”最终举起弹弓,实则是对父亲的背离,“我”从本质上就是不理解父亲的。在实实在在的饥饿感面前,“我”与父亲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写字》中,“我”对汉字习得的过程,正是父亲主导下“我”的童年走向末路直至结束的过程。这种与父亲的疏离感、陌生感也统摄着毕飞宇笔下的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充斥着紧张与胁迫的情感氛围,如上述文本中光头对大哥的忌惮,殷图北对殷图南的恐惧等。
综上所述,种姓的遗失和困惑是毕飞宇童年记忆中影响其文学创作的显著因素,种姓的遗失带来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在作品中,要么直接表现为语言话语,要么表现在种姓赋予的使命感与生命主体的背离,以及与代表种姓权威的父亲或兄长形象的疏离。
第二节 关于“祖坟”
寻祖坟未得是毕飞宇另一个重要的童年经历,这一童年经历对毕飞宇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对“乳房”意象的把握以及对“哺育”这一情节的书写。祖坟对毕飞宇而言,也意味着故乡。祖坟意味着家族源流的存在,是一个家族存在印记的证明。但是,在毕飞宇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属于他的祖坟,他的根系,他的全部根系就只有立于他眼前的父亲。童年时,别人家清明时的祭祖上坟,便构成了毕飞宇生命最初的疼痛——
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故乡,也没有祖坟。每当到了清明节,看到别人到坟上祭拜我就感到特别好奇,经常跟过去看。我还经常到坟地看人家烧七。
遍寻祖坟未得而生的失落与惶惑情绪,成了毕飞宇童年无法释怀的情结,这成为了毕飞宇童年经验中的创伤性体验。而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其生命体验的外化过程。弗洛伊德说,“创伤性经验作为作家潜在的创作动力”其迹化过程在文学文本中的展现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表露在作品中;另一类则是通过补偿或变形的方式,反向表露出来”。
在毕飞宇的作品中,这种童年创伤性记忆主要体现在《雨中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和《婶娘的弥留之际》。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有这样的话语表述,“坟是泥土的乳房,我们的家”。当红豆痴迷于曹美琴的乳房时,他的心理独白是,“这才是我的家,我什么也不怕了”。坟,是大地上的一堆堆隆起,坟的这一形态特征,在毕飞宇生命初年创伤性童年经验的作用下,被视作乳房。乳房这一意象的情感指向是母亲,是母性,是生命的原初,是生命的来处。乳房是家,它带着生命诞生之初的体温,默默凝望并守护着另一个生命的成长。而坟又是生命的归处。因此,毕飞宇对乳房这一意象的书写,寄予了他对家族,对根系的追问与想象。它既意味着哺育,指向生命的延续,家族的繁衍,又意味着生命的消逝,唯一的归属。毕飞宇对于家族的依恋这一充盈的情感冲动,在刻画乳房这一意象时得到了释放。乳房也意味着哺育,在毕飞宇文本中多以“喂奶”这一场景来呈现。喂奶的场景往往传达出“儿子”对母亲的依赖与迷恋。因迷恋“喂奶”情景变得美好神圣,这在《哺乳期的女人》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惠嫂的乳房硕健巨大,在衬衣的背后分外醒目,而乳汁也就源远流长了,给人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印象。惠嫂给孩子喂奶格外动人……旺旺一直留意惠嫂喷奶的美好静态。惠嫂的乳房因奶水的胖胀洋溢出过分的母性……旺旺坚信惠嫂的奶水就是天蓝色的,温暖却清凉。
旺旺对惠嫂的乳房极度迷恋,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只能服从于渴求母亲、渴求母爱的本能,而用尽全力一口咬住了惠嫂的乳房,“咬住了,不放”,要不是惠嫂的尖叫,“旺旺肯定还是不肯松口的”,相应的,母亲也倾其所有,回应着“儿子”的依赖与迷恋。当别人纷纷指责旺旺的行为时,惠嫂的泪水“泛起青光”,“像母兽一样凶猛异常”地吼叫。这体现了惠嫂偏执、疯狂但却异常纯粹的母爱,也是毕飞宇对祖坟未得创伤性童年记忆在作品中的变形补偿。除了《哺乳期的女人》,《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也有类似的意义表述,主人公耿东亮是“吊在奶头”上长大的孩子,耿东亮吃母亲的奶水一直吃到五岁。“……母亲总是不用声音回答的,而是把上衣上的第二只扣子解开来,托住自己的乳房,把乳头放到儿子的嘴里去……母子便俯仰着对视,幸福得只剩下母乳的灌溉关系。”
如前所述,乳房这一意象的原型是坟,而坟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因此,在毕飞宇的创作中,乳房也暗示着死亡的召唤与降临。这种死亡或体现为儿子的消逝,或体现为母亲的绝望或失落。《雨天的棉花糖》中有这样的对话:
妈,我饿了。
我给你做。
妈,我要喝奶。
红豆妈钉在了那里,不动。
在红豆最后一次呼唤母亲,渴求奶水之后,他踏上了生命逝去的道路。而红豆的母亲只能在儿子的日趋疯癫中一遍遍体味无力回天的绝望。她只能目送儿子走向生命的终结,在深切的无奈与无力中,再一次体会那份来自生命诞生之初的撕心裂肺的痛。
在《婶娘的弥留之际》中,婶娘一生无子,她把“我”——小三子,当作亲儿子一样对待。在生命的末年,她忘了所有人,却从不曾忘记她想要拥有孩子的渴望。她想做一回母亲,哺育生命。“婶娘哭着说:‘乖,喝妈妈一口奶’,婶娘的手抬起来,要解她的前襟了。我慌忙摁住她的手,婶娘却无端地固执起来,‘喝妈妈一口奶’”。“我”拒绝了婶娘,这使“我”不堪面对她,只能逃离,在“我”离开之后,婶娘又多了一个毛病,“她动不动就解开上衣,让自己的乳房喝另一只乳房的奶水”。在这之后,很快就传来了婶娘的死讯。婶娘带着毕生的遗憾走向了死亡。祖坟是故乡的标志。毕飞宇童年经历中失去家族,寻根觅系而未得的怅然与伤痛,在其对乳房意象的刻画与书写中得到代偿。
第三节 关于“方言”
童年经历中的方言使用使毕飞宇表现出对周围环境的疏离和格格不入。方言,成为毕飞宇看待自身与外界的重要参考因素。毕飞宇23岁进入城市之后,方言便成了他书写城乡差异、城乡冲突的独特角度。在毕飞宇的文学创作中,方言有多重含义:方言是一种身份认同,指向生命的来处;方言亦是一种情感标志,指向对故乡、对土地的归属。
对毕飞宇而言,方言就是故乡之所在。这依旧是其童年经历的展现。在《充满瓷器的时代》中有这样的表述,“王五和他的老婆是外地人,他们带给秣陵镇的贡献是:‘方言和王五老婆白嫩的皮肤’”。“王五仿学秣陵镇的口音过犹不及的时代就是他被秣陵镇认同,但同时又无疑是外乡人的这段时间”。在《哥俩好》中,模仿小镇口音并不能换来小镇人的认同,相反会确认自己的外乡人身份。这里,毕飞宇向我们昭示了进城的艰难,这艰难不在于物质生存,而在于城市身份认同的获得。模棱两可的“外乡人”方言,彰显了身份认同的艰难。“他(殷图南)的语调里没有半点断桥镇的乡间口音,他早就能够正确区分‘Z、C、S’和‘zh、ch、sh’了”,殷图南背弃了他的方言,他的断桥镇,他的故乡,他寄希望于弟弟殷图北,尽其所能供弟弟接续家族的传统,但却一切枉然,在文本的最后,“故乡一步一步得被送进棺材”,故乡永恒的失落了。在《生活在天上》上,“她(蚕婆婆)的五个儿子分散在五个不同的大城市,个个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
蚕婆婆不喜欢普通话,蚕婆婆不会说普通话……就想找个人大口大口地说一通断桥镇的话。和儿子说话蚕婆婆总觉得自己守了一台电视机,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中间隔了一层玻璃。家乡话那么好听,儿子就是不说。家乡话像旧皮鞋,松软,贴脚,一脚下去就分得出左右。
《生活在天上》用对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话语的选择,来彰显城乡隔膜与冲突。蚕婆婆是断桥镇人,她的五个孩子都是土生土长的断桥镇人,在进城之后,他们接受城市高等教育以及城市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后,都无一例外地背弃故乡,放弃了断桥镇的方言,说起了普通话。这意味着他们对故乡身份的决然放弃。他们斩断了对故乡的感情,希望自己能完全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但是对城市的主观融入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小说最后这样描述困在茧中的蚕,“它们扭曲着,像忍受着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它们唯一需要坚持并需要完成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吐干净”,这是对五兄弟的真实生命写照。
毕飞宇小说中还有另一种方言出现的情境,这一情境中的方言意味着对家园、故乡身份的认同与维护。在这里,当方言与普通话世界发生冲撞时,主体也仍然不动摇对方言的坚守,这里体现了强烈的故乡归属意识。在《祖母》中,有这样的话语表述,“太祖母听不懂家园方言以外的任何语种,乃至电波传送的普通话”,还有,“我看见我的家族排着长长的队伍螺旋状款款而至。他们用我的家园方言和家族遗传神态向我招呼”。太祖母始终坚守着家族方言,这坚守贯穿她的生命。在《叙事》中,毕飞宇如是说,“人类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家园方言,也就是地图上那一块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着家乡方言向四周辐射的语言变异”,她(“我”奶奶婉怡)老人家用最纯正的楚水方言梦,见了多年以前。《叙事》叙述的是“我”对奶奶婉怡的追寻,实际上也就是“我”对家园、根系的追寻。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对家园方言的痴迷与坚定,“我”在梦中梦见的是奶奶依旧操着“最纯正的楚水方言”,并以家园方言回忆从前。这种执拗的坚守左右着“我”的世界观,暗示着“我”对家园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方言的另一种表现在毕飞宇小说的“进城”故事中。外乡人带着有别于城镇的方言进入城镇,然后在城镇中慢慢地放弃方言。这种放弃的结局是要么外乡人销声匿迹,要么是外乡人永远再不能回到故乡。这样,进城便意味着永远的失落与漂泊。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说,“而惠娴也开始用里下河一带的方言与人打招呼了……”这里,惠娴放弃自己的城市普通话,不是因为“被改造”的成功,而是乡村带给她的毁灭性绝望,在被奸污与被威胁后,惠娴不得不接受与乡村的联姻,不得不屈服于乡村的蛮力与权利,向耿长喜低头,向耿书记服软。这种屈服表现在语言上的顺从,向方言示弱。值得注意的是,惠娴与耿长喜的婚姻始终存在着隔膜与冷漠,表达着惠娴对方言本质上的难于融合。在《玉秀》和《玉米》中,都有对于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描写,“玉秀已经开始让郭左教她说普通话了。《玉米》中,“玉米和彭国梁已经开始交谈了,玉米有些吃力,因为彭国梁的口音里头夹杂了一些普通话”。这里无论是彭国梁与玉米,还是郭左与玉秀,他们的爱情都存在着危机,毕飞宇在这里是以“普通话”和“方言”的交谈障碍,暗示着他们的恋爱关系中的障碍与危机。
第四节 关于“文革”
毕飞宇的启蒙教育发生在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文革”时期。毕飞宇说,他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是“专制意识形态教育”,它始于1969年,中心词为“听话”,底色是“万岁”,“揭露”、“打倒”、“批判”、“推翻”等攻击性语言构成了毕飞宇启蒙教育的关键词,而“毛主席万岁”式的呐喊口号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是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最富代表性的宣传形式。“文革”时期的阅读启蒙环境对毕飞宇等一代作家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苏童就曾说过:
我出入学堂是在1969年秋季,街上的墙壁到处都是标语和口号。我生平第一次写下的完整句子都是从街上看来的,有一句特别抑扬顿挫:革命委员会好。[6]
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神秘和敬畏之感充斥着他们的内省,他们需要了解世界,最终也会去掉世界的神秘感,但这个过程是需要成人的有效引导的,成人应该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但“文革”阶段,这样的过程被简化甚至歪曲了,满街的标语和口号教会了孩子们的只是“万岁”、“打倒”,“文革”意识形态告诉孩子们的只是人与人的相互倾轧。社会危机潜伏于此。“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是尤其危险的,因为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沃丁顿也认为,“人类进化和选择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人类的儿童有能力接受长辈的权威和他们对是非的判断价值。没有那样的保证,儿童会发现怀抱希望、充满勇气和表现纪律是很困难的。”[7]“文革”时期的童年经验给予毕飞宇的启蒙读物是“大字报”和宣传标语,这些“大字报”和宣传标语以及漫画等阅读启蒙的“教材”充斥着粗俗、肮脏、愤世嫉俗等态度,语言污秽而残酷,这些无疑是儿童在进入成人世界前的禁忌。但在“文革”这一社会语境中,这样的禁忌被忽视甚至被反向扩大,畸形的媒介使儿童的好奇心被愤世嫉俗或狂妄自大所取代,儿童应有的羞耻心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至于全面崩塌,这严重导致他们价值失范,成年权威意识与童年的好奇心也随之一并消失。
在毕飞宇的“文革”描述中,“文革”不单单是“文革事件”或者“文革记忆”,而多是“文革”影响下的个人。1964年,毕飞宇出生,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966年,中国社会进入动荡的“文革”时期。这段“文革”的慌乱岁月跨越了毕飞宇从2岁到12岁的生命过程。这段岁月在毕飞宇的童年经验中,挥之不去,带有特别的意义,它作为一种题材,进入了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在毕飞宇的创作中,“文革”记忆首先体现着童年阅读启蒙上,以及这种启蒙阅读带来的阵痛。比如,在《白夜》中,李狠、张蛮等“坏孩子”逃课,肆无忌惮地破坏课堂纪律,与身为教师的父亲发生冲撞。又如,在《写字》中,作为长辈和教师的父亲,对“我”玩耍的时间进行规定与限制,父亲要求“我”自觉练习,控制玩心,并告诉“我”识字、写字的重要性和“不会写字”的羞耻。还有,在《地球上的王家庄》以及《平原》中,王家庄孩子上课的片段也都涉及了童年经历中的阅读阵痛。
毕飞宇曾有这样的意义表述:
对“文革”,我们不能拘泥于所谓的“十年”,不能简单地认同一次会议,一个政治人物的宣告,我们要从更为细小的地方认真细致地推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基础心态,我们的文化面貌。[8]
我对我们的基础心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恨大于爱,冷漠大于关注,诅咒大于赞赏。[9]
正如毕飞宇所说,“文革”给予他的是一种“基础心态”,这心态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首先表现为狂妄自大以及对权威的无视。在《平原》中,沈从文就描写了以王学兵为首的一群孩子,对王世国、孔素贞等人的批斗游行。这群孩子在游行口号中获得“雄壮”感,感知着自己的“无所不能”,尽管他们与王世国等素不相识,但与之的仇恨仿佛从天而降,王学兵命令王世国跪下,骑在王世国的脖子上,以王学兵为代表的一代对人格的侮辱与践踏表现出天生的领悟力,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长幼秩序、社会伦理的终极颠覆。在《白夜》中,李狠食言了,他们没有因为“我”射击教室的玻璃而放过“我”的父亲,故事的结尾,父亲回家时镜片被击碎了。这里,毕飞宇书写的父亲只是被孩子们揶揄、捉弄、颠覆的对象,毫无权威性可言。在《写字》中,主人公“我”写下的第一个句子是“我是爸爸”,在这里,“我”最初从读写中得到的喜悦是来自对父亲、对专制、对权威的反抗的,而非来自获得新知的喜悦。“我”用文字记录下的是猪、猪崽、践踏,“我”以文字为武器,向成人世界开火,宣泄“我”的愤怒。
童年经验中的这段阅读启蒙除了表现为无视权威、狂妄自大,还表现为对暴虐和仇恨的习以为常。毕飞宇早期作品《那个男孩是我》是以“文革”为背景展开的叙事。小说中的表姐对白毛女有一股无名的仇恨,她们之间并无过结,也无任何生活的交集,但表姐嫉妒白毛女姣好的体态与容貌,表姐用最恶毒的言语来诅咒白毛女,并为白毛女的不幸欣喜不已。在《白夜》中,有这样的描述:
射出弹弓的刹那,我恐惧至极,然而,快意至极,内中涌上一股破坏的欲望。……我几乎不可阻挡了,不停地对他们说:‘再来!再来!给我子弹!
“我”在破坏的行为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快意满足,这是一种可怕的暴虐倾向。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毕飞宇来说,弹弓是他童年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玩具。弹弓具有警惕与仇恨的意味,带有威胁性,它与“红小兵”这一身份相配。个体心理学认为,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准备”,更是一种社会联系,“它满足并实现儿童的社会感”。弹弓作为具有防备性与侵略性的游戏工具,是那个特定时代紧张氛围的反映。儿童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成长,并接受“文革”阅读启蒙的教育,其个性中必定萌生暴虐因。在《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也有这样的暴虐因素描写,“另一个自己即使和自己再像,只要肯下手,破碎并消失的只能是她,不可能是我”。《唱西皮二黄的一朵》是一个以城市为空间背景、以改革开放初期为时间背景的文本,故事的主人公是19岁的一朵,稍加推算便知她生于20世纪60年代。一朵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仇恨的敏感,这是那个时代人物共同的性格特征,在文本的故事中,仇恨情绪围绕着一朵,她甚至不能接受卖西瓜的大婶长得与自己相似,他们素不相识,但对大婶的仇恨却在一朵心中蔓延。毕飞宇在《男人还剩下什么》有这样一句描述:
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男人还剩下什么》也是以城市为背景叙述的作品,其间明显流露出对于“仇恨”的关注。文本中,妻子与“我”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文革”的童年经验让我们对仇恨都极度敏感,我们相互猜忌、并善于将猜忌夸大成为事实,再加以添油加醋的渲染。这种基础心态也波及我们的下一代,妻子对“我”的仇恨也影响到女儿。女儿就在仇恨气氛渲染中慢慢长大,她的成长伴随着对父亲的猜忌、诽谤与仇恨。毕飞宇认为这才是最令人心痛的,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它所造成的“基础心态”还存在,阴魂不散,它伺机而动,逮着机会便再次袭来。
现象心理学认为,童年经验建构起了个体意向结的最初图式,尽管个体的经历会随着实践和心的丰富而不断充实、发展,但它终究脱离不了由童年经验形成的现在意象结构的影响。个体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德勒认为,“童年经验与往后精神生活的种种现象联结在一个不容置疑、前后关联的模式中。从心理运动的观点看,某种心理象的外在形式及其具体化、符号化的形式可能会变化,但是其最基本的原理、动力以及所有那些引导心理生活通向其最终目标的所有东西,则保持不变。”不可否认,童年经历与记忆,对毕飞宇文学创作有着必然的联系和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了,童年部分经历在文本中的反映或表现,童年经历是不可忽视的研究毕飞宇创作的重要因素。
注释
[1]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4)。
[2]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陈太胜,陈文颖译:《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45~46。
[3]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陈太胜,陈文颖译:《理解人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51。
[4]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花城》,2001(4)。
[5]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6。
[6]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4。
[7]尼尔·波兹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3。
[8]毕飞宇:《沿途的秘密》,昆仑出版社,2002:375。
[9]毕飞宇:《沿途的秘密》,昆仑出版社,2002: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