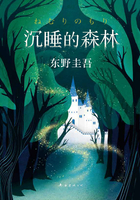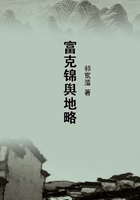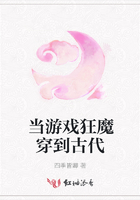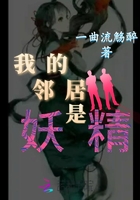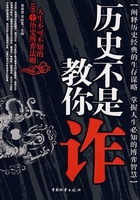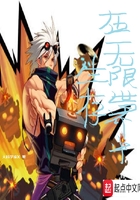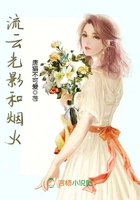1
范志军的线索最终破灭。
聂风好不容易找到了重要证人刘得意,煮熟的鸭子却突然飞了。那个背后的“炸弹客”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肖焱有嫌疑但却找不到他作案的任何证据。警方最后查明,他的“不在场证明”几乎天衣无缝,也查不到他雇凶的任何形迹。
“1·23爆炸案”的三条重要线索,就此都成了“死结”。案情侦破陷入重重迷雾中。
在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无形地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案情扑朔迷离,警官们有点一筹莫展。聂风列席了案情分析会。唐放没有到会,他去南京参加公安部主办的全国爆炸案学术会去了。
殷队检讨说:“我们反省了一下,陶晓玉提供的线索,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胡伟在弥留时确实说了‘这是针对三妹的’,这是胡伟临死前的判断,或者是猜想;第二种可能,胡伟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陶晓玉听错了;最后一个可能,胡伟没有留言就咽气了,陶晓玉故意编造了这句话,她是想引火烧胡丽,以此来发泄对小姑子和胡家全家人的不满。”
李波发言:“如果是第一种可能,说明胡伟临死时确信自己不是这枚炸弹的对象……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胡伟最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一定没有做过会遭到别人怀恨、引来杀身之祸的事情,才会这么说。这就提醒我们:胡伟有可能不是礼品炸弹的目标。”
他的推测很大胆。
“波波这个分析,道理是对的。但陶晓玉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很难说。”殷队表态说。
“我们可以对她进行测谎嘛!”李波说。
“她差一点被炸死,情绪处在极度不稳定中,咋个测谎?!”
“可能连她自己都弄不清这句话是真是假!”有人说了一句。
聂风听着大家的话,不露声色。
殷队:“我认为后面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魏局:“为什么?”
殷队:“范志军说‘那个婆娘没有安好心’时的表情很愤怒,反应很强烈。波波他们都看见的。我觉得陶晓玉编造关于三妹那句话的可能性很大。”
魏局扭头问聂风:“聂记者有什么看法?”
聂风思索了一下,说:“陶晓玉目睹了老公被炸死,自己重伤昏迷,精神上受到巨大刺激,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她完全可能陷入‘灾难臆想症’,产生某种幻觉。所以,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她编造假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赞成聂记者的分析。”殷队点头。
“可是,那几句‘偷水缸’童谣,她记得很清楚哦!”李波质疑道。
“胡伟是在爆炸发生之前念童谣的,这个时候陶晓玉的记忆没有受到强烈刺激。从心理学角度说,她记得胡伟念的童谣并不奇怪。”聂风解释。
“那几句所谓的‘童谣’,对我们破案一点用处都没有。”李波悻悻地说。
一时,大家都缄默了。童谣的谜,的确没有一个人能解。
聂风搔了搔头,继续说:“我在想,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那个礼品炸弹,是指名送给‘胡医生’的。这里面有几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胡医生’是教授楼302室的一个指示词,表明礼品炸弹要送到302室胡医生家;第二种含义,‘胡医生’指的是爆炸的具体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家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胡医生’:父亲胡大渊、老大胡伟、老二胡彬,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可能是爆炸的目标哦?”
他这话有点出其不意,引起众人震惊。
“换句话说,即便胡伟弥留之际说过‘这是针对三妹的’,也不排除爆炸可能是针对胡家父子三个人的。我说完了。”
“殷队,你觉得呢?”魏局问殷队意见。
“这个可能性不大。”
殷队否定了聂风的假设。他解释说:“胡大渊早已退休,德高望重,与世无争,不大可能与人结这么大的仇。胡家老二在珠海市工作,我问过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得罪了谁?’他说:‘我只是给人看病。如果是报复我,应到珠海市找我嘛。’这也合乎情理。”
聂风无语了,但对殷学强的话他心里并不服。
魏局说了一句:“剩下的唯一希望,就看‘唐鼻子’了。”
2
《西部阳光》编辑部。
聂风向吴总编汇报:“‘1·23爆炸案’的三条线索,最后都成了‘死结’。”
“下期的封面文章,只好换一篇了。”吴总编遗憾地说。他打开案头的胡桃木盒盒盖,取出一支深褐色雪茄,点燃抽了一口。
聂风坐在他的对面,表情有点沮丧。
“市民对这个案子迟迟破不了反应很强烈,警方的压力很大。”
“你怎么看的?”老报头问他。
聂风说:“美国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说过,案发的头三天,案件是一宗‘热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阶段;三天后就变为‘温案’;若一个月后仍未能破案,这宗案件就会变成‘冷案’。今天是2月24日,‘1·23爆炸案’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所以说,案子已经成了‘冷案’?”
“可以这么讲。”聂风点头。
3
3月中旬,突然传来肖焱与杜盈盈举行婚礼的消息。
聂风赶去体院打探,得知3月18日傍晚婚宴在“佳韵酒店”举行。
佳韵酒店地处闹市,离体院不远,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婚宴的布置豪华隆重。大厅里立着新郎新娘的大幅喷绘照片,鲜花点缀的签到牌、红地毯,以及餐厅门口的彩色气球拱门,都洋溢着喜庆色彩。
新郎新娘站在门口迎宾。客人络绎不绝,有亲朋好友,也有单位的同事。聂风把自行车停在树荫下,饶有意味地观察着。
新郎一身白西服,神采飞扬。聂风觉得他的模样确实可以用“又黑又瘦”来形容。经过礼仪公司的精心包装,肖焱显得潇洒帅气,但举止之中总掩不住粗野之气,或者说是“江湖气”吧。
新娘身穿粉红色婚纱,非常漂亮,属于那种小鸟依人型的女人。有婚礼公司的摄像师,举着SONY摄像机在一旁跟进。
在案发后不久,警方曾到医院找过杜盈盈了解情况。据说杜竭力回避与胡伟有暧昧关系的事,但她称赞胡伟的医术精湛和有人情味,说单位里的护士都喜欢他。谈话中流露出对死者的惋惜。警方问到肖焱警告胡伟的传闻,杜盈盈承认有过这事,但说那是误会。她相信肖焱不会做出丧失理智的事,而且肖焱也不懂炸药,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器。杜盈盈这话并不能说明什么。肖焱不懂炸药,不等于他不会雇懂炸药的人去干。
聂风发现李波和殷队也出现在现场。两位警官穿着便服,站在彩色气球拱门旁。李波高挑个,殷学强矮胖敦实,活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有点戏剧效果。不过在塞万提斯老儿的笔下,瘦高个堂吉诃德是主人,矮胖的桑丘是跟班。眼下的角色关系却正好相反。
聂风走了过去,和师徒俩打招呼。
“新郎官很帅啊!”他调侃道。
“这个目标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李波悄声地说。“看起来他有三十多岁。”聂风上下打量着肖焱。
“年龄完全相符,肖焱的身份证显示他生于1966年5月,今年正好三十五岁。”李波说。
这个年龄和刘得意提供的情况吻合。
“不过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指证他。”殷队平静地说。
这时,新娘走过来,殷勤地敬烟。虽然殷队和李波脱去了警服,但杜盈盈也认出他俩来。
“两位警官大驾光临啦!欢迎,欢迎!”
在新娘身后,肖焱笑吟吟地迎过来。
“我们是顺道路过这里的,”殷队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向新人表示祝贺!”
“呵呵,谢啦!”肖焱语气夸张,话中带刺地说,“爆炸案还没有破呀?!全市人民都在替你们着急啊!”
殷队被戳到痛处,脸色有点难看,但他忍住了。
李波不服气,回敬了肖焱一句:“我们一定会把凶手捉拿归案的!”
“哦,相信,相信,”肖焱讽刺道,“那个姓胡的流氓医生就死也瞑目啦!哈哈哈……”
聂风明显感觉到,肖焱的笑声中包含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如果他与胡伟的死无关,这笑声意味着泄出了心头之恨。如果他是凶手,那就太嚣张了。
“呵呵,这位是?”肖焱发现睨视着自己的聂风,收敛住笑声。
“你好,我是《西部阳光》的聂风。”聂风大度地伸出右手。
肖焱握住他的手,摇了摇。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聂记者呀!我拜读过你的独家报道,嗬!比英国那个阿加莎老太婆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还精彩哩!”
“你过奖了。”聂风听见恭维,有点喜形于色。
所有的作者都有一种虚荣心,见别人称赞自己的作品,就像母亲听见人夸自己的娃娃乖一样。名记者也不例外。不过他隐隐感觉对方的手劲很大,不愧是武术冠军。
这时,身着礼服的男司仪走过来,叫新郎官上台讲话。
“呵呵,失陪啦。英雄的记者和警官们。”肖焱并起两个指头,在右额上碰了碰,模仿电影里的美式军礼,然后转身消失在花团锦簇的人群中。新娘朝他们嫣然一笑,也转身跟着新郎官走了。
望着他俩的背影,殷队有点哭笑不得。
李波干瞪着大眼。
聂风目睹这个尴尬的场面,咧嘴做了个怪相。
虽然肖焱身上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警方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指证他。现实有时很无奈。
爆炸案疑犯搭乘火三轮的地方,为什么离体育学院这么近?
肖焱同那个“跑江湖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只有找到那个叫刘得意的车夫,才能解开这个谜。他是唯一见过犯罪嫌疑人的人,是最重要的证人。
4
“我总觉得在哪个环节上,我们被误导了……”
唐放坐在工作台前,对聂风说。
他穿着藏青色的警官服,没戴警官帽,圆脸,单眼皮。在他身后的棕色工作台上,摆着一些待鉴证的物品。
“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又说不清楚。”唐放的眼里透着困惑。
聂风之前联系采访唐放,几次被拒绝。包括打电话联系、一大早骑车到城北市刑侦局理化检验室门口拦截,都扑了空。
最后,唐放同意见他,情绪有点无奈。
“唐主任破过好多爆炸案,”聂风讨教说,“你认为这次的失误究竟在哪里呢?”
“破获爆炸案的两个关键——爆炸袭击的目标是谁,爆炸的动机是什么。”唐放回答说,“这次我们一条都没有弄清楚。”
唐放摇摇头,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2月底参加的全国爆炸案学术会上,他通报了“1·23爆炸案”的情况和爆炸残留物的细节,希望作串并案比对。
唐放讲了一个案例。去年川北一个城市发生一起超市爆炸案,迟迟没有破案。不久之后,在该市一个居民楼又发生一起爆炸案,现场勘查确认为不小心引起的。根据现场残留物证比对,唐放主张并案,结果一举侦破,两起爆炸案为同一个人所为。爆炸的居民楼住宅,就是这个作案人的家。
“这说明,偶然之中往往包含着必然。而且对爆炸残留物作串并案比对,对破案非常重要。”唐放作结论说。
“这次‘1·23爆炸案’现场的爆炸残留物,查到什么名堂没有呢?”
“爆炸物来源是查到了,但是和作案人还对不上号。”
唐放告诉聂风,他对残留物作了各种分析检验。从雷管的残骸仔细辨别得出结论,爆炸现场的雷管是四川省绵阳市一家公司生产的8号纸壳瞬发电雷管。起爆电池为××牌9伏方形电池,属于中外合资的××电池厂生产。炸药的成分为硝酸铵和少量TNT……
“炸药、雷管和起爆电池,都是四川省的产品哦。”聂风咕哝了一句。
“这些产品销往全国,产量很大,单凭这一点很难确定东西的具体的来路。”
唐放说完,眯缝着眼,回顾赶到案发现场时的情景,仍觉得历历在目。他总觉得,至今眼前仍弥漫着茫茫的白色迷雾,几乎看不见一点真实的东西。
“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个盲点,不知在哪个方向。”
“盲点?”聂风玩味着他的话。
“还有,我始终搞不懂,那张贺卡究竟有什么含义。”
5
3月下旬的一个中午,一个貌似刘得意的人突然出现。
这段时间,全市的巡警都在寻找刘得意的下落,目标锁定为围着三色编织袋的火三轮。寻找范围以城区和近郊区为主,这些地段是火三轮最活跃的地方。经过一番拉网式的搜寻,一共发现了三辆围编织袋的火三轮。但三个司机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他们自然不知道刘得意是何许人也。
事实上刘得意一直没有离开S市。他是怕警察找他的麻烦,借口回老家,在住处躲了起来。过了一阵,他觉得风声好像过了,又驾着火三轮出来挣钱了。他仍然驾驶那辆围编织袋的火三轮,所以比较容易辨认。不过等客的地点,他换到了城北一带。
这天中午,巡警小黄戴着白头盔,骑着摩托路过五块石车站。小黄是警官学校毕业生,刚上岗不久,是个胖墩儿。他偶然瞥见拐角处的一排火三轮中,好像有一辆围三色编织袋的车停着,挺打眼。
黄巡警停下摩托,上前查询。车里坐着一个穿旧防寒服的中年男人,秃顶、高颧骨、脸颊有些瘦削。这和通报材料上的面貌特征很像。
中年男人看见他走过来,脸色有点变了。
“请你出示一下身份证。”黄巡警说。
“我……我……没带身份证。”车夫吞吞吐吐地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车夫迟疑了一下,说道,“刘二娃。”
黄巡警见他目光闪躲,喝了一声:“刘二娃?你娃子不要打冒诈(说谎)哈!”
“小的不敢。”
“你们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吗?”黄巡警转过脸问旁边的几个车夫。那几个都说他是昨天刚来的,并不认识。
黄巡警盯着“刘二娃”,突然问道:
“你娃子是不是叫刘得意哦?”
对方尴尬地笑了一下,摇头,仍然不承认。
黄巡警举起步话机,拨通W区公安分局值班室,通报了发现的情况。
接到巡警的报告,W区分局全局振奋。
半个小时后,一辆警车把“刘二娃”连人带火三轮请到了W区公安分局里。
聂风接到了殷学强大队长的电话,匆匆赶来W区公安分局。他一进刑警大队办公室,就看见“刘二娃”一脸沮丧地坐在殷学强和李波的对面。
“嘿,刘得意!你终于又露面啦!”
聂风大喜。想不到飞走的鸭子又飞了回来。
“哦,记者同志。”刘得意如同见到救兵,向聂风诉说,“你说过的我不是帮凶哈!”
“当然不算。”聂风安抚他说,“你咋个会是帮凶呢!你是‘1·23爆炸案’的重要证人,如果协助警方破了案,可以立大功啊!”
“警官,他说的是真的?”刘得意向殷队求证。
“当然是真的。”殷队拍拍他的肩头,“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刘得意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
“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殷队和李波对他送礼品袋的经过进行了问询,并作了详细笔录。刘得意提供的信息,和聂风上次获知的完全一致。
然后,进行照片指认。
殷学强从抽屉里取出两张照片,递给刘得意。
“你看仔细了,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那个雇你送礼品炸弹的人?”
刘得意接过照片,低头端详。
殷队师徒和聂风三人不约而同地望着他,目光里透着强烈的期待。
“这一张不像,”刘得意指着肖焱穿橘黄运动衫的照片,说,“叫我送礼品袋的那人有点精瘦,身材没这么结实。”
殷队和聂风交换了一下目光。
“这一张……”刘得意的目光盯着肖焱的肖像照,“脸形很像,有点印象,我们叫四方脸,年龄也差不多。”
“你确认吗?”殷队急切地问。
“说不准……”刘得意犹豫起来。
殷队和李波耳语了几句。李波会意,出去挂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李波进来对殷队说:“体院那边说可以。”
半个小时后,殷队亲自驾上捷达警车,载着李波、刘得意和聂风赶到体院保卫部办公室。保卫部部长姓包,是个矮胖子,很配合。殷队同他商量了一下,胖部长拿起电话,接通肖焱电话,通知他过来一趟。
大约过了十分钟,肖焱急匆匆地走进保卫部办公室。他穿件李宁牌红色绒线运动衫,脸颊上还带着汗渍,像是刚从练功房出来。
办公室里这时只有保卫部部长和刘得意两人。
“包部长,这么急叫我来,有什么指示啊?”肖焱笑眯眯地问。
“你们班不是有人丢了自行车吗?是什么牌子的?”
“哦,是辆高档山地车,捷安特牌。”
肖焱只顾和胖部长说话,坐在一旁的刘得意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刘得意偷偷地瞄了肖焱两眼,表情有点紧张。
“派出所前天说,最近查获了几辆失窃自行车,你叫丢车的同学去认一下。”
“好的,多谢了!”
肖焱告退时,无意间瞥了刘得意一眼。他就像看见一只茶杯或一张空椅子,没有任何反应。
待肖焱走后,殷队、聂风、李波三人像旋风一样从里屋出来。
“是不是他?”殷队急不可待地问。
刘得意摇头。
“你看清楚啦?”
“不是这个人。”刘得意有点沮丧,立功的希望显然成了泡影,“那人还要黑瘦些,嘴唇有点厚,也没有他高。”
殷队他们面面相觑。一股浓重的失望情绪笼罩在众人脸上。最后一条线索中断了。
侦破最后走入死胡同。
“1·23爆炸案”侦破搁浅,就此成了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