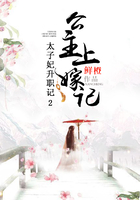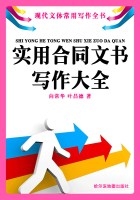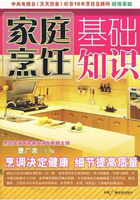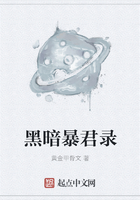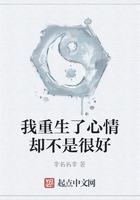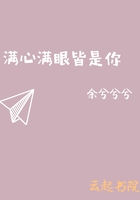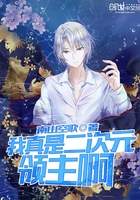阿心
今天我来参加会议,很高兴,很激动。感谢这次文学国际研讨会的组委会老师们,感谢我们匈牙利作协的张执任会长,给了我这个机会。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的文学研讨会和笔会,我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愉悦。凡是喜爱文学的人,大都做过作家梦,我也如此。从小偏爱语文,爱看小说,从初中起我就是图书馆的常客。当知青下乡后,曾悄悄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在文化的荒漠中,获得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工作后的业余时间我尝试着写小说,稿纸几箱子,全是退稿,我依旧锲而不舍,埋头耕耘,也许是精诚所至吧,上帝终于为我打开了发表作品的大门。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花园》杂志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健康带菌者》,更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接着又发表了小小说、散文数篇,并成为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那时候郑州市作协有个文艺沙龙,作家们常在一起畅谈创作体会和经验,气氛十分活跃。作为一个初踏进文学殿堂的人,我总是静静地听着作家们的真知灼见,像海绵一样汲取着文学创作的营养,心里别提多兴奋了!我曾对一位女作家朋友说,我每次参加沙龙活动,感觉像过节一样高兴啊。女友说,你还没参加过笔会呢,参加笔会你就天天过节了。
90年代初,我随丈夫一起来到匈牙利,居住在被称为多瑙河畔璀璨明珠的布达佩斯。二十多年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经历了孤独与失落、困惑与徘徊、拼搏与挣扎,最终走出了心灵的低谷。在年逾花甲之际,能够从容坦然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这种力量不仅来自内心的坚强,更为重要的是,我心灵深处始终怀着美好的梦想——文学梦。是文学,陪伴着我在远离祖国与亲人的地方,度过了无数个孤独寂苦的夜晚。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温良敦厚的匈牙利人接纳包容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给了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们在异国他乡有了自己的家。蓝色的多瑙河是我创作的源泉,美丽的布达佩斯给了我创作的灵感。经商之余,夜深人静时我拿起了笔,抒写着海外华人浓浓的思亲思乡情,记录了旅匈华商历尽艰难奋力拼搏的创业历程,描绘了匈牙利优美的风景名胜,书写了中国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包容与友谊。
众所周知,90年代初,闯欧洲的中国人大都是乘坐国际列车,扛着大包小包来打拼的。当时有人称之为“国际倒爷”,我也忝列其中。国际列车七天七夜的颠簸,初次踏出国门的兴奋与迷惘,还有车上流动百货商店的经历,促使我写下了《再见!国际列车》。海外华人在创业初期过得非常艰难,可以说,每一个出国的同胞都有自己打拼的生动故事,那首《爱拼才会赢》的歌曲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因着生存的压力,许多华商从不知道休息,遇上匈牙利人的节假日,算是被迫放了假,却没有过节的感觉。同胞们见面调侃说,那是人家老外的节日,咱们过什么?好不容易盼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华商们照样练摊开门做生意,并自嘲说,都出国了,还过什么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市场练摊的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她在大年三十中午卖货时给母亲打电话拜年的事,弄不明白时差的老太太,说了句:你们是不是也吃着呢?过年了,多炒几个菜,叫朋友来热闹一下。那位朋友是当笑话讲的,我听后却五味杂陈。于是,有了小小说《越洋电话》,那个叫娟娟的女华商在寒冬顶风冒雪练摊时,不忘给国内亲人拜年的感人场面,是匈牙利华人创业初期艰苦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
小小说《莎莎的生日Party》的创作,是因参加一位亲友给女儿办的生日派对,我发现,宾客中除了我,每年都是新面孔,可谓是铁打的生日Party,流水的客人,她为什么年年岁岁换宾客?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小说中的阿惠,聪慧能干,吃苦耐劳,她像许多在匈华人一样,经历了生意上的三部曲,即零售、批发、发货,一步一个台阶。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后,她的精神层面也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她女儿生日Party的宾客,自然也随之变化。从市场练摊的朋友、匈牙利各阶层的关系户,到供货商,再到她的衣食父母——中外客户群,然后是一些华人社团的人士,如同乡会、妇联会、教会等。换一拨人,不仅是生存需要,更是精神上的需求。她的心灵深处,不仅仅要求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需要精神上的依托。
长期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时刻感受着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与匈牙利人之间的友谊与纠葛,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思维和观念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于是我写了小小说《下次AA》《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散文《租房风波》《泪眼》《耐人寻味的婚姻现象》等。
有人说过,全世界也只有在中欧,老外方给中国人打工。在匈牙利创业的华商,大部分雇用了匈牙利人当员工。根据发生在中国老板与形形色色的老外打工者之间的真实故事,我创作了叙事性散文《黑眼睛蓝眼睛》。在与外国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华商与匈牙利客户之间充满着信任与冲突、感动与无奈,于是便有了叙事性散文《曾经的客户》。
匈牙利优美的名胜以及匈牙利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深深地感染了我,为此我写了《永远的巴拉顿》《会唱歌的湖》《匈牙利人与花》《街头演奏者》《春到多瑙河》《布达佩斯不相信眼泪》《去一趟歌剧院》等几十篇散文。
在此,我要感谢张执任先生,感谢他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上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聊起一些素材,是他鼓励我写成小说,并讲了他的一些巧妙的构思,比如《没有警察》《越洋电话》等。
在匈牙利生活的日子里,也许我不具备经商才能,也许我的经营理念不如一些同胞灵活,但令人欣慰的是,文学创作始终是我的精神家园,多年的异国漂泊生活,我收获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还有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创作是我生活的动力之一,我享受着创作带来的乐趣。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聆听各位老师关于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我将获取更多更新的创作知识,我的眼界会更开阔,我的创作水平也将会因此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谢谢大家!
[2016年7月在世界华文中东欧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八届文心作家(布拉格)笔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