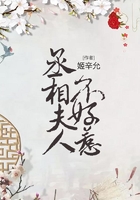行宫之中,夜半有风徂徕,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外,石横刚想阻拦,看见来人后,便放进了屋。
“既然醒了,不如想想是谁要害你吧。”
泽国太子叶檀徐徐睁开眼睛,虽然大病初愈,面色苍白,眼神却如锐利的剑锋。出鞘就要伤人。
他颧高鼻挺,一双邪魅中透着锐意的鹰眼略带疲倦。略微有点暗淡的嘴唇微微上翘。
叶檀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似在嘲讽他又似在自嘲“每次你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今天我都快死了,你却在一旁看戏?你真是没良心的!”
那男子报以微笑走到床前“如果不是你遇刺,快马加鞭往云城而来,照我的安排,你和我应该是今日正午在凤冠山下见面。”
叶檀只得无奈笑笑,“你这老奸巨猾也有失算的时候?要不是你失算,我怎么会命悬一线,那块守城的木头是你的人吧!!死心眼!!!差点害死老子!!”说着伤口因为太激动,扯的疼了,疼的叶檀呲牙咧嘴。
来人摇摇头,“今天这事确实怪我不好了,本想着在凤冠山亲自迎接你进城,不成想有些小事耽搁了……”
“你?!你这个不靠谱的!还要一个弱女子来救我,差点把老子吓死了,还以为真要死在你那守城小将手里了!”叶檀破口大骂,气的直翻白眼。他也是听石横后来说的,不过,如今他不说的过分点,以后怎么跟凤南天谈条件?
因为伤的严重,此时只有眼睛和嘴可以动了,不然他一定下地撕碎了这个不靠谱的黑心鬼!他是为了谁才千里迢迢跑到云城的?没良心!
“想撕碎了我?等你好了再说吧”男人从阴影中走到床前,正是凤南天。只是此时却换了一身黑衣,夜晚灯光忽明忽暗看不清纹饰。
“你怎么穿成这幅鬼样子?又想干什么?不会刺杀我的就是你吧,你穿成这样,你说不是你的人干的!?那我都要考虑考虑!”叶檀没好气的冲着他撒气道。
凤南天摸了摸脸,无奈一笑。
叶檀可没心情笑,居然半路遭了毒手,他泽国的精英暗卫折了大半。他泽国太子还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让他查出是谁的手笔他定要那人血债血偿!
“这女子是谁?多亏了她救我一命,救我时我看了一眼姿色不错,我若不以身相许了她,好像有点对不起她这一番情深意重啊!”叶檀想起朱妍俏丽的容颜,一丝不苟给他处理伤口的样子,眉眼如画,小手给他包扎的时候,摸在胸口上凉凉的,挠的的他一阵心痒痒,于是便半真半假的说道。
“回主子她说她是医圣的徒弟……”石横刚要答话。
“你这种人油泼不进,水滴不进,你居然会喜欢女人!”凤南天嘲讽他道。
“不过,医圣的徒弟,我倒是想亲自会会她,她在哪里?”
“这,都怪臣一时疏忽,竟连恩人何时离去都不知道!”石横一拍大腿,他才想起来朱妍已经不见了。
叶檀捂着伤口,想笑又不敢笑,因为稍有幅度大点的动作,伤口就扯着疼。脸上确实一副开心的神情,她居然跑了!
叶檀赶忙收了话,一脸笑意,一本正经“看来此等艳福,我是消受不起”
“刺杀我的人我也没查出是何人所为,在云国地界,还是你来吧”
凤南天剑眉微蹙“我知道了,你的身体,果真没事了?”
叶檀给了他一个你很烦的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那是一片无穷无尽的花海,开满了各种颜色得鲜花,日光倾泻而下,天地间只有朱妍一个人,她跑啊跑啊,跑累了,躺在花丛里。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还想着这是哪里怎么会如此美丽。
突然,乌云密布,阳光散去,天塌了,地也陷了,黑暗铺天盖地袭来,花海被一寸寸吞噬。朱妍跑啊跑啊,终于跑不动了,跌倒在地,她和那无尽的花海被黑暗吞噬。
朱妍忽的从睡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打湿了中衣,扶额急促得呼吸,朱妍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使劲摇了摇头,也许是一天之中经历了太多,太累了。
她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在深山里的破庙,远离官道想必不会有人来,篝火在噼啪作响,朱妍把白天捡来的柴火又填了一些进去,她没有进城,看着人被浩浩荡荡的云国迎接队伍接走,她毫不犹豫的就转身离开,往城外外走了,这次她可是马不停蹄,一口气走出了七十里,已经到了文山驿了。
肚子饿了就在庙里充饥,好在太平盛世贡品还是有的。只是是在走不动了才找到这间破庙落脚。
每到一处城镇她就去活人属过夜,因为她从母亲去世以后就是在活人属长大的,虽然活人属是官府建立的给流民孤儿的机构。
可是任谁管理活人属都很难,活人属里的人,如同三月的风,今天吹到这里明天指不定吹到哪里了,都是流离失所的人,更多的是孤儿。
当年她母亲还在的时候,还会给书院做些粗实活计,养活她们娘俩,顺便让朱妍可以在一旁跟着读书识字。
直到她九岁那年,一场洪水,冲破了一切。
灾民流离失所,她和娘也不例外,随后而来的就是瘟疫,人间就仿佛人间炼狱,整户整户的染病,一个镇子一个镇子的死人,十去其七,家家有丧事,户户烧纸钱。
娘就是在那场瘟疫里一病不起,那时候的活人属里已经没有多少能动的人了,娘再也抬不起头喝水了,只留下一句“妍儿,活下去,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便一口气出来,撒手人寰了。
那时她不懂也不想懂,她趴在娘的身上哭,可娘再也没有醒过来。
她连埋了娘都做不到,她抱着娘的身体在活人属的院子里,四周都是病入膏肓的人,有老有少,她只知道,她哭,娘不应了。
后来她这开始像娘一样发热,她知道她要去见娘了。昏昏沉沉中她躺在娘的怀里睡着了,梦里娘抱着她,她开心极了。
醒来后,已经是三天后了,她依旧在活人属里,只是娘不见了。
她面前是一个蒙着面的白衣人,他对小小的她说“你活下来了,你娘我们已经安葬了。”
“我不要,我要和我娘在一起,我娘在哪里?”
男人眉头紧锁“你娘……永远和你分开了,但是她让你活了下来。”
朱妍只记得她哭,她闹,她找她娘,男人跟在身后,什么也不说,她小小的身躯跑遍全城,终于她跑累了,白衣人把她带到城外乱葬岗,在一堆新起的小土丘中,给她指了一个小小的土丘,说娘就在那里,她才抱着土丘睡着了。
从那以后她天天在活人属和乱葬岗之间往返,白天去活人属要饭,晚上去乱葬岗陪娘睡觉。
后来她发现白衣人每天都在活人属忙着什么,他用草根和树叶给那些病人吃,再后来她发现,有很多人活了,虽然也有人死,但是更多的人活了过来,像她一样。
她哭着去求白衣人救救她娘,白衣人没有回应。
良久他终于开口“你可要学这救人的本领?有朝一日你也可以救你想救的人?”
朱妍点头如捣蒜,她那时想的居然是救活娘。
再后来她被白衣人带到了医宗,见到了师父,师父见她孤苦无依,直接收她做弟子,朱妍也是后来才知道,医宗弟子,分量是多么的重。
眼前的活人属和十年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了,虽然也有乞丐,也有人生病,却生机勃勃了。
朱妍习惯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去活人属看一看,找一找有没有需要看病的病人,好在太平盛世,活人属一些草根树皮不怎么名贵却也能治病的药材还是有的。
这里有乞丐,有无家可归的穷人,有被人遗弃的老人,有病入膏肓被家人放弃的病人,也有……朱妍一眼就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
她直奔角落,只见脏兮兮的地上连一点干草都没有,十月已经开始变凉了,一个小小的身躯就蜷缩在角落里,连一片完整的衣服都没有,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儿。
朱妍大声喊着“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个男孩,已经晕过去了。
“姑娘,这孩子的娘前两天病死了,已经被活人属的人抬出去了。”
“那这孩子怎么没人管呢?他连衣服都没穿”
“姑娘,这活人属你还真以为是菩萨庙啊!一天有一次舍粥就不错了,哪来的衣服。”
“那你们怎么没人给她喂些饭?”
“我们自己都吃不饱,哪有饭来给他吃!”
活人属的情况她是清楚的,可她还是想问,她想问问为什么。
不然她也不会每次都到活人属来。
她四下环顾,整个活人属就只有门帘有一块布,那是用来挡住活人属里不堪入目的景象的遮羞布。
朱妍抱着孩子一把扯下门帘,给孩子裹上,再摸他的脉门,只是太饿了。
她如今虽然身无分文,但是多亏师父高瞻远瞩,每个城都有她医宗的分号,她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文山城的朱雀大街,医宗全天下分号的情况她都清楚,因为这些分号都是她帮着师父建立,打理起来的。
甚至哪个师兄弟分派到哪个分号,也是师父让她去安排的。
文山城的分号,是她的师弟单平。朱雀大街上门外人最多的就是医善堂,朱妍直接抱着孩子冲了进去。
“这位……”朱妍此时还是一身乞丐装扮,她看了看自己,再看看拦住她的小药童。
朱妍不好意思的停住了,这身装扮确实有碍观瞻,门外排队的病人们也急了。
“你个要饭的看还看病!就是看病也得排队啊!”
“是啊连点规矩都不懂,排队都不知道,我看你也就只配要饭吃!”
“算了算了怎么还和叫花子计较!”
朱妍此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这孩子快不行了,对不住各位了!”
说罢继续往里走。药童一个没拦住朱妍已经到了后院了。
“你不要乱跑,这可是医宗的医馆,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快来人呐!”药童开始大呼小叫的叫人。
朱妍根本不管他,直接冲到厨房。
“诶你这个叫花子你是饿疯了吗?来这里抢饭吃你给我住手。”
朱妍实在是无暇理他,两个手指在他关门上一点,他顿时呼吸困难蹲在一边喘气都来不及更别说给她捣乱了。
朱妍在厨房里找到了些粥,在锅里还是温的,赶紧给小婴儿喂下,想来这孩子是饿的哭都哭不动了,只几口粥米汤,孩子的嘴就会动了,朱妍又给他喂了些水。
这些事她做起来驾轻就熟,因为从六年前开始她和师父四处建立医宗时她就四处收养弃婴和孤儿上医宗了,好在医宗财大气粗,师父索性不差她这几口人的口粮,默许了。
既然如此她便见人就收了,只要是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孤儿,她都喂饱了换好衣服带回医宗,医宗她那个院子已经成了孩子窟了,带孩子比当娘的还熟练。
又喝了些温水,孩子脉象平稳了。小小的脸上神色安稳多了,沉沉的睡去了。
“我当是谁,原来是‘医宗之娘’啊!见怪不怪了!”一个清朗的男声从背后传来。
单平也是她捡的,不过是她捡的最大的,和她同岁,是她要饭时的伙伴,后来再次在活人属遇到,就求师父带回了医宗。
“我看看单平平,哦如今已经亭亭玉立了呢”朱妍和他自小便是玩伴,再熟悉不过。
回首,果然是单平,他和医宗的人一样平时一身白色的粗布麻衣,朱妍上前就照着脸上捏了一把。
看的一旁的药童目瞪口呆,更加喘不上气来了。
朱妍顺手解了药童的穴位,吓得他急忙跑了。
单平揉着脸凑过来看怀里的孩子。
“又捡了一个?不会是你在外面偷偷跟别人生的吧!”
不一会,单平捂着脸回到前堂。
“呀!大夫您这脸怎么肿了?”
“啊,嘴不严,漏风,就肿了!”一边捂着脸一边若无其事般继续把脉看病。
不过,单平说对了一半,这孩子是她捡的,可她也确实要在外面怀了别人的孩子。
“唉!”朱妍长叹一口气,药童给她找了间客房准备饭去了,她去柜上赊了些钱去街上买了些布,又找有母羊的人家买了一罐子羊奶,喂饱了孩子,坐在客房里开始给孩子缝衣服。
养的孩子多了,衣服就得动手缝,虽然她一个人是缝不过来的,总是拉着医宗的师兄弟姐妹一起缝,可她还是缝的最多。
时间久了,调皮如单平这样的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医宗之娘,照顾师兄弟姐妹的饮食起居,给师父打理医宗大小事务,她可不就是医宗里的使唤婆子吗?
“大娘,又在做衣服?!这孩子又是活人属捡的吧!”单平终于看完了一天的诊,天热已经暗了下来。
“怎么?你还是我捡的呢!”
“行!得得得!你爱捡就捡吧!人家都喜欢捡点金银财宝,最不济捡破烂,你呢,爱好捡孩子!你说那天下没人要的孩子那么多,你捡的起吗?你捡的起,你养得起吗?”
朱妍认真的抬了抬头,“你说得对!”
所以,“你们的得加油赚钱了啊!”
“对了这月诊金赚了多少了?”朱妍低头继续缝衣服。
单平认真的看着她“五两银子,还被你赊出去一两买布和羊奶”
“有点少啊,要加油了!”朱妍低头不语。
她怎么会不懂,医者仁心是患者送的牌匾,可既然悬壶济世了就没抱着赚钱的心思。可她们也是人也要衣食住行。
所以她只能另寻出路。确实多个人就多张嘴吃饭,像单平这样出师的,还能自己养活自己,那些小的全靠师父在养。
前世她一朝麻雀变凤凰后,她的嫁妆,月钱全都给医宗她养的那群孩子了,凤凰毕竟是凤凰,最起码钱是源源不断从来不愁的。
第二天朱妍又去了活人属,把有病需要治疗的开了方子,活人属有药的就直接抓来教他们自己用活人属的罐子煮了吃,活人属没有的药她就去医善堂拿。
单平也拿她没有办法。
第三天她要启程回医宗了,想来想去还是要回去,如果她那个“夫君”侥幸不死,也许会参加一个月后的医宗大比也说不定,天下之大找他如大海捞针,况且,医宗大比各路豪杰云集,总会找到一些线索的。
文山城距离医宗只有一天的路程了,朱妍给那孩子起名粥粥,她实在是起名字起的快废了,后来干脆遇见时看他身边有什么就叫什么吧。
她背着粥粥和他的新衣服走了一天终于在黄昏到达了医宗脚下的镇上。她决定马不停蹄的上山。
给粥粥喂了些从路过村庄买来的羊奶,就背着夕阳了内景山了。一路风光无限,却又那么熟悉,三年了,恍如隔世。
医宗叫是叫医宗,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宗门,名叫内景宗,有总宗主的,只不过她从没见过总宗主老人家,据说宗主活了二百多岁,长年闭关。
除了医宗还有道宗,药宗,奇门宗,而其他几个宗门也不是没有发展壮大。只是因为近几年医宗被师父普渡壮大到爆发一般发展'显得其他几宗越发没有地位。
四宗各有宗主,各自为政。但医宗求医求学者最多,广为传颂。
因此,此地也被广泛传播误导称为医宗了,其实这里是内景山,山上四峰分位四宗,医宗只不过在主峰而已。
而且,医宗的弟子很少和其他几宗往来。朱妍对其他几宗几乎不怎么了解。
除了,道宗那位,他是道宗掌门,她刚上山那段日子,是她这辈子最难过的日子,那时她十岁,乞丐出身,无依无靠,她知道师父是可怜她才把她带上山的。
可是要知道,她没有考过试,更没参加过医宗大比居然有机会拜在医圣门下,而那些想拜师拜不成,拜成了却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到的艰辛的人几乎无法容忍她的存在。
她像个丧家犬一样被呼来喝去,朱妍!去捣药!朱妍!去倒药渣!朱妍!过来给师兄按按脚!“师兄一天的活太多,累都累死了!”
朱妍才十岁,而且无家可归,能在山上学医她已经感激涕零了,她也和师父说过给她换个普通点的师父吧,她撒自己什么都不懂,跟着师父浪费了。
可师父就是不肯,还给她留了更多的课业。
她每天只能睡两个时辰,五更便起,给师兄师姐们烧水砍柴,还要一边背完师父留下的课业,三更才睡,她采药,晒药,炒药,做灸,煮针……样样都要她做。忙完了还要给师兄弟们都端上洗脚水。
稍有不慎便会被师兄弟们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甚至责罚她不许吃饭。
终于有一次她实在是累的端不动了,一盆上好的金汁被她端洒了,刚好洒了大师兄一身。
整整一天都没有给她吃饭,而且也不许她洗掉身上金汁的味道,让她跪在院子里,所有师兄弟姐妹面前,她终于体力不支昏倒在地。
他们恨她,尤其单颜,他是大师兄,是所有人中最努力的一个,为了拜师他付出了整整三十几年的青春,抛妻弃子,来到医宗,怎么肯承认她这个叫花子。
于是她就成了大师兄“重点照顾”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