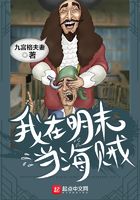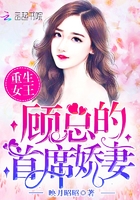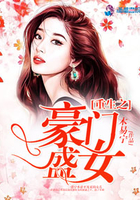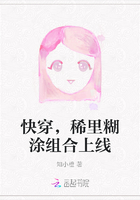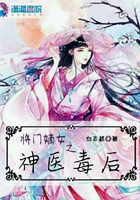第二日,皇帝直睡到日晒三竿方才醒过来。袁宝传皇帝口谕,让各位宗室子弟,文臣武将自行狩猎,皇帝身子不适,休息一日。众人皆知皇帝不胜酒力,自然是酒后不适了。
吐过两轮之后,皇帝才觉得脑袋轻缓了许多。吴淑妃和袁宝忙了半天才将皇帝安置好。用过午膳,淑妃却说要带十二皇子回宫。
“这是怎么了?”皇帝问,“朕已经着人盯着发羌那二人了,爱妃还担心什么?”
吴淑妃作忧心状,道:“陛下不知,臣妾昨晚去子枢帐中,才知那孩子这次吓得不轻。只是碍于皇家颜面,才苦苦撑着,陛下是知道的,子枢这孩子比谁都要强。”
“遭了这种事,任谁都会受惊。”皇帝点点头,道:“既如此,朕便派人护送你回宫吧!”
淑妃出了皇帝行宫后,皇帝盯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不见。才问袁宝:“昨日朕醉酒,可曾说过什么不该说的?”
袁宝答道:“奴婢不知,昨日陛下急着与淑妃娘娘安歇,奴婢不敢久留,实不知陛下有说过什么。”
皇帝怒声道:“今后朕若再有酗酒,须得你亲自照料,任何人不得插手。明白吗?”
袁定吓得跪下,连声道:“奴婢知道了!”
吴淑妃回宫时,太后正在永康宫正殿上。殿阶之下跪着一个内监,从他紫色的服制上看来,品级不低。
“你说说,哀家要你何用?你呆在皇帝身边这些年,替哀家做过什么?”太后怒问道。
“太后息怒!”那人低着头战战兢兢道,竟是皇帝身边的林永。
“别的什么事也就罢了。当年皇帝派陇西的兵马南征鹤拓,这惊天动地的事,你贴身伺候皇帝,竟半分都不知情。简直无能至极!”
“太后息怒,并非奴婢无能。只是陛下像是防着奴婢一样,奴婢虽是陛下身边的首领太监,也只是虚有其名。陛下多疑,重要机密之事绝不让宫中的内监插手。再轻缓些的事,陛下也是交给袁宝处理。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啊!”林永道。
“哦?皇帝竟防得这般紧吗?”太后疑惑道,“你伺候皇帝该有十五年了吧!”
“回太后,就快十六年了。”林永答道,“或许正是因为奴婢是太后赐给陛下的……”
他说了一半便不再继续说下去,太后自然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只是惊讶皇帝防了林永十五年,却并未打发他。这毅力着实不容小觑。
“罢了!”太后叹了一口气,道,“哀家也不指望你什么了,你若能为哀家探点消息自然最好,若是不能,就好好当你的差吧!你自己也要当心,皇帝疑心归疑心,若是你留下什么把柄,哀家也救不了你。”
林永如获大赦,谢过太后又重重地嗑了几个响头,方才离去。
“看来陛下一直是防着林公公的。”身侧的张正道。
“当年哀家选他当贴身伺候皇帝,也不过是看他底细干净。”太后道,“哪知皇帝竟多疑到如此地步,也不管他多干净的底细,只因是哀家给他的人,便弃之不用。明面上却还给了首领太监的虚衔。”
张正见太后有怒,便转了话锋笑道:“不过话说回来,这林公公也并非一事无成。前几日若不是他在陛下的紫砂壶上做了手脚,七皇子哪能伪装成阿晏前往秋猎呢?”
“是了!这么些年,也就这事办得让哀家满意了。”太后道,“这人怕是也没什么其它用处了,由着他去吧!”
太后刚说完,一小太监上前报道:“启禀太后,吴淑妃娘娘求见!”
太后看了一眼殿外的天色,已是日薄西山。
“此次秋猎,吴淑妃不是随行的吗?怎么这个时候回宫了,还要见哀家?”太后自问道。
“淑妃此时前来,怕是有事。”张正道。
太后像是想起什么,道:“文箐今日寄来的信上不是说过了吗?子枢既然识破了子焕,他母妃前来,只怕是与子焕有关。”
言罢,便召吴淑妃进殿。
吴淑妃身着一件暗红色的便服,衣角尚有尘垢。可见她一回宫中,尚未更衣便来求见太后了。
行过大礼后,淑妃并不急着起身,道:“臣妾急着面见太后,未来得及沐浴更衣,失仪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吴淑妃得皇帝盛宠,却也知道孝顺太后。众多妃嫔中,也只有吴淑妃能讨得几分太后的欢心。
“无妨!”太后赐座后,让张正上了茶,接着道,“你且说来,有何急事?”
“并非急事,实为要事。只因事关重大,臣妾不敢怠慢,唯恐迟则生变。”淑妃说完,瞅了张正一眼。
张正知道淑妃此举是在告诉太后此事重大,只能说与太后听。他一向贴身保护太后,太后也信任他,因此这种场合他向来也不回避。不过当他像是征求意见一样看向太后时,太后冲着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退下。张正便依太后之意退下。
“吴淑妃此次急着回宫,是为了七皇子之事?”太后试探道。
吴淑妃惊道:“太后神算啊!”
“好了!你别奉承哀家了。”太后道,“哀家可算不到你是为了七皇子的何事。总不会是为了拿此事威胁哀家吧!”
吴淑妃呷了一口茶。听到太后此话,险些喷了出来,连称不敢。
她说道:“只因子枢这孩子侥幸识破了七皇子的身份,臣妾才知道七皇子的本事。太后可知,七皇子在狩猎时救了子枢一命?”
“竟有此事?”太后吃惊道。
原来赵王寄来的信中只说了十二皇子认出子焕之事,其余诸事却并未提起。吴淑妃便将十二皇子遇刺的始末粗略讲了一遍。
太后听完拍案而起,怒道:“好个发羌竖子,以为秦王殿下在他发羌,便能有恃无恐了吗?”
“太后息怒,所幸皇子们都相安无事。陛下已经派侍卫盯着他们了,想必不会再有此事发生。”吴淑妃道。
“此事绝不能就此放过,哀家要让他们知道我大靖皇子不好欺负。”太后狠狠道。
“臣妾先行谢过太后了!”吴淑妃顿了一会,接着说道,“也正是因为此事,臣妾才多关注了这个假阿晏。说来,臣妾还要恭喜太后,您老人家真是教出了个好孙子。不仅能文能武,还聪慧过人。”
太后明知她说的是奉承话,听起来却还是格外高兴,更何况她所言不假。
“淑妃这么急着面见哀家,难不成是来哄哀家开心的?”太后笑道。
“太后说笑了,臣妾说的是事实。”吴淑妃正色道,“臣妾急着见太后,是为了与太后商讨一事。”
“何事?”
淑妃再次跪地说道:“臣妾想抚养七皇子。”言语中,尽显恳求之意。
“哦!”太后举杯的手悬在空中,然后慢慢放下,说道,“你这意思是要与哀家合力,救七皇子出城了?”
“正是!”
太后毫不犹豫道:“好!只要能将子焕救出城,哀家答应将他交给你抚养。却不知你有何计谋?”
“臣妾就只能吹吹枕边风了,倒是关键一招,还得太后出手。”
“如何出手?”
淑妃嘴角一扬,道:“陛下因星象之说,迁怒于七皇子。可这星象如何又有谁知道真假呢?”
“此事哀家当年便查过,太史令赵天知是个耿直之人,也未曾与人勾结。星象之说不像有假。”
“或许吧!可若太史令大人说这星象是假的又有谁能质疑呢?这星象可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若是太史院有人为太后说话,那这星象如何,还不是看太后的意思了。”吴淑妃道,“况且赵大人年岁已高,是该换人了。”
“哀家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可歪曲天意是会遭天谴的。”太后眉头紧锁,似乎很为难。
“太后竟也相信天意吗?方才太后也说了,赵大人耿直。若真信天意,那太后是否也信了那星象之说,信了七皇子身负轼君轼父之命?”
“哀家固然不信。”太后迟疑道,“不过这些年来,哀家越来越觉得皇帝囚禁子焕并非仅因为星象之说。”
“太后就不必忧虑这些了,太后只需处理好太史院的事,其余诸事,臣妾自当办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