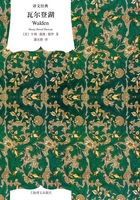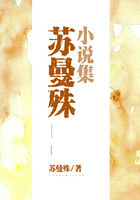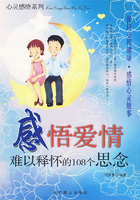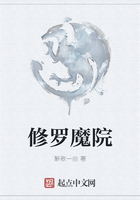番薯
无论它有多少个名字,我永远把它叫作番薯。这个习惯来源于我操习多年的母语词汇,就像番薯对泥土的坚守,早已根深蒂固。
起初我以为这名字土得掉渣,后来略长见识,方知“番”其实是和洋气沾着关系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甘薯疏》有云:“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此中所提番薯便是了。相传此物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传入菲律宾,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处以死刑。明朝万历年间,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冒死将番薯藤运回中国,从此广泛种植,最后遍及中华大地。
原来,它是正儿八经的“舶来品”。在我的故乡麦菜岭,一切和远方有关联的作物都被冠上了“番”字,譬如番芋、番豆、番茄……就连外地娶来的媳妇,一辈子不能融入当地方言的,背地里也被人呼做“番声婆”“番背人”。
无论如何,番薯在中国大地上活了,而且活得很滥贱,不管红土黄土黑土,它只顾遍地生根,根茎横贯东西南北,没有一丁点娇贵和水土不服的意思。以至于许多人都对它的存在感觉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根本想不起来它曾怎样漂洋过海,历经千难万险,才落入我等口腹。也不知那两个不怕死的先祖,在泉下是否心有腹诽。
番薯的好种易活,在为它赢得广泛喜爱的同时,也被人为地附着上了诸多的轻视和贬义。你想,随便扔一根番薯藤在泥面上,高山也好,坡地也行,河沟也罢,它都要落地生根,竭尽全力地铺展开枝叶,还没心没肺地开花结果。不挑土质,不挑肥料,不挑水分,就这么恬不知耻、愣头愣脑地长,谁会小心翼翼地把你捧在掌心,像大熊猫那样金贵地呵护着呢?
因此,家乡人普遍爱用“番薯”来骂人,“死番薯”“番薯婆”“番薯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专指那些痴愣愚钝、脑子不会转窍、想问题不懂换个角度的人。说白了,就是一个“蠢”字。我依然记得儿时,混在祖祠的人堆里看热闹,望见一个前来提亲的后生坐在一边,垂头丧气,默默地领受着他的长辈不迭声地责备:“我家这个死番薯啊,就是不懂事……”他长得很帅,还会做爆竹,经常来我们村找未出阁的莲娇。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知何故竟冲口而出:“莲娇,我是不爱你了哟。”一门即将到手的亲事就这么黄了,长辈们“死番薯长死番薯短”的替他道了无数个歉也无济于事了。那后生此后再没来过,但终究成了全村人恒久的笑柄。他叫什么名字已无人记得,提起那桩事,人们只是会意地一笑:“哦,那个死番薯啊。”
番薯似乎浑然不觉委屈,它匍匐在大地上,沉默、隐忍。它对抗着一切旱涝,连虫子都不惧,不需要给它特地施肥,也不需要替它喷洒农药。假以时日,便慷慨地捧出它的叶,捧出它的茎,捧出它的根,尽着人类与牲畜大口朵颐。它难登大雅之堂,却往往成为很多人舌尖上终身惦记的美味。
我们家乡盛行着一种小吃,叫番薯叶米果。小时候,因为种番薯,我挖地、开沟、担水,把一切劳作之苦都尝了个遍。但摘番薯叶却是件极愉悦的事。一走进番薯地里,到处铺开着水灵灵打着露珠儿的叶子,看着便满心的欢喜。在每条茎上取顶部最嫩的几片摘下来,不消多久,菜篮就沉实了。洗净拌上米浆,上锅蒸熟,绿莹莹地端出来,切块蘸上佐料吃,那种滋味简直妙不可言。此后,我的家乡人走到哪里,便将这味小吃带到哪里。先是大范围地占领了本市的早点市场,后来,他们又在打工者密集的地方,一家一家地开出店来。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只要有九堡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这味九堡特色小吃。甚至连外地人也寻上门来,大声称赞:“真好,的确是绿色食品啊!”
在饥荒年代,番薯充饥果腹的作用功不可没,曾经成为众多乡野农民的救命食粮。时间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末,谁也没想到我的堂哥春林还会在番薯的救命史中添上一笔。那一年他第一次出远门,随乡人去武汉打工,不多日突遭变故,乡人各散西东。而他被包工头抛弃,身无分文,只得徒步回家。他日夜兼程,整整走了26天,方才一屁股跌坐在了我家的椅子上。奶奶抚摸着他瘦削的脸,老泪纵横:“孩子,这么多天,你是吃什么过来的?”堂哥说:“只有番薯,饿了就趁没人时在路边掘几个吃。”幸而有番薯,幸而只要有泥土的地方便有番薯的身影。
番薯的好,乾隆皇帝也知道。他在晚年时曾患“老年性便秘”,太医们千方百计给他治疗,但总是不见效。一天,他散步来到御膳房,闻到一股焦香气味,十分诱人。乾隆问道:“什么东西如此之香?”正在吃烤红薯的一个小太监见是皇上,忙跪倒磕头道:“启禀万岁,这是红薯。”乾隆从太监手里接过一块烤红薯,吃后连声道“好吃,好吃”!从此,乾隆经常吃烤红薯,不久,他久治不愈的便秘竟不药而愈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领着孩子在野外烤番薯。一群大人聊着番薯的N种吃法,N种功效,聊得口沫生津,直到香味在整个田野飘散开来。恍惚间我又看见了烈日下挥锄种番薯的那个少女,金黄的老茧握在手心里,多年来仍未消散。像眼前的番薯,无论被人们端上多大的台面,开发出多少的功用,它还是它,不邀宠,不谄媚,不忘初心,安静地活着。
芋头
这个时候,乡间沃野上的芋头应该已经长得亭亭如盖了。
比之番薯,芋头显然有着更值得倚老卖老的资本。早在《诗经》的《小雅·斯干》中便出现了“君子攸芋”这样的句子,据说这里的“芋”便是指的芋头。不管这说法靠不靠谱,至少《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一曰蹲鸱,一曰芋魁,和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诸种叫法,盖因芋的个头之大也。
幼时在麦菜岭,有个小伙伴就叫“毛芋头”,因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头发则又黄又短,根根往外倒竖着,活像个大芋头。也不知是谁最先叫起,得到全村人一致拥护,越叫越响,以至于他的大名早被人们忘记。直到今天,连他的媳妇也一张嘴就是:“毛芋头——”农村人取外号之形象生动,信手拈来,由此更见一斑。
初春时节,便要开始种植芋头。将床底下藏了一冬的芋子取出来,选那些出了芽的,一个一个小心地平切了底部,切面还得醮上草灰。田里早已做好了芋沟,把这些带芽的芋子埋进土里,撒上稀松的粪肥,再盖上一层干稻草,淋点水,便告功成,只等着小伞盖一样的嫩叶破土而出了。那时候,我常常是撒粪肥的那一个,提着畚箕,将和着草灰的猪屎捏得细碎,再均匀地撒在土里。春光明净,鸟唱虫鸣,田野里到处膨胀着生长的气息。我欣欣然被大美的万物陶醉,早忘了手里握着的东西里夹带了脏和臭。
其实芋头只是埋在土里的那一部分,长在地表上的茎和叶,被我们称作芋荷。我估摸这个名称的来由,是因它那撑开在地面上的椭圆形叶子,像极了荷叶吧。一样的翠色,一样的光滑,就连叶面上驻留的雨水或露珠,也一样的晶莹剔透。但是你千万别被它那完美的表象给迷住,以为可以亵玩。若是把叶子弄破,汁液不小心沾到衣服上,那好了,不论是什么颜色的布料,一律印上了难看的褐色花斑。
田间劳作的人们,渴了就去找一眼泉喝水,旁边不忍心扔下锄头的人会说:“给我带点水回来啊。”用什么带呢?随手摘下一片芋荷叶,盛了水,团成一团便是一个水瓢。逢上下雨,来不及跑,摘片最大的芋荷叶,顶在头上,便成了最简陋的雨具。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发明,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芋荷是我们家乡特有的一道美味小菜。取粗大的茎,撕了表皮,晒干,切碎,放进瓦缸里腌成酸菜,炒着吃,极其开胃。但撕芋荷却是一件苦差事,被沾上芋荷汁的皮肤,无一例外地红肿奇痒,几天难以消散。偏偏这事又一般是细皮嫩肉的女人做,男人是不屑于动手的。可是年复一年,女人们从没停止过制作芋荷,可想而知这道美食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如果把芋头分得细一点,有母芋和子芋之分,甚至还有孙芋。那种圆溜溜的,附着在子芋旁边个头最小的便是孙芋了。而口感最好,最面最烂的也是孙芋。这种小芋子刮了毛后不用切,圆溜溜的,直接入锅煮着吃。小时候不懂,只把它叫作圆芋子。我们家常煮芋子粥。芋子加米煮烂,将熟之际再撒上绿油油的青菜,淋点辣椒盐,堪称世间美味。像我这样饭量极小的,也能撑上三大碗。当然,其中最美的事,还要数舀到了圆芋子。在一锅煮得黏稠的粥里,捞着几个圆芋子,感觉便像如今的中彩。需得意地高声宣布:“啊,圆芋子!”长辈们对我慈爱,如果碰巧舀上,定要体贴地搛进我的碗里。似乎听我兴奋地高呼一声,比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芋子的吃法可谓多矣。最简单省事的,便是煮毛芋子。洗净了,连皮也不去,放进大铁锅里,烧旺了火呼呼地蒸。蒸熟后剥了皮直接吃,绵软流香。农村人,芋皮连毛也不会浪费,可以喂猪。但在父亲的口中,剥下的芋皮还有用处:“就这样,把光滑的一面翻出来,有毛的那面卷进里面,放进嘴里,‘咕’地吞下肚去。”他认真地示范给我们看,却并不吞下。然后是更长久的说教:“我们小时候没得吃,只能把芋毛吞下去充饥。一粒粮食一粒汗呀,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儿时的我和哥哥如鸡啄米般地点头相信,并身体力行地执着于勤俭节约。上初中以后,哥哥对这种反复的说教有了质疑和反感,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经常说他小时候吃芋毛,但从来没见他吃过。即使吃过,现在时代也已经不同了。如果照他的逻辑,他应该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才对……”多少年过去,吃芋毛的故事仍然成为我们家的餐桌佐料。我每次提起,父亲只羞赧地笑,并不承认真的吃过。但他说,困难时期的确有人吃过的。在特殊年代,芋毛可充饥保命,这,我必须要信。
尽管对我们兄妹从小施以节俭教育,父亲的慷慨大方却是连乞丐都知道的。彼时乡里有个叫“包子嘴”的乞丐,颇有些年岁了,没有亲人,也从不说话,长年住在一个破砖窑里,靠乞讨活命。此人只要来到我家,父亲总要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桌上有的菜,一样不少地给他添上。合上煮了毛芋子,还要取几个放在他的布袋子里。“包子嘴”也聪明,平时在外面能讨到,决不到我家来,有点感恩的意思。但实在讨不到了,他来,就一定有他吃的。
说起来,芋头还助林则徐报了一“仇”呢。广州的英美俄德等国领使,用冰淇淋来招待林则徐,林则徐看到有气冒出,以为是热的,便用嘴吹之,好凉了再食,惹得领使们大笑。后来,林则徐宴请那些领使们吃饭,上了一道芋泥,颜色灰白,表面闪着油光,看上去没有一丝热气。领使以为是一道凉菜,用汤匙舀了就往嘴巴里送,被烫得哇哇乱叫。林则徐嘴里抱歉,说没想到他们原来不知道这“芋泥”外冷里烫,其实心里想必是偷偷暗笑罢。
而我喜欢煨芋子。打小无人教授,却每于烧火时,懂得取了芋子在灶膛里煨,火烧完了,芋子也熟了,兀自吃个满脸乌黑满嘴香。陆游有诗云:“地炉枯叶夜煨芋,竹笕寒泉晨灌蔬。”“烹栗煨芋魁,味美敌熊蹯。”看来煨芋远非我的独门馋功也。
我在石城县一所小学实习时,曾吃过一顿最回味悠长的芋饺。彼时我住校,周末,一群女学生携了芋子等食材来到学校。十一二岁,她们已谙熟了做芋饺所有的复杂程序。没有人提出过要求,孩子们只是要做,做给认为重要的人吃。后来我想,她们多么像田里的芋,毫不起眼地生长于沃野,可是只要你一想起来,便觉得唇齿生香。
花生
离开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后,每年春天,我开始怀念一片黄色的小花朵。那时候,它们在我的词典里叫作番豆花。少有人注意到那些花儿,它们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只安静地贴着泥土开放,还被一丛丛茂密的绿叶遮掩着,像一粒粒生怕被人发掘了的金子。花落之后,花茎伸进泥土,不声不响地便将果实给结了。
据名猜想,番豆应该是有着洋出身的。其实关于花生在中国的起源,一直以来被世人争论不休,主流说法是明朝时期经南美洲引种而来。后来一次次的研究证明这一说法从时间推论上站不住脚,一来在江西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炭化花生种子,二来元朝贾铭的《饮食须知》中已经提及了花生。不管怎样,它是来自海外无疑,算坐实了番豆这个别名。
当然花生根本不需要理会人们的喋喋不休,它只管铆足了劲地适应各种气候各色土质,然后安然地生长、开花、结果。它似乎对中国的土地非常满意,温暖、厚实、肥沃,正符合它喜好被深埋、被包裹的性子。现在,它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早已发展成铺天盖地之势,位列世界三大生产国之一,将老祖宗南美洲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常常想,如果花生也会思乡,它会于梦中和那片美洲的老母土相遇吗?就像我们这些离开故土的人,终生念念不忘的,永远是故乡的事物。
我们家每年都要种花生。我几乎不记得花生需要人们特别的伺候,把种子埋进土里,甚至无须施多少肥,也不用经常给它浇水,你完全可以扔下它不管,继续干其他的农活。只消等待上四五个月的时间,它就乖乖地把一串又一串的果实给捧了出来。彼时村里有个根头叔,因为当兵受过刺激,脑子已经不太好使了。自从大嫂让他分家后,只能一个人生活。分得的那些田里,他也栽下过禾苗,可是草长得比禾苗还高,最终只收获一小箩筐秕谷。唯独那一大片花生地,出人意料地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泥土对人类是慈悲的,但它讲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花生,它却不挑人,不挑地,不挑肥地给予,这份慈悲,已接近了佛的意味。
如果把花生比作母亲的话,它绝对算得上英雄的母亲。埋进土里的一颗花生米,最后结出的是成百上千倍的果实。人们都说花生多子多福,有着吉祥之兆。所以在乡村婚娶大事中,花生是必不可少的事物。它们被撒在陪嫁的箱子里、新婚的床上,和红枣桂圆莲子一起,被赋予了诸如“早生贵子”这样热切的期盼。
在我的家乡九堡,有九件宝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之一便是杨梅村艾刀石的花生,有民间顺口溜为证:
“艾刀石,种花生,稀奇古怪,引人论争,生摇有响,晒干无声;何故如此?水分不等,壳胀仁干,果壳收紧,细细思量,科学论证。”
普通的花生都是刚挖出来摇不响,晒干了才响,而艾刀石的花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世界这么大,为什么独有这个地方的花生能长成这样?不可谓不奇也。这个传奇我自小便有听说,言之凿凿,应为真实。杨梅村离麦菜岭亦不算远,而我多年来却从未亲身前往验证品尝过,颇为遗憾。
相比于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花生,我更偏爱壳中尚裹着泥土的花生。似乎只有连带着泥土香,才不失了原始的甘美香醇。小时候,母亲一直以为我不喜欢吃花生。家中洗净晒干屯放好的花生,我极少染指。而我有一个羞于出口的秘密,她至今仍不知晓。在花生成熟的季节,我愉快地接受拔鱼草的任务,然后钻进花生地。将草拔好了,我定会拔一颗花生,坐在地里慢悠悠地吃个够。刚刚起土的花生,尚带着清新和湿润的气息。嗅着泥土的清香,咀嚼着甘甜多汁的花生仁,只觉得内心被一种幸福装满。田野寂静,只有风哗啦啦地吹过花生苗。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在密密麻麻的田畴间享受美味。
数日之后,待到全家一起挖花生,摘花生时,我偶尔还会就着泥土吃上几颗,但兴致早已大减。及至晒干,我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当然,水煮盐花生除外。但家里舍得拿来水煮的,往往是那种挑剩的颗粒不饱满的嫩籽儿,嚼劲和味道都差了许多。
我不知道和我有着同样癖好的人是不是很多,但我的确在市面上发现了供售卖的泥花生。金黄的泥土还粘在壳上,抓一把在手上,香味就悠悠地渗进鼻腔,仿佛久远的时光又一次重现于眼前。于是无论生的,熟的,我都喜欢买这种带泥的。我把它们含在嘴里,似乎就把泥土咀嚼进了生活里。
在城市里,再没有一块土地,可以供我们种植一畦花生。只有父亲时常回到麦菜岭,看望那些已经老得掉光了牙的近亲,看顾我们家那栋苍老斑驳的旧屋。他从城里给那些嬷嬷叔叔们带上松软的面包、橘饼,而那些老人,总是用抖抖索索的手,量上一二升花生,让父亲提回城里。父亲一直不忍饕餮,一颗一颗细心地剥了壳,炸成花生米,用玻璃瓶装了,放在饭桌上。吃的时候,他总是极有节制,极有耐心地,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品咂出故乡的滋味,那回味无穷的故乡的滋味啊,才不至于很快地从空气中散去。
许多年以后,我忽然回想起属于乡村教师的那段时光。我的讲台上,常常会出现一小把花生。那些农村的孩子,睁着纯净的眼睛,却无人承认是谁放的。只是七嘴八舌地说:“老师,你就把它吃了吧。”有时候甚至是一大包,无声无息地潜伏在我住房的办公桌上。那样单纯的用心,甚至令我不忍用肠胃去脏污它。
后来我知道,每天生吃一把花生,可以润肺、化痰、清咽,防治咽喉炎。而我,时常嗓音嘶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咽喉病。这些每天在我的目力威严之下小心翼翼的稚童,没有计较我的严厉,却记挂着我的隐疾。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在我离泥土越来越远以后,几乎再未有过了。
现在,我在钢筋水泥地面上生活的年头,早已超过了在泥土上面翻滚的日子,可是泥土对我捧出的东西,却永远超出于城市的给予。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离开了泥土,却用一生来怀念泥土。是的,世界上永远不缺乏这样接近于矛盾的守恒定律。当泥土越来越少,钢筋水泥越来越多。经年以后,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抔土,会温柔地,慈悲地,给予我们一个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