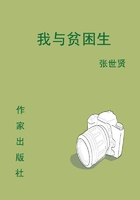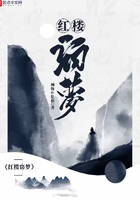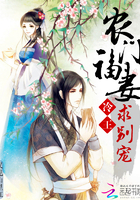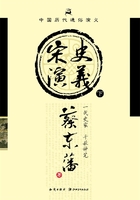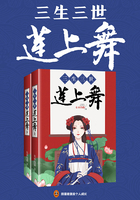偷盗的行为历来为人类所不齿,因它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实为恶举。而我在认识这种行为的性质之前,确实做过一次小偷。
儿时家境贫寒,父辈一年累到头,除口粮之外,一点钱领不到是常有的事。家中油盐酱醋的来源是母鸡的屁股,因此家里虽养了一群鸡,但鸡蛋是万难吃到的,都源源不断地进了供销社的大门。那时卖鸡蛋不论斤,七分钱一个,卖了鸡蛋才能换回生活必需品,遇到年头不好闹鸡瘟,鸡会死得差不多一只不剩,这时奶奶就要重新孵小鸡。奶奶把那只老火盆搬上了炕角,仅剩的那只生命顽强的老鸡婆(我们称它“老抱子”)趴在上面执着地一动不动,一天除拉屎吃食之外从不离窝。平时一向驯良的它忽然变得凶悍,小孩子到不了跟前,怕它的尖喙。不多日一只只小鸡就从它的身下钻了出来。从此这位鸡母亲就要尽职尽责地找食、护卫,直到这些鸡雏“撇窝”(离群)。有一年我家的一只白母鸡总是丢蛋,也不知它把蛋下到了哪里。一段时间后它居然从柴栏里领出一群鸡雏,令全家欢呼雀跃,无疑这是一位十分自觉的合格的母亲。我家的鸡一般维持十几只这个数量,多了也喂不起。所以有些出于动物本能而欲做“老抱子”的母亲们就要为此遭受许多痛苦,它们先是固执地趴在鸡窝里,哪怕身下一只鸡蛋也没有。主人为了制止这种行为而让它们生蛋,开始是打,不管用就用冷水浸头,直到它们消除这种热情才罢休。幼年的我感到的是人的残忍和母鸡的无私。
六岁那年夏天我在目睹了一窝小鸡诞生的全过程后,突然产生了探求生命奥秘的强烈愿望,一只普通光滑的蛋,怎么会钻出美丽可爱的小鸡呢?鸡蛋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决定开始自己的探究行动。自家的鸡蛋是不敢拿的,我最终选定的对象是东院的老地主家。王家是我村唯一的地主,此时地主的名头早已和财富无关。他家的鸡窝就横在我们两家中间。一天我瞅准机会到鸡窝里摸了一只刚下的还热乎乎的鸡蛋,飞快地跑到房后,我的心怦怦直跳,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激动,我就要揭开生命的秘密了。小心翼翼地磕开薄脆的外壳,看蛋清蛋黄从里面慢慢流出,并没有我预想的小小鸡,我失望极了。转念一想,可能是刚下的没有,明天再拿一只“引蛋”(用以引鸡生蛋的)。第二天我溜到老地主家的窗下,见地主婆正坐在窗前做针线,还戴着老花镜,趁她不备,我又成功了,之后依法炮制,结果仍是大失所望。当我准备锲而不舍的时候,我发现地主婆在连续丢失了两个鸡蛋(一毛四分钱)后,已将针线笸箩搬到了窗下,我的宏伟计划宣告破产。
我的这次偷儿经历使我在长大后悔恨万端,悔的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偷的对象——那时已从巨富沦为赤贫的老夫妻,他们为此损失了七盒火柴或者是一斤酱油,或者是半斤盐,这些东西足够他们消费很长时间。“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幼小心灵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否则我怎么没去西邻老贫农的鸡窝偷蛋呢?老夫妻既然始终不知道偷窃者为谁,也就无从原谅我的童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