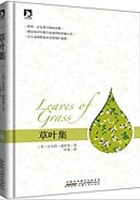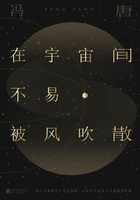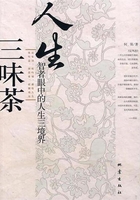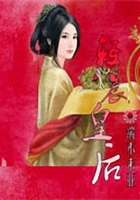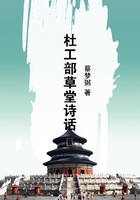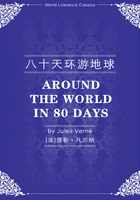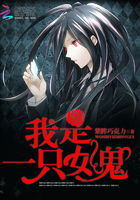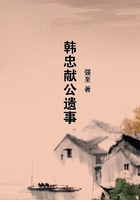七十年代初,人少地多的黑喇嘛屯来了一批山东、河北等地的盲流,善良的村支书请示公社后,一一收留。
这群盲流中,有一位相貌特别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人的嘴巴长到了右边腮帮子上。他带来了两弟弟,大家呼之曰“刘氏三兄弟”。那时,村里人没绰号的少,除了德高望重的老者,其他人往往据其特点而名之,“歪嘴子”就随之而产生了,村人认为这一称谓绝无不尊重之意,纯属客观描述。当有人问起他嘴何以歪时,答曰:小时候长疮烂掉了一块骨头……说得轻描淡写,却让人不敢想象。
别看“歪嘴子”外貌奇特,人却精明强干。不几年,他为大弟弟娶上了媳妇,新娘是当地一位相貌平平但勤劳能干的村姑,三条光棍总算少了一条。他自己呢,落下了户口,又入了党,不久即升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即便如此,也没有哪位姑娘钟情于他,也没人做热心的红娘。农村风俗,只要有残疾,即便家资丰厚,人如何好,亦无人愿攀亲。
眼见“歪嘴子”年逾三十,可急坏了乡里乡亲。终于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可一听对方的情况,就有人大摇其头。原来那是个寡妇,已不年轻,且又拖一嘟噜“油瓶”。但好心人还是讲给“歪嘴子”听了,出乎意料,“歪嘴子”沉吟片刻,竟然点了头,令一些人大惑不解。
“哼,想老婆想疯了!”
“喂,话不能这样讲,‘歪嘴子’虽是盲流光棍,可从未对哪个女人动过邪念哪!”
第一个明确反对的是他的大弟弟。有人讥之: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就这样,寡妇与“歪嘴子”只匆匆见了一面,对方谁也没嫌弃谁,当即订下婚期。
有“歪嘴子”的小弟弟和热心的村人的张罗,不久就将村部借给的两间土屋稍加布置作为新房。
结婚那天,全村人都参加了。寡妇的孩子暂住祖母家,真可称热闹非凡。
第二天,“歪嘴子”不顾媳妇的劝阻,毅然套上小马车,去外村接孩子们去了。没想到出村不远就遇到了麻烦。那是个冬天,一条雪路直铺过去。马儿正跑得欢,却见大路中间坐着个人。歪嘴子心道:当你们家热炕头呢,这是谁啊?近前收住马,你道谁一个?他的大弟弟。只见他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正哭得稀里哗啦,歪嘴子劝得嘴都歪歪到耳朵边上了,他愣是不起开。歪嘴子只好摊牌:“你那点心思我知道,放心,咱哥们虽然分开过,你们将来有困难,我当长兄的绝不会坐视不管。”话毕,把小心眼矮身材的大弟弟往车上一扔,说:“得,和我一起去接你的侄子侄女吧!开路了。”此事传出村人又给他大弟弟赐一外号——稀屎刘子。
从此,寡妇一改愁容,“歪嘴子”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干净整洁。原来破衣烂衫的孩子也因了“歪嘴子”多年的积蓄而改头换面。
每当村人过其家门,总可听见孩子亲切地唤“爹”的声音,而“歪嘴子”的回答总是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