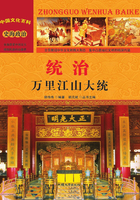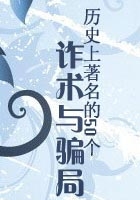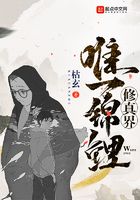毕业前夕,曹天钦遇到了重要抉择,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成都攻读研究生?当时我已病愈,在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就读。他怕去解放区后,和我见面将更遥遥无期。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通过友人介绍,他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该馆为在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和书籍。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一方面协助李约瑟为写中国科学史收集材料,一方面也了解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科研的情况。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少科学工作者还是努力在工作,曹天钦看了非常受感动。这些科学家的工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出国前他到长汀去看我,我们订了婚。由于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去英国的交通还很不正常,没有定期的轮船或飞机。他被迫在南京和上海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边工作边等待。当时我也从厦门大学毕业,来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因此在他出国之前,我们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重聚。没想到这一别又是6年。
1947年我得到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录取作为研究生兼助教,于当年8月启程赴美。1949年得到硕士学位后转到位于美国麻州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和英国的剑桥相隔一个大西洋。曹天钦本打算在得到博士学位后先到美国作一段研究,然后在我得到学位后一起回国。我们都从家人的通信中得到有关新中国的情况。感到很兴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少在美国和英国的中国同学纷纷奔回祖国参加建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了胜仗。美国政府不许中国学理工科的学生回国。当时曹天钦虽然已得到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邀请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决定,他打消了去美国的计划,坚决要我在1952年春到达英国。因他已联系好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他改变了去美国的计划,使我很失望。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听到种种关于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消息,诸如某某人自杀等,其中有的是真的,也有许多是谣传,这些都使我对回国产生了一些疑虑。同时我最担心的是回国后是否有机会进行当时刚开始的半导体研究。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根据天钦的意见,做好去英国的准备。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承认新中国,但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英国要求我要有三个月后离开英国的证明,但是我要以去英国结婚为由才有可能被允许离开美国。正在为难的时刻,李约瑟博士以个人名义到英国的有关部门担保我三个月后离开英国,我才得到了英国颁发给我的旅行证,终于在1952年5月从纽约启程去英国。当时在菲律宾的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回国,他要我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我没有听他的话,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在英国结婚后。于1952年8月乘“广州”号客轮从英国南罕普顿港启程,经历了1个月才到达香港。9月下旬我们经罗湖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广播声中进入深圳。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最高兴的是遇到从北京来的天钦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他是从北京专程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他们都向我们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限,进行思想改造。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东省教育厅只有一个干部兼管接待归国留学生的工作。我们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到达目的地上海。我们在稍事休息后即到北京探望我的母亲和曹天钦的父母及其他家人和朋友。有一些天钦的老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改了姓名。老同学吴惟正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护厂,被特务杀害。天钦很伤心。为了纪念他,我们后来给儿子起名为惟正。
回上海后即投入紧张工作。天钦在上海生理生化所开始建立实验室,我原联系到周同庆教授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经院系调整,我也随周教授到了复旦,开始繁忙的教学工作。我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课程,当时百废待兴,两个系都有很多学生,和我在厦门大学时代数理系很不相同。当时还强调要一边倒,学习苏联,用苏联的教材,或自编讲义。因此对初次走上讲台的我,是个机遇,也是挑战,相当紧张和忙碌。好在同学们对我都很好。该年进校的新生,今年刚好是毕业四十周年。前不久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在母校相聚,济济一堂,他们中有不少人已是科研院所的骨干,也有些人已退休。我一直认为,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在新中国教书的启蒙老师。
1955年我们投入“肃反”运动,当时虽然对这个运动很不理解,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参加过思想改造,任何运动对我们都是一种补课,也就积极参加。1956年春国家为了开始组织12年科学规划。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了关于半导体的报告会,当时我已怀孕,将近临产,未能前去参加,但半导体工作即将在我国开始的前兆,扫除了我回国前的顾虑。为了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向科学进军的行列,我们鼓起了勇气,向各自的支部提出了入党的申请。我们深知和许多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同志不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天钦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紧要关头,是他做出了重要而正确的抉择。现在他已离开了我,在党的领导下,我将继续勇敢地向前。
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为《风雨同舟半世纪》作序
谢希德
上海政协之友社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风雨同舟半世纪》一书,在众多社员的支持下,经主编王兴和全体编委、作者的共同努力,编书事宜进展顺利,行将付梓。对此,我深感欣慰。
作者们大多是退下来的历届委员和部分长期从事政协工作的老同志,他们根据各自在政协舞台上的实践和感受,精心构思,认真下笔,写出篇篇华章,这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献上的一份火热的、诚挚的心意,是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是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笔思想财富。
就我个人而言,自任第二届市政协委员开始,直到今天被选为上海政协之友社理事长,期间虽中断数届,但和人民政协仍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我出任第七届政协主席,感觉上还是一名新兵。由于教学、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繁忙,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对政协和政协之友社工作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10年来,我向大家学到了许多政协工作的经验,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当本书出版后,我在捧读之时,想必是又一次和大家重温美好友情的极好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协,好比是一个充满团结、民主氛围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家庭。退下来的委员们的职责虽已不同于在任之时,但依然是政协大家庭的一员。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社员们个个都是有着丰富阅历的长者,个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50年发展的见证人,个个又是根据各自特点在社会上发挥不同作用的可敬可爱的老人。想及此,更使我对我的前任——第六届市政协主席李国豪教授深怀敬意,是他首倡建立政协之友社。上海政协之友社自1987年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她是有生命力的,有凝聚力的。本书在短短半年内编成出版,也是一个明证。我为此由衷的高兴。正像书名所揭示的,我们大家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地走过了半世纪的历程。21世纪在向我们招手,而过去半世纪里大家风雨同舟的经历,必将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里取得更大胜利。
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