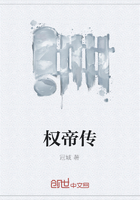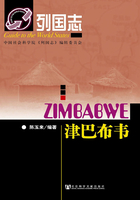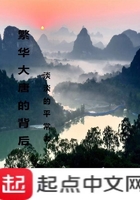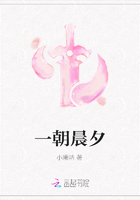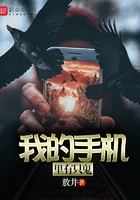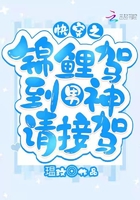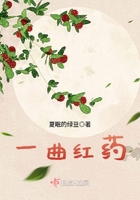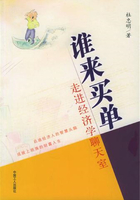1988年,已步入生命黄昏的谢希德完成了由大学校长到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角色转换。虽然人们仍叫她“谢校长”,虽然她的学者身份依旧,但这个熟识的身影从此更多地活跃在另一个舞台上了:她主持政协会议,她率委员深入基层调研课题,她上电视、报纸发表真知灼见,她会见外国友人,她出席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而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则往往从电视新闻里、从曹天钦教授的病床边,交换着角度——一会儿是主席,一会儿是妻子,注视这位素朴、典雅的名女人。
欢乐颂
有段时间,和人一说起谢校长,我的心里就会浮出“伤花怒放”“蚌病成珠”之类的词汇。那是何等锐利的叫人心痛的美丽啊!
可是现在,我坐在同样位于麻省的波士顿的书桌前,轻轻敲打出这篇文字的时候,谢校长促使我思考人生:一个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几乎终身与病痛相伴相随的弱女子能够成就为一部传奇?人的一生究竟应当怎样走过才算没有虚度?为什么大多数没病没灾的人反倒一辈子庸庸碌碌?我们如何去争取使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成正比?……
我的眼前,回闪过一组组温馨的镜头:她爱穿一色的套裙配以鲜亮的真丝衬衣,她理发的时候捧读英文小说,她用弹钢琴的双手给第三代的小婴儿换尿布,她访美为病榻上的丈夫带回一台配有教程的小英文打字机,她每周出一些数学题发E-mail给在美国的孙女练习,她在物理系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夹了Einstein的名言“A clean desk is a sign of a sick mind”,她戴了老花眼镜宽容地审读我的专访稿,她在政协主席会议间隙疲惫地小憩,她中午到文化俱乐部简简单单地吃一碗面条……
我想,几时去一趟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查阅半个世纪前这位中国女子的博士毕业论文。我不会读懂相去甚远的物理学专业,但我相信会读懂泛黄的字里行间跳动的音符,因为那正是谢校长“第九交响曲”的旋律啊!
有的人死了,她还活着。
让我们为这精神之永恒,高歌一曲《欢乐颂》!
四年疾病折磨 三次高考搏击
——谢希德的学生时代
醒梅
国家在胸中
在一艘由福建北上的轮船上,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唱一首流行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几个大哥哥一旁和着她。轮船缓缓开进上海港,这时大哥哥正色对她说:“过了上海就不能再唱这首歌了。”“为什么?”“因为北方有军阀。”女孩虽然不太懂,但从此心里有了“军阀”“列强”这样的一些概念。
这是1927年的谢希德。当时谢希德父亲谢教授到燕京大学任教,全家跟去。谢希德在燕大附小、附中及贝满女中读书,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七七事变后,谢希德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活,先是来到武汉。父亲到湖南大学任教,她则考入圣希理达中学读高三。本来一般学校高三不收插班生,但国难当头,逃难学生不少,便破例收了她。可仅此一学期还未读完,武汉受到威胁,全家又逃到长沙,谢希德转入长沙福湘中学,毛泽东夫人杨开慧曾是该校学生。当时教谢希德国文的老师是李淑一的父亲,学期结束她考了第一名。
谢希德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这使她强烈地感到,没有一个强盛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安定的生活。所以1952年,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虽然她身在美国,又是美国禁止回中国的物理学科学家,但她还是转道英国,与她在英国的同学、生物化学家曹天钦结合后,同道回国。
挫折压不倒
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统考,她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由于父亲在湖南大学教书,为便于照应,也就考入湖南大学。就在这时灾难出现了。
一天,她突然感到腿痛,以为是扭了,并不在意,可疼痛一天天加剧。在长沙湘雅医院拍了X光片,医生认为骨头没问题,作为风湿来治。然而没有用,终于,不能走路了。这时,又开始逃难到贵阳,由于公路路面很差,到了贵阳病情加剧。令她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39年2月4日这一天,大批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因她不能走动,母亲和弟弟也没有逃入防空洞,炸弹在离她家很近的地方爆炸。这时候,如果炸弹偏一点点,那她们家就只留下在长沙没有同来的父亲了。
千方百计入住医院,那时南京中央医院一批医生也来到贵阳,经重新拍片,确诊为股关节结核。可那时没有特效药,只能牵引,把发炎的关节松开。痛是不痛了,但不能动,当然不能读书了,只好休学。牵引半年,以后上石膏把关节固定,每上一次是半年,连上3次是一年半,加上先前卧床1年,一共3年过去了。病是好了,但下床后不能走路了,学习走路又用去1年。这时浙江大学搬到贵州湄潭,于是她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考入浙大。还未及读,她的父亲转去厦门大学任教,当时厦大迁至福建长汀,那里交通不便,日寇没有侵入,她第三次参加高考,进入了厦门大学。虽然她走路不方便,但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和意志。
就这样,高中毕业后,她经过4年疾病的折磨和3次高考的考验,终以优异成绩进入了高等学府。
一寸光阴一寸金
在她卧床的4年中,光阴似乎应该从她身边悄悄溜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不少人来看望她,当然有人送给她吃的东西或鲜花,但也有不少老同学送书给她,其中有一些英文小说,她就看了起来,可好多看不懂,怎么办?查字典又不方便,她硬着头皮看,从上下文关系中来揣摩、验证,日积月累,她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病愈后她的英文水平超过一般的同学,同时她还自学数学与物理,读大学时轻松不少。
谈及往事,谢希德笑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4年卧床,我的知识面扩大了不少,我高中毕业的时候17岁,是全班最小的,但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5岁了,是全班年龄较大的了。”
她影响了我的一生
——复旦博导朱传琪与谢希德的故事
郭颖
“因为谢校长的信任,我才得以出国,又是因为她的信任,我回来了。”提起谢希德教授,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朱传琪一脸的敬重。
1982年,已在计算机并行处理方面颇有建树的朱传琪得到了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作学术研究的机会。但在当时,却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为此,朱传琪找到了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谢希德。“谢校长思想解放,对后辈非常关心。”朱传琪想出国深造的想法,得到了谢校长的理解。不久以后,朱传琪出国的事便“批”了下来。按规定,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满2年就应回国,但朱传琪参与了历时7年的美国计算机领域重大项目——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从申请经费到研究完成的全过程。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研制人,朱传琪当时有些“舍不得”马上回国,希望能在美国多留2年。于是,他又写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谢校长。
1984年,谢希德访美期间,专程从芝加哥驱车几百里到伊利诺大学看望朱传琪。“谢校长当时就同意了我的想法,她对我说:你需要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回来。”1986年,已分居太长时间的朱传琪夫妇想团聚一下,又是谢校长为他妻子赴美作担保。“谢校长对我的这种信任实在太令我感动了!”朱传琪后来才听说,为了担保他妻子出国,谢校长当时是承受了一定压力的。
尽管从并行处理计算机研究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来说,伊利诺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与朱传琪共同研究的库克教授也为他办好了留美的一切手续,可项目一结束,朱传琪便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他对热情挽留的美国人说:“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
1988年,朱传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复旦校园。“报到的第二天,谢校长就安排学校有关方面,解决了我的职称问题。要知道,当时提教授的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谢校长特意为我留了一个名额呵!”
已获得“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的朱教授真诚地告诉记者:“谢校长将永远是我的人生楷模!”
生命是可爱的
——我所了解的谢希德先生
孙小琪
归国,心灵深处的呼唤
谢希德,1921年3月出生于依山傍海的泉州。父亲谢玉铭教授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一,曾长期在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他终日埋首书房的身影给了少年谢希德极大的影响和熏陶。
谢希德的青少年时代,一面是积弱积贫的祖国;一面是五四运动唤起的民主与科学的觉醒。摆脱强权压迫,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浸润着两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发奋读书学好本领,是当时谢希德生活的主旋律。1946年秋,她在厦门大学数理系毕业,一年后即赴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物理系任助教,同时攻读硕士,以后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理论物理。青年谢希德很幸运地有一位志同道合、相知颇深的男友,名叫曹天钦。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闽西万山丛中依依惜别,曹天钦先谢希德一年去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化学和生物化学。整整五年,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无情地隔开了两个热恋着的年轻人,但共同的志向又使他们在频繁的书信中亲密无间。纵然远离故国,在留学生中间辗转流传的进步报刊,使他们的脉搏和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像划破苍穹的闪电,飞越万水千山,飞渡大海重洋,传到英伦三岛,传到波士顿城。两个年轻人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互相告勉:一旦学业结束,马上启程回国,把青春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51年,已获博士学位的31岁的曹天钦,被剑桥大学Caius学院破例吸收为荣誉院员,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英联邦科学界获得荣誉;同年,刚满30岁的体弱多病的谢希德也获得博士学位。
回祖国去,回祖国去!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执拗地在耳畔回响。他们归心似箭,一面节衣缩食积攒路费;一面冷静地筹划归国路线。
就在这时,在朝鲜战场屡吃败仗的杜鲁门政府突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时间议论纷起,传说有些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被扣押、威胁。
怎么办?惊讶而愤怒的谢希德没有动摇;1952年3月,和她心心相印的曹天钦拍来一封急电,决定取消原定的到美国和谢希德一道返国的计划,让她想尽办法尽早来英国,并且告诉她,已经订好了两张回国的船票。他们要把英国作为回到新中国的跳板。
然而,英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谢希德几番穿过悬跨于查理士河上的铁桥,走进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百般说明只是路过英国而不会久留。但她没有成功。曹天钦向他敬重的李约瑟博士求助。由于李约瑟先生在英国科学界的声望,内政部官员只得把电话打到波士顿。
1952年8月,一艘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部南安普敦的海港码头拔锚启程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们的急切就像孩子要扑向母亲的怀抱。
谢希德顾不得拍打身上的仆仆风尘,立即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矮小却不知疲倦的青年女教师。
当时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尚处于初兴阶段,教材十分缺乏。常常是她刚刚开设了一门新课,编好教材,打好基础,又根据需要去准备新的课程,把这门课交给别人去教。
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披肝沥胆
1956年的一个晚上,当容光焕发的谢希德推开家门,几乎同时,和她同样激动万分的丈夫曹天钦也脱口而出:“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这一天,他们各自被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为了奠定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在不长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党中央决定,把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电子学列为主攻方向。
十万火急的军令,从中南海传遍全国,各路兵马迅速调集,一场威武雄壮的科学攻关大战即将打响。国家决定集中复旦大学等5所高校物理系部分师生,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半导体专门组,加速培养专门人才。谢希德接到通知,兴奋至极。她在美国就参加过半导体研究,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展半导体科学。现在,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而且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这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
谢希德像出征的战士,告别亲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尽管当时她唯一的孩子刚满5个月,但她没有丝毫犹豫,不无歉疚地对同样忙碌不堪的曹天钦说:“我走了,你又做爸爸又做妈妈吧。”
两度春秋,一个病弱的身影时时在风光秀美的未名湖畔奔忙。白天,不会骑自行车的谢希德不辞辛苦地从宿舍奔往几里外的教室,又匆匆奔往距离更远的另一个教室。她在和时间赛跑,和遥遥领先的先进国家竞赛。夜阑更深,燕园睡了,她的宿舍依然灯火通明,她在不知疲倦地翻译国外文献,起草讲稿,同教员们一道研究教学方案,作业务辅导。
1958年,谢希德和黄昆教授成功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的科学论著《半导体物理》,这是一部在当时国际上堪称权威的专著。
两年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半导体专门人才300多名。半导体的种子从未名湖畔撒向大江南北,从实验室的单炉撒向工厂车间。近代物理学的一项最新成就奇迹般地在我国广泛普及,连小学生也开始学着装配半导体收音机了。
为我国半导体科学的诞生付出辛勤劳动的谢希德,马不停蹄开始了新的艰巨而富有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