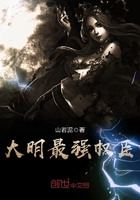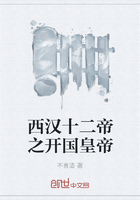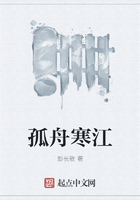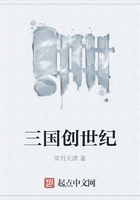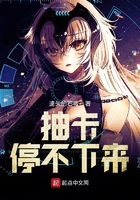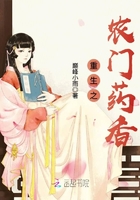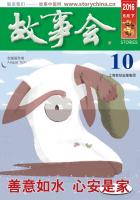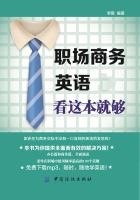回到上海,她一面主持筹建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同时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与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技术物理研究所。国家把培养我国固体物理专门人才的任务交给她,要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在固体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成果,填补这门学科的空白。
教学、科研,谢希德恨不能一天多出几个小时,多干一点,干好一点。每天天刚蒙蒙亮,她便已等候在市区西南端的公共汽车站,然后搭早班汽车斜穿整个市区,到地处东北端的复旦校园上班。她总是提前到校开始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当城市的灯火早已闪烁辉耀的时候,幼小的孩子往往等不到妈妈回家,便呼呼睡着了。一身疲惫的谢希德回家,必定还要在灯下工作到深夜:审定、修改研究生的论文,替青年教师校对翻译的外国文献,连夜起草给兄弟科研单位进行学术辅导的讲稿……
几年时间,她同方俊鑫副教授合编的《固体物理学》出版了;她和助手们以硒化锌、锑化锢的能带研究获得初步成果;他们先后在《物理学报》《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群论在固体物理研究中应用的科学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揭开物质结构的奥秘有积极的意义。
1965年冬,谢希德作为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英国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当她走出机舱,她的眼睛湿润了。13年前,她仅仅要求在这儿转程,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必须限期离境;然而今天,她作为新中国一个科学代表团的团长,在这儿受到尊重和欢迎。祖国母亲的神圣意识又一次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扉。在参观中,她向朋友们介绍新中国的科学成就,也向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物理学的最新动态。她感到自豪,让祖国插上科技翅膀腾飞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鼓舞着她,催促着她。
两代物理学家的沉重话题
1998年7月,有过多次患病经历的谢希德突然觉得很难受,到医院一查,很快被确诊为乳腺癌,立即住院治疗,并在上海罕见的高温天气里又一次作了右侧大面积切除手术。手术前,她还在华亭宾馆主持了“98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不少境外专家是由谢希德出面邀请的,大家对发展上海的高科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手术后谢先生恢复得很好。医生在病房门口贴出“谢绝探望”,但来探视的人依然很多,床前、窗台上始终摆满了鲜花。
谢希德4岁丧母,以后继母生了几个弟弟,父亲谢玉铭对家里唯一的女儿、自幼多病又勤奋异常的谢希德十分钟爱。父亲1946年去了菲律宾,1947年谢希德去美国留学,父女间常有通信联系。
1952年回国后就和父亲断了联系。
谢希德的父亲和杨振宁的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是同学,相交甚深。杨振宁和谢希德是同辈人,他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文中写道:“我很偶然地在一本研究物理学史的书中发现,在发现重整化概念的实验与理论的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加州理工大学工作过的谢玉铭教授有过重大贡献,他与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先于后来因此发现而两次获诺贝尔奖者10多年。”向来对推介中国科学家成就极其热心的杨振宁非常兴奋,又猜想这可能就是谢希德的父亲。正巧不久谢希德访美与他通话,杨振宁便在电话里问她。《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十分简洁真实的笔触,描述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因为那之前不久,谢希德突然得到消息,父亲在台湾去世了。父女情深,又是同搞物理学且有相当成就的,但他们有整整40年不通音信!他们没有任何讨论物理学的机会。谢希德在电话中对杨振宁说:“他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杨振宁对这个“真实的故事”未做评论,谢希德在《杨振宁传》的“序”中谈到这次电话和这篇文章时称:“这些对我心中的震动,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杨振宁先生使她了解了父亲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这是无法释怀的思念,也是一个女儿为父亲的成就而体验到的无比自豪。除此,她还能说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忠孝不能两全,就像精忠报国的岳飞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当时他知道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就写信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去世后有人把他的遗物带回大陆,发现所有我给他的信和照片都在,他一直保存着。”
谢先生说她后来有机会去台湾,看了父亲最后几年生活的地方。别人告诉她,父亲是常常对人说起她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教授的大弟弟的,但她却从未在父亲生前听到过。
“对于视祖国的荣誉、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谢先生,她别无选择!”
几经周折 回到祖国
郭颖
要想了解半个世纪前谢希德和夫君曹天钦满腔热情地回到祖国的历程,不能不采访王应睐。因为,当年正是他“成全”了年轻的谢希德、曹天钦夫妇的报国理想。2000年3月16日,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中科院院士王应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时曹天钦在英国念书,谢希德在美国念书,他们已经订婚并且都获得博士学位。”本来,曹天钦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但曹天钦剑桥大学的同学邹承鲁的造访,激发了曹天钦的爱国热情,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他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尽管父亲反对,可谢希德还是支持曹天钦的选择,两人在信中商定:由曹天钦去美国,两人完婚后一同回国。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美国在朝鲜战场失利,杜鲁门政府禁止在美学理工的中国学生回国。夫妇俩不得不改变计划,由谢希德申请去英国。
几经周折,1952年8月,新婚宴尔的曹天钦、谢希德夫妇终于离开英国,在南汉普顿登上了“广州”号海轮回到了祖国。谢希德于8月到复旦大学报到,执教于物理系。当时尽管谢希德只被评了个讲师,可她毫不气馁,全力以赴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谢希德就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固体力学等七八门课程,为复旦物理系日后的学科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不久,谢希德即被正式提升为教授。
在科学的春天里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除了校务工作外,我还挤出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了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我十分珍惜科学春天的到来,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再立新功。
——谢希德
“明智的选择”
黑夜终于过去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焕发了谢希德的青春。她在人妖、病魔双重折磨下,非但没有躺倒,反而以更坚强、更充满活力的姿态,迎来了祖国科学的春天。
1977年8月,分管科学教育的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科学、教育领域出现了完全崭新的面貌,知识分子受到特别鼓舞。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党中央的号召,如阳光、雨露,照亮了科学研究的道路,也滋润了谢希德久旱的心田。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更专注地思索,如何夺回损失的时光,加快科学研究的进程。
早在1977年,谢希德就认真查阅了国内外专业文献,发现清洁的半导体和金属表面和界面问题已有很大发展,涉及许多学科,已经形成介乎表面物理、表面化学和材料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正如国内一位物理学家曾说过的,“我们沉睡了10年,在苏醒之后,面前出现了一片大好森林,这就是表面物理。”谢希德注视着查到的大量新资料,思索着奥妙而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不锈钢不会生锈?是什么起了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苏美两个大国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4000万吨左右,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
专长于半导体和固体物理研究的谢希德,如果继续搞她的半导体,可以说既省力,又稳妥,还可以快出成果;如果从事表面物理研究,即使付出艰辛的劳动,五年十载能否取得显著成绩,仍是个问题。然而,她不是守业的人,表面科学亟待人们去研究,哪怕付出10倍、20倍的代价,也要勇闯难关,有所创造。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鼓励年轻的同事们,去开拓这个有前途的新领域。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谢希德摸清了表面物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有三部分:一是确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结构和成键性质;三是表面的电子态和各种特具的物理性质,也弄清了表面物理同国民经济和科学发展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例如,寻找有效的抗腐蚀保护层,以减少钢材的损失。表面物理和量子化学结合,将为催化科学理论的建立拓宽道路。有人更认为,有效的能源依赖催化科学发展,更显得表面物理是何等重要,半导体集成电路规模越做越大,要进入原子级的加工,更需要在原子线度的范围内,认识表面的各种物理性质,以便于提高集成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为探索新器件、新材料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对新开拓的研究领域的认识,正在一点一滴地聚集着,逐步系统化。时机终于来了。1977年11月,谢希德教授应邀出席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会上,她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大胆地提出填补我国表面科学空白,发展表面科学的建议,并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赞赏和国家科委以及高教部的支持。返校后,乘规划会的东风,谢希德满怀信心地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现代物理所。奔波操劳换来了收获,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复旦大学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研究室。
各科各系每一个实验室的建立,都像一颗颗明珠缀嵌在复旦校园里。这些闪烁着科学之光的“明珠”在草坪间,在校舍里,甚至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着光和热,点缀着复旦大学这座科学“不夜城”。
1978年9月底,谢希德又拟订了两个计划,组织两个讨论会,一是表面物理,系统讲述表面物理的基础内容和发展前景;二是固体能带理论,并安排好参考文献供报告人阅读。7个多月,她带病亲自组织的报告不下30次。
与此同时,谢希德教授还把过去写下的《群论及其在固体中的应用》讲义,请几个同事协助,整理成书,于1986年由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她还编写了有关《表面物理》讲义。至1992年上半年为止,谢希德和同事们一起,已写出40多篇学术论文,大部分已发表。
1982年,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科恩(WalterKohn)教授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表面物理实验室在“六五”期间,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在“七五”期间又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列为重点科研支持项目。1990年,国家计委组织专家评审,并确定该实验室为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开放实验室,继续给予支持。
欧美之行
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7届国际会议于1978年9月11日至14日在西德慕尼黑附近的伽兴召开。谢希德作为团长,带领一个8人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西德的一些实验室作了参观、访问。随后又应法国巴黎奥赛核物理研究所的邀请,在巴黎参观了2个研究所和3所大学。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谢希德的第一次出访。呼吸新空气,增长新见识,借鉴新成果,使她感到很兴奋。许多外国学者都对我国代表团十分友好,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对国际科学交流的态度,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希望今后继续保持联系。戴玻尔教授刚从美国回来,没有休息就赶来与谢希德一行会面,邀请全体人员到他家中共进晚餐。后来,当谢希德他们从海德堡重返慕尼黑要离开时,戴玻尔教授又亲自到车站和机场迎送,甚至协助他们搬运行李。其他许多西德和法国的物理学家,有的邀请他们到家中喝茶,有的在居室里为他们举行小型晚会,有的特地设宴招待他们,表现出极其热情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愉快和感动。在巴黎参观时,几位大学校长和科学机构负责人,一再对我国派遣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表示欢迎。
出国访问是向国外学习的好机会,多年来,谢希德总是带着问题,在访问期间认真观察、询问,并把收获记录下来,下面就记载了她访问报告中的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