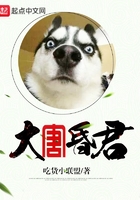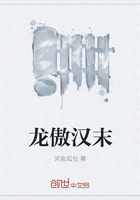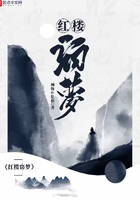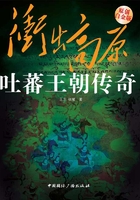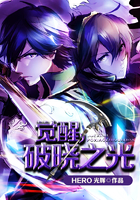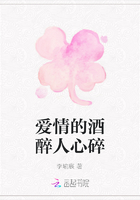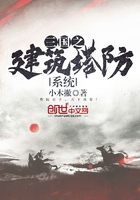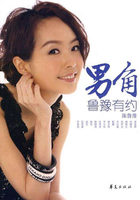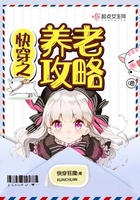北宋仁宗皇祐三年,浙江宁波东钱湖畔的一座小楼里,一位老人在酒桌前,已经坐了快一个时辰。酒肆的小二几次把目光投去,想从他身上看出一点什么消息,最重要的当然是看他有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喝下的两坛白药酒。
小二并不知道,窗边坐着的这位鹤发如丝的老人,只是于辗转途中路过此地。他更不知道,这名落拓的旅人,日后将会成为一名名垂后世的词人。他只是隐约看出来,这个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碜的老人要支付他喝下的酒,似乎确实有些艰难。
老人看着窗外东钱湖上雨过留下的薄烟,和薄烟中渺小的舟子,伸手拿起酒杯,杯中照见了他早已黯淡的神色。这是六十八岁的容颜。他还能饮,能诗,看见漂亮姑娘也还能有良好的反应,所以他没意识到,这是他去世前的倒数第二个年头。
他看见杯中的自己,忽而想起考上科举的那年,那是四十七岁的自己。这些年来,他常常梦见京中的繁华,尤其近几个月,酒肆之中酣眠,白马系柳,笙歌如云,少年的光景和壮年的慷慨,历历眼前。然而京师虽大,却已渐渐容不下他这个瘦弱的词客。漂泊在江浙淮扬之间,卖词鬻文,买酒买乐,个中滋味,更与何人说。更与何人说?想到自己的字句,他不禁笑了。当时光流逝,残躯暗老,往事剩下的只是一些字句罢了。那些早早写下的字句,又成了如今的谶语。他轻轻叹了口气。毕竟是年龄大了,再美的姑娘,简单地看着就已足够。他甚至开始想念武夷山下的家,人一旦老去,总无法避免这样的情绪。
杯中酒已尽,老人拿起粗陶酒坛,却再也倒不出来一滴。暮色越来越重,酒意也凶猛地窜了出来,仿佛潜伏已久的凶禽,终于找准时机扑向猎物。酒为猎手,饮酒者就是猎物。他捋了捋稀疏的银须,低声起了一曲小调,窗外的景色,竟忽然温顺得如同一只猫,乖乖地躺进了曲调之中。词句如这湖中的生产的乌青鱼,从他的松动的齿牙间滑落而出: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懂曲儿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曲《安公子》。吟罢时,他并没有在意这首词的命运,和大多数篇章一样,写了也就忘了。直到一个月后的一次宴饮里,应主人邀请制词,一时无对,才想起这曲《安公子》,便胡乱拿来作为搪塞。现在,他起身从兜里掏出一贯钱,扣下几文,其余都给了柜上。柜上的先生穿着也不甚讲究,却并不急着收钱,向柳永道:
“恰才听尔唱词,皆是未闻之作。其非君所作乎?”
老人作势向北面一拱手,苦笑道:
“某奉旨填词罢了。”
柜上先生一时瞋目而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面前的人便是闻名已久的柳永柳三变,眼前人却已转身下楼,飘然而去。他知道,柳永与当地县官刘和邕是少年知交,柳永自荆州放舟而下,便是来应约的。不想,今天却亲眼见到了这位大才子。柜上的本是个落第秀才,小九九打罢之余,于诗词歌赋总不能自已。甚至颇能颂柳永佳句,只不知柳永是何等风流人物,今日一见,却是如此这般的糟老头子!
柳永仍是不愿回乡。儿时的柳永,第一次在私塾拜师,先生问他:
“耆卿,汝读书将有何求?”
“求圣贤之学,成有用之身,佐尧舜之君,传名于天下耳。”
在入私塾之前,童年的柳永便有诗文流传于乡里,其中一首《中峰寺》尤为乡里书生秀才所称道。先生曾给他的父亲柳宜说:
“令贤郎天纵之才,然……然吾恐其才大难用也。”
幼年的柳永还不明白先生的话。现在他似乎开始懂了。
他漂泊的心,已经被秋风吹动。虽然听得“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可他往何处归去?他不意回故乡,回故乡又有何用呢?只好再度入京。
十月的秋风萧瑟,刘和邕给柳永包裹了盘缠,柳永便在这萧瑟的秋风里,匆匆北上。
他记得,第一次北上入京,是一个温和的春日。只不知是季节迎合了人,还是人迎合了季节。那时的柳永,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谁能知道,这一去,便在汴梁耽了二十五度春秋。而在这二十五年里,他最不能忘的一个名字,便是陈师师。
少年时的柳永,鞍马白衣,文采灿烂,虽然没有功名,却是京中的才俊翘楚。京中女子多有歌谣唱到:
“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歌;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柳永在家排行第七,歌中的柳七,便是他无疑。五陵子弟闻此,争相结识他,以为也能让自己沾染一点才气,多讨得女孩的一丝欢心。柳永小心地应付着,他知道,这些人或许能让他在科考以外,尚存一线进身的机会。他的考虑实际上并不必要,他想要的名声,早已传到了天子阶前。在天子看来,这样的少年才子,恃才放浪,尚需磨砺几年方才可用。也许,这便是当初私塾先生所谓的“才大难用”。
京中的青楼最佳,是城东的倚红楼,倚红楼最佳,便是陈师师。陈师师有着青楼女子不该有的清傲,当姐妹们小生议论柳永的时候,陈师师总是冷冷地望上一眼,极为不屑地走开。姐妹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陈师师的脾性她们已经习惯。而她们不知道,陈师师的房间中,藏着一本用蝇头小字誊写的《柳三变词》。若是她们知道了这个,必定又会叽叽喳喳,叫个没完了。
柳永第一次见到陈师师,是被一个叫赵文浦的贵冑少年所带去。倚红楼是柳永常去处,只是,陈师师这样的头牌,没有引见是见不着的。倚红楼规模之宏大,俨然一座殿堂,金碧辉煌之间,却难得的不透出丝毫俗气。京中达官贵人,风流子弟,往往来此寻花问柳,倚红偎翠,竟至于乐不思蜀,散尽家财者常常有之。
陈师师的闺房很大,便是寻常人家小姐,也不见得有如此气派的住宿起居。绣帘之后,陈师师的倩影绰约,柳永正要上前,赵文浦拉着了他,又拍拍他肩膀,径自走了。柳永一时方寸大失,半晌,道:
“姑娘……”
话正说着,他听见绣帘中传出陈师师的温柔的声音:
“‘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先生便是柳耆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