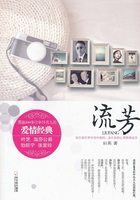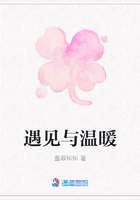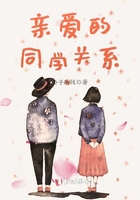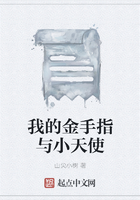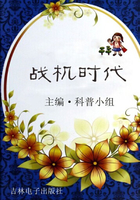赵义山
我于赵玮、张强两位青年学者,一直未见其人,却有缘先读其文。去年8月,赵玮将他们的《〈林石逸兴〉校注》书稿寄我,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意见,无奈事冗,未能通读。但凭我所抽看的一些篇目,发现他们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也较为踏实,且又虚心向学,遂就管见所及,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数月后,赵君告以修订完毕,希望我能再读一次,我也答应了,结果却仍未如愿,实在有负他们的热望。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经他们认真修订之后的书稿,其校订与注释,当更简洁明了,确凿有据,于薛论道散曲之研读,当大有帮助。他们辛勤爬梳几载的著作即将付梓,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思前想后,倒还真有一些话想说。
首先是对于《林石逸兴》的作者薛论道,我想说,他的确是一位才华卓荦却又很不幸的人。薛氏字谭德,号莲溪,生当嘉靖、万历间。幼年多病,至一足残废,乃身体之不幸;未及冠而孤,乃家门之不幸;博学能文,又喜谈兵,从军30年,屡建奇功,然终遭疑忌,未能腾达遂志,此乃人生之不幸;所著《林石逸兴》,其金戈铁马之声,足可警醒曲坛,而自明清以迄现代,却几乎被学人遗忘,此乃文章之不幸!何莲溪不幸如此之多,不仅人妒其能,而天亦嫉其才乎?此真莲溪之不幸,抑或乃晚明之不幸与曲学之不幸耶?然莲溪其人其曲,近年来终于得到治明曲者的重视和较高评价,此又不幸中之万幸也!
其次,是对于《林石逸兴》一书,我想说,这又是一部很不幸的书。该书收录莲溪所作小令达999首,是中国散曲史上存曲最多的一部散曲别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已有刻本,或因其流传未广,被发现较晚,不仅明清曲论家未尝置论,近人任中敏《散曲概论》、卢前《散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等,也都全然忽略,直到20世纪后期,一些较有影响的散曲史论著,依旧置而不论,与一些存曲不多,却因曲家置评而广为人知的曲集相比,莲溪《林石逸兴》一书之遭遇不幸,可谓绝无仅有!然此书终有赵玮、张强二君为之校订注释,并即将付梓,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
再次,我想说的是,因为曲学界长期以来对于莲溪散曲创作,以及晚明整个北派曲家如薛岗、王寅、赵南星、丁彩、丁惟恕等人的忽略,便导致了“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的偏见。这一偏见,自20世纪30年代起至20世纪末,影响明代散曲发展史研究长达60余年,似乎直到拙著《明清散曲史》出,才最终得以澄清。事实是,昆腔以后并非只有南曲,而依旧是南北曲并行曲坛,只不过北曲不敌南曲,未能盛行歌场,已大多退位为案头创作。有人或据此鄙薄,我在《明清散曲史》中却另有看法:“流行歌坛者,虽活于歌者之口,但作者或旨在应歌,临纸握笔,为文造情,口不应心,亦多有焉;而退于案头者,其曲虽死,但作者以之抒情写意,我手写我心,其词或多发于性灵;两相比较,曲活者或情伪,而曲死者或意真,故不可以北曲未能传唱歌坛而予以轻视忽略也。”
复次,我还想说,莲溪是晚明曲坛上一位用心于散曲创作而且成就极高的作家。他在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所作的《林石逸兴》自序中有云:
殆我圣朝人文极盛,政化是务,而声律渺矣!儒者陋而莫为,庸者为而莫耻,是以清歌雅调烟灭灰飞,俚语淫声塞衢盈耳。休明盛世,而声教坠之(一作“之坠”)若此,宁无惜乎!余少读章句,时趋庭履市,过则掩鼻,深不欲污吾之耳。既而学以病废,竟堕武流,自分樗散,无堪世用。乃游心乐圃,用情词苑,颇得音律之微,歌咏之趣。或感慨于夙昔,或游睹于心目,辄敢望其谫陋。昼咏宵兴,措得千曲凡十种,一种百首,每百首析为一卷,共得十卷,名曰《林石逸兴》。其所制作,或忠于君,或孝于亲,或忧勤于礼法之中,或放浪于形骸之外,皆可以上鸣国家治平之盛,而亦可以发林壑游览之情。求无声律之弊,或庶几焉,曰工则未也。
由此可知,莲溪是有感于明代曲坛之“俚语淫声,塞衢盈耳”,遂有志于拯衰救弊,“乃游心乐圃,用情词苑”,并对自己能“得音律之微,歌咏之趣”颇为自负。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入世又玩世的曲学观:他一边倡导着“忠君”“孝亲”“勤于礼法”,一边又“放浪形骸”“游览林壑”,乍看起来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执著的入世者,其玩世则仅仅是因为入世而不得志,以求心态的调适而已,这正反映出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对于莲溪散曲创作的成就,我在《明清散曲史》中曾有较详论述:莲溪南北曲兼作,其题材内容相当广泛,举凡叹世、归隐、言情、写景、咏物、抒怀、咏史、怀古等曲中常写的内容,《林石逸兴》莫不具备,而举凡诗词所能写者,莲溪又莫不写之于曲,就此而言,他是可以与冯惟敏相提并论的。在他众多的散曲作品中,以写边塞军旅生活最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或抒写将士的报国雄心:
腥膻何敢易天朝?颇牧山林妆睡着。九重但肯颁一诏,把燕台增尺高,论割鸡焉用牛刀?轻踏碎单于道,慢折磨可汗巢,贺兰山瓦解冰消。(【双调·水仙子】《宿将》第四首)
朝廷命我镇边关,一线封疆万里山。旌旄到处遮云汉,把胡儿心胆寒,净烽烟国泰民安。准备着擒可汗,安排着系呼韩,大将军义胆忠肝。(【双调·水仙子】《为将》第四首)
或抒发久戍不归的惆怅情怀:
两眉不放,望白云几回断肠。白日里身在胡天,到晚来梦绕高堂。半生壮志自堪伤,一片乡心万里长。(【仙吕入双调·玉抱肚】《乡思》第四首)
或描写战骨抛荒的悲凉情景:
拥旌麾鳞鳞队队,度胡天昏昏昧昧,战场一吊多少征人泪?英魂归未归,黄泉谁是谁?森森白骨塞月常常会,冢冢碛堆朔风日日吹。云迷,惊沙带雪飞。风催,人随战角悲。(【商调·山坡羊】《吊战场》)
或反映戍边将士的落寞人生:
玉门迢雅蹄奔绽,铁衣寒征袍磨烂,将军战马岁岁流血汗。功名纸上闲,秋颜镜里残。烽烟历尽壮志逐云散,酒郡无缘青丝带雪还。知还,一身得苟安。求安,余生得瓦全。(【商调·山坡羊】《塞上即事》)
或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甸奴未灭,壮怀激烈。空劳宵旰忧贤,那见虏庭蹀(一作“喋”)血?任胡尘乱飞,污辱郊社。堂堂中国,谁是豪杰?萧萧白发长扼腕,滚滚青衫弄巧舌。(【仙吕·桂枝香】《宿将自悲》第四首)
这些曲子豪情激荡,感慨深沉,或有盛唐诗人的壮怀,或有中唐诗人的感伤,或有南宋爱国词人的悲愤,都是在曲中很难见到的新鲜内容。这不仅打破了“曲言隐”的定式,开拓了散曲文学的表现领域,而且提高了曲的境界,使曲文学中一向灰暗的士人形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与边塞军旅之曲一样表现出作者的雄心豪气的,是渴望飞黄腾达、建功立业的曲子,如【商调·山坡羊】中一组题为《青云得路》的小令:
笔下龙蛇放浪,自觉文章官样,七篇翰墨一扫群英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磨穿铁砚赢得琼林上,剔尽青灯博来姓字香。昂昂,乌纱射斗芒。堂堂,紫袍拖地长。
遁脱吕蒙悒怏,跳出颜回陋巷,宫墙万仞一跃三千丈。拜别孔孟堂,不愁陈蔡粮。衣冠气概换了寒儒像,头角峥嵘忽然宰相腔。奎光,风云护帝邦。文扬(一作“文场”),名题翰苑香。
十载寒窗独傍,一举成名天上,三场压倒五百英雄让。青云足下翔,虹霓万丈长。鳌头先据禹门桃花浪,金殿传胪蟾宫桂子香。眉扬,宫花插两傍。名扬,春雷震四方。
非是英雄豪放,还是斯文未丧,穷经皓首不负生平望。男儿能自强,天公自主张。一朝发奋位列公卿上,三策重瞳身登将相堂。经邦,绵绵万国昌。安邦,元元四海康。
此组小令所写金榜题名,出将入相,平步青云,名扬四海的理想,对于绝大多数的科举士子来说,虽然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官场梦幻,但却是无数读书人十年寒窗的根本动力,它不知牵动着多少才人的心魂!作者直写用世豪情,如此神完气旺、豪气干云,在一般文人士夫的笔下,的确又很难见到!如果再结合前述边塞之曲,以及《林石逸兴》中写“忠”“孝”“廉”“节”“仁”“义”“礼”“智”“信”等曲子看,可以说,散曲文学的基调在莲溪笔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叹世归隐,转向了忠君报国,这虽然有悖于散曲文学一贯的讽世精神,也有悖于晚明文学以情反理的时代思潮,不是散曲文学的主流,但却表现了一种激越的豪情,具有催人昂扬奋发的力量,相对于南派曲家艳情香风中一片婉丽柔媚的红牙丝竹,却不失为曲坛一阵激扬蹈厉的铁马金戈,是值得为之喝彩叫绝的!
因为仕途不顺,莲溪也不免产生愤世嫉俗之情,于是,大量的叹世讽世和隐逸闲适之曲,便出现于《林石逸兴》中,其中也有不少佳篇。其叹世讽世者,如: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鸮,失时鸾凤,大家挨胡撕弄。认不的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恸。(【中吕·朝天子】《不平》第二首)
不读书善文,有才学道村,镴枪锋青萍钝。时年依假不依真,鱼目把明珠混。驽马金鞍,绝尘盐困,寂寞杀谁来问?乱訇訇几群,死把定要津,说起来教人闷。(【中吕·朝天子】《不平》第三首)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起波千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双调·水仙子】《愤世》第一首)
忠肝义肝,颠倒生忧患。神奸巨奸,到处多称赞。并处贤愚,同炉冰炭,一脚把消息踏犯。地覆天翻,活活杀人卖死棺。谗佞妬心安,清白骨肉寒。青天无眼,做甚么英雄好汉?(【仙吕入双调·朝元歌】《世味》第一首)
与此等作品类似的还有【双调·沉醉东风】《四反》、【仙吕·桂枝香】《仕途》等等。这些曲子感叹社会混乱,贤愚颠倒,小人得势,奸臣当道,志士受阻,君子命穷,当是莲溪高才未展、仕途落寞、目睹现实而愤郁不平的切身感受,与元代曲家和明中叶康、王一派的叹世之曲,可谓同一感慨,虽时代有别,其愤世嫉俗之情,却并无二致。但是,前人感叹之余,往往情不自禁地产生对现实的绝望情绪,莲溪在发一番感慨之后,却常常充满着壮心不灭、来日可期的坚定信念:
也休说命穷,也休夸运通,谁认的真梁栋。老天生我定不空,有才必有用。司马题桥,非熊入梦,那其间识麟凤。困时节草蓬,亨时节鼎钟,满乾坤声名重。(【中吕·朝天子】《屈伸》第三首)
大丈夫困敛鹍鹏翼。鸡鹜由他戏,有日吐虹霓。一举成名惊天地。三策献重瞳,六尺惟忠义。(【仙吕入双调·步步娇】《屈必伸》第一首)
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李白式的自信与执著。其仕途不顺,却壮心不灭,这在散曲文学中,是一种少见的士人心态,它与明代文人入世心态的彻底修复和作者以儒家思想主导自己的人生是分不开的。
有时,莲溪还通过咏物寓意,以达到叹世和讽世目的,【双调·沉醉东风】《题钱》中的两首:
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不得你见官无理,不得你与吏为敌。不得你反是非,不得你违条例,不得你祸福时移。那怕胸中气正直,空着手先不见喜。这些曲子把世人钱迷心窍的拜金主义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社会丑行揭露无遗。又如【商调·黄莺儿】《斗鸡》:
芥羽一身轻,倚豪雄起斗争,樱冠披发不恤命。且立且行,且战且鸣,倾心抵死搏一胜。总然赢,锦衣零乱,金距血腥腥。作者写雄鸡争斗的残酷,惟妙惟肖,实以此暗讽世人的争名夺利和争强好胜,情趣盎然,寓意深刻。
在莲溪的讽世叹世之曲中,还有的感慨世风的浇薄,揭露人性的丑陋。如【仙吕·傍妆台】《世情》中的两曲:
笑时人,趋炎附势满乾坤。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箪瓢陋巷蛛结网,白马红缨春满门。鹍鹏志,鸡鹜群,等闲谁肯认苏秦?
谩量度,人情更比纸还薄。有患思知己,遭难念弥陀。雪中送炭亲朋少,锦上添花车马多。春富贵,赛江河,几曾杓水济人活?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慨叹,似乎亘古如斯!难道这浇薄的世风与丑陋的人性,会永远伴随着人类而竟无终止之一日么?
莲溪的隐逸闲适之曲,亦为数不少,其题为《逸乐》《恬退》《村乐》《归兴》《游乐》《忘机》《隐逸》《思归》《归乐》《甘贫》等归隐乐闲的曲子,在《林石逸兴》中俯拾即是,仅就这些曲子的表面看,仿佛酷似元人的乐隐乐闲之曲,如:
对青山虚亭闲立,听枝头黄莺(一作“鹦”)嘹(一作“喳”)呖,声声如劝争甚名和利。陈平六出奇,张良三进履。为韩为汉都做了一场戏,机浅机深只争的半着棋。知几,知几要见几。休提,大家葫芦提。(【商调·山坡羊】《草堂漫兴》第四首)
谁不待封侯拜将?谁不待为卿作相?谁不待腰金衣紫?谁不待麒麟像?谁不待姓字香?谁不待福寿昌?谁不待妻荣夫显?谁不待儿孙旺?天有安排浮生空自忙。心强,心强命不强。人长,人长天也长。(【商调·山坡羊】《安命》第一首)
辞别了繁华朝市,消磨了凌云豪志,掠起官人样子点检(一作“检点”)庄家事。逢人莫道诗,再休者也之。无多田地老手亲扶耜,广种桑麻山妻颇善丝。闲思,过一时少一时。还思,饮一卮是一厄。(【商调·山坡羊】《村乐》第二首)
一间茅舍一蓬牎,一盏清茶一柱香。一轮明月一天亮,一阵风一阵凉。一卷书一卷文章。一鼓腹一舒畅,一扬眉一举觞,一醉来一枕黄粱。(【双调·水仙子】《消遣》第一首)
这些曲子看起来识破红尘,超然物外,醉心闲适,但实际上不过是作者在仕途受阻和人生失意之际的自慰自解。莲溪本不是彻底放脱的人,也不是全然绝望的人,所以他既不像明中叶康、王诸人潜气内转的愤郁,也不像元代关汉卿、贯云石等人身心两放的真正闲适,而往往是在表面的放达中深含着功名心和是非感。他口头上说着“王侯第宅,元戎将台,说起咱不爱”“湖山一派眼睛宽,名利都割断”(【中吕·朝天子】《隐逸》),“但把眉头疏放,多少清闲佳况,存亡兴废不在吾心上”(【商调·山坡羊】《归隐》第三首),但骨子里恰恰是割不断名利,向往着王侯,关怀着天下。这种既痛恨现实,又牵挂着现实的矛盾痛苦,在不少曲子中都有真实的表现:
天际边头,龙潭虎口,历尽眉不皱。英雄豪气海天浮,肯落他人后?勇冠三军,才堪八斗,尽做了干生受。鸡肋难丢,朱门耻求,都只为名不就。(【中吕·朝天子】《名不就》第三首)
壮怀难破,叹英雄其实命薄。谁不待爱国忠君?谁不待暴虎冯河?弹铗有意向谁歌?投笔无门奈我何?(【仙吕入双调·玉抱肚】《壮怀》第一首)
正因为不“肯落他人后”,也正因为“壮怀难破”,十分执著于现实功名,所以他的乐隐乐闲之曲虽貌似元人,但精神实质和情感内蕴却已有天壤之别了。
莲溪还有许多题为《相思》《闺怨》《闺情》《妓怨》《妓叹》等等的言情之作,看来晚明艳情香风的泛滥,莲溪亦未能免俗,他这类作品虽不像一些市井文人的庸俗淫滥,但绝大多数作品感情浮泛,缺乏深情巧思,难脱散曲中言情之作离恨怨思的俗套,仿佛为写够千首小令凑数而已,艺术上难入上乘。倒是其中一组【双调·水仙子】《寄征衣》的四首曲子,写思妇对征人的牵挂,颇有真情实感。例如:
西风吹妾妾忧郎,为办冬(一作“寒”)衣检旧裳。千针万线奴心上。一针针泪两行,瘦和肥仔细端详。两肩窝削三寸,四停身照旧长,不伤情铁打心肠。(第四首)
写思妇对戍边夫君的刻骨思念和贴心关切,笔触细腻,生动传神。尤其“瘦和肥仔细端详。两肩窝削三寸,四停身照旧长”三句,由思妇想象戍边人之征战劳苦,身子骨一定瘦削不堪,所以征衣之肩宽要减削三寸,多少怜惜牵挂之情,仿佛于不经意中写出,真是神来之笔!
从艺术上看,莲溪的散曲,无论南北,大都洗尽铅华,显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本色质朴,在自然真率、圆融朗畅中又时见其锤炼精工的艺术匠心。其曲境的壮阔,情怀的豪放,气势的雄浑,就更非梁辰鱼、沈璟一派所能梦见。总而言之,无论从题材内容的新颖,还是格调上保持了曲体的神韵,莲溪之曲在晚明的曲坛都是独树一帜的。明清曲论家对莲溪之曲不置一词,主要的原因,或因为它仅仅是自我抒写的案头之曲,未能流播坊间,无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次,也因其特殊的将帅身份和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以及卓然高标的格调,都与晚明文人的风尚格格不入;明清人未能论及,近现代人又未能给予应有关注,是非常遗憾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赵玮、张强二位所著《(林石逸兴〉校注》的出版,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散曲史研究而言,可以让更多的人知晓莲溪其人其曲,也从而让更多的人知晓,在晚明的曲坛,除了有梁、沈南派曲家红牙丝竹的柔媚,也还有薛论道等北派曲家铁马金戈的雄浑,这对于明清散曲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散曲史的研究,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就曲学研究之学术承传而言,赵玮、张强《〈林石逸兴〉校注》的出版,昭示着新一代曲学研究者正在健康成长,而且其路数很正。当年,任二北、卢冀野等前辈学人治曲,莫不先用功于散曲文献,然后再进而论曲体、曲家、曲派、曲史,最后终成大家。赵玮君本科时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地)专业,其后又保送入该校中国文学与文化专业进一步深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如今在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供职,却能不辞辛劳,继续在曲学园地中辛勤耕耘;张强君乃扬州大学硕士,亦为一心向学的优秀青年。二位如能循前辈学人已经开辟的路径不断进取,则必将有新的认识,有新的成就。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像赵玮、张强二位一样执著于中华学术的年轻朋友加入曲学研究的行列,使我中华之曲学,有如江河行地,绵延不绝,流向未来,流向远方。
2010年8月22日于西华师范大学斜出斋
(作序者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元散曲通论》《明清散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