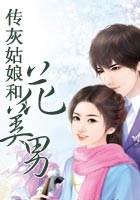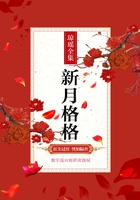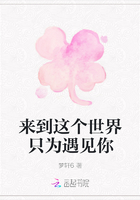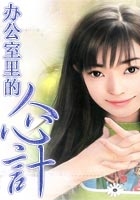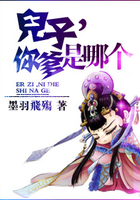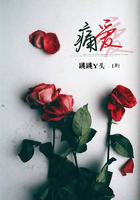历史上最沉痛的悲剧,莫过于人们喊叫“不可能”喊得太早……
——悉尼·胡克
谁也不知道那场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很长时间过去后,人们对那个久久不肯离去的黄昏记忆犹新。落日的辉煌像一簇祥云滞留在古老的梦境里。据说当大火像林子一样矗立起来时,村子却异常地宁静,连狗也不叫。有人看见一只巨大的红蝙蝠呼啸着从钢蓝色的火焰中穿过,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竹子烧裂时发出的那种声响。那红色的飞翔物似乎瞄着月亮飞去了。于是那夜的月亮鲜红鲜红……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它像民间的一句谚语流传到现作。我不是目击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仍然把它看作一场普通的天灾。对于其中一些近乎玄奇的因素,很自然,我把它们看作人对历史的一种润色。但是,有一点我感到很奇怪——我常常在梦中复制着这个传说,而且越来越清楚地复制。甚至某些细节,我事先并没有听别人说过,但与后来调查所证实的完全一样。我预感到我与那场火存在着某种联系。正是基于这种感觉,使我坚定了写这部书的信念。一切从头开始。
——作家手记
长水故道边上有个地方名字极古怪,叫罐子窑。何时有了这地方,县志无有记载。显然它是以制作陶器而得其名的,几乎户户都出操这门手艺的人。其实也并非只做罐子,碗、钵、油坛、夜壶都有。所以为何偏偏要称为罐子窑,至今无法查考。
制陶是极有趣味的活儿。从坡上挖取黏土,倒入池里化浆;滤浆沉淀的即为细泥。手艺人把泥搬回作坊里堆着,用时抠下一团,置于形同肉案的泥凳上揉,像揉面一样,不粘手为熟。再把熟泥团安放车上——车也是用泥拍打成的,模样、大小和倒扣过来的澡盆差不多,中心有轴。车面上还有一只由碎碗底嵌进去的“脐”。做活时,手艺人用搅车棍插入这脐,朝顺时针方向猛力搅动,车便飞快旋转起来。于是手艺人凭借这惯性,双手从泥团中拉拽出一件件的陶器。成型后,还要用油亮的枣木板周身“熨”一遍,再拿棉线锯其根部,就可以取下送到外面去晾。待八成干逐一上釉,之后便可码到窑里起火烧冶。行话称进窑的叫坯,出窑的叫货。
这种窑,不同于一般的砖瓦窑或炭窑。它是长形的,有七八丈长,卧龙似的倚坡匍匐着。高的一端是窑头,低的则为窑尾。窑膛内设有七级台阶,叫“七档”(坯就码在这些档上)。窑的两侧相对开着五十四只“眼”和十个小窑门,供塞柴、蹲窑用(烧时,窑门须用泥堵死)。然而这么一条窑,仅三个人伺候。在窑尾烧的叫烧小火的。烧左侧的叫烧大眼的,烧右侧的称作烧小眼。其实“眼”无所谓大小,之所以要这么称呼旨在突出大师傅的权威性。他主宰着窑的命运。窑是一档一档地由尾往头烧。一窑的货色如何,全仰仗大师傅的本事。大师傅并不是用手烧窑,而是用眼——看火。这看火的名堂是极为玄乎的,你无法说清楚。
县城与罐子窑距离三十六华里,但不通车。那年的秋天,我为民间的一个浪漫的传说所诱惑,第一次来到这地方。我记得我是下午动身的,骑着一辆很旧很脏的单车。其时秋已深了,太阳非常软,落叶纷飞。路很不好走。前一天的雨把路面泡得稀烂,再让太阳一晒,就全是疙疙瘩瘩的。我好像是骑在一匹没有备鞍的马上。不久我看到了一棵大枫树,它的寿命至少有一百年,依旧根深叶茂——那叶子完全红了,像凝固了的血一样有厚度有分量。接着我产生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幻觉:我仿佛看见了许多串刚被剁下来的手掌挂在一只青筋暴跳汗毛林立的大胳膊上。我下了车。这儿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大枫树下面摆着一个简陋的茶摊。茶具一律是陶的,又一律上着酱油似的釉子。我心里琢磨着,这些东西全是罐子窑出品的。罐子窑不远了。那天只有一个茶客,是位须髯飞霜的老者,看上去已逾古稀之外,却天生一副仙风道骨。他用一把精巧的小茶壶喝茶。在他的身边,斜靠着一根用斑竹做的钓竿。我移到树下的时候,那把壶在他手里仿佛一片羽毛,茶所剩无几。他的喉咙像车水一样响,以致两只正欲斗架的公鸡同时蹿开。这情景让我差一点儿笑出了声。我在老人对面的条凳上坐下来。自然我是打算同他搭讪的。可他的眼皮始终低垂着,好像我不过是树上飘落下来的一片叶子。这时候茶家也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便很有些尴尬,就拿出香烟,先敬他一支。他毫不推辞地接过烟,仍然是一语不发。他把过滤嘴拽掉:“烟也带屁股,又不是堂客!”
他的声音很低沉,甚至带有一点浑浊。说实话,我当时对他产生了亲近感。这是个有魅力的老人。而且从那一刻起,我就推断他年轻时,必然是非常讨女人喜欢的。
“老人家,去罐子窑怎么走?”我问道。
“跟我走。”他放下那把大茶壶,立起来。
那一次我很累。我随着他走。他走的是一条很奇怪的路,从一大片芦苇丛里穿过去,又拐到一片干涸的河床上。“没有水了。”他说。他一路上总是重复着这句话。
现在我知道,他是沿着长水的故道走的。我仔细对照了这个县过去的地图,他没有错。从前的长水流经这里形成了西去的态势,很有点山不转水转的味道。民国三十七年之前,罐子窑还是个规模可观的商埠。长水通江,且水面宽阔,可泊驳船。
黄昏时分,我进了罐子窑。老人并不多管我,自个儿走了,不知去哪里。我不想去惊动村里的干部,带着介绍信住进了一家私人客栈。当时里面的人正在议论城里刚上映的一部香港片子。我的到来似乎破坏了热烈的气氛,店家也许因此把住宿费抬高了一档。五块一夜。他说完便领我上了阁楼。这会儿暮色业已从四面围上来,村里陆续亮起了灯光,黄黄的。我很喜欢这个阁楼,它的结构和徽派建筑中大户人家的私宅有点相似,是木制穿枋的,隔墙也是木板。南北各有一扇小窗。床很大,还挂着看上去脏兮兮的夏布蚊帐。床的周围有一些残余的花板,彩也十分陈旧,但是图案依然清晰。有八仙过海,有梁祝楼台相会,有鲤鱼跳龙门。床的内侧镶有一面圆镜子,水银大都驳落了。床前置有一只七寸高的踏板,同样雕着花饰。踏板的两端是当地人所称的那种脚柜,一般是姑娘出阁时娘家陪嫁来的。
“等会儿田藕来替你铺床。”店家说。这个精明的中年人又迟疑地转过身,看看我:“同志,你是打老远来的吧?”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他好像很随便地看了一下,然后说:“省里下来的。这么年轻就在省里谋事,不简单不简单。乡政府该出面嘛!”
“我就住这,”我说,“这儿蛮好。”
“你住宿报销吧?伙食不用掏,还是五块一天。城里叫‘吃床腿’可是?我有国家正式的发票。”店家的情绪明显好了许多,他让我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姓陈,耳东陈,叫陈士林。我原来是大队会计,现在负责乡镇企业。”
我同他握了握手。这地方我很喜欢。
这以后我就躺下了。我告诉陈士林,晚饭开迟一些,我有点乏。下午随那老头乱逛了一场,不知绕了多少冤枉路。那实在是个古怪的老人。他的精力体力那样好,他完全还能生儿育女。我想等事情办得有点眉目了,最好还能去看看他,同他聊聊。他肯定住在这附近。这里的人也肯定知道他。我这次来得比较匆忙。那位大名鼎鼎的英雄郑海与我的家族没有任何的联系。我知道这个名字却是在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听到许多长辈谈起过郑海——他们说郑年轻有为,说郑智勇双全,如此等等。直到不久前,我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这位出现在传说中的英雄。那是在一次有关党史资料整理的座谈会上。有人介绍中的郑海似乎与我想象中的郑海距离很大: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纤弱的男子能够戎马疆场。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能提得起那只二十响的驳壳枪。当然,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却疑云重重。这就是郑海的死因。郑海死于渡江战役之后不久。档案上只说“牺牲”。然而谁也没有看见现场。因此他究竟是战死沙场还是惨遭暗杀,至今仍是悬案。郑海死后的第三天,县委才得到消息。那正值最热的季节,尸体无法保存,所以大家后来见到的不过是一堆黄土。几年后,有关领导对郑海的死表示了怀疑,于是掘墓开棺,验尸的结果表明:死者是男性,胸部确有一个枪眼,但这一枪是从背后射入的。接着,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死者是郑海吗?专程前来鉴定的法医希望有关部门能提供一张郑海的半身照片。然而这一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郑海。后来,我在一本内部交流性质的革命回忆录中,发现了一篇涉及郑海的文字:郑海,又名郑伯滔,书香门第,三代行医。那篇文章说郑海当时以行医作掩护,在罐子窑这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曾为渡江战役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但这位优秀的干部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了。”显然,文章的作者至今仍持怀疑态度。我于是写信给那位作者,可是很不巧,他(或她)也去世了。(那篇文章因审查拖了近两年才得以发表出来,作者的署名却没有加一个黑框。)
我不能不疑惑。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我决定先下罐子窑走马观花。
有人上楼来了。我欠起身,想把行李简单地安排一下。这时候门在我面前推开了,一个笑盈盈的姑娘抱着浆洗得平整的床单和被里走进来:“同志,你下去用饭吧,我来收拾。”
我想这大概就是田藕了。她长得很清秀,皮肤白皙,两只眼睛透明传神。她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那额前的刘海分明是她自己卷的。这个姑娘和这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似乎见识过一些人事,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豪迈。她养着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她管它叫“黑儿”。
我对她点点头,就下楼去了。
陈士林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这位前任的大队会计如今是乡办企业的负责人,不用说是位权势人物。他的每一句话,给我的感觉是,似乎都在暗示着他的能力。我对这种人本能上是排斥的,但我不能排斥热情。在杯来盏去之间,我在悄悄反省自己。我无权评判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在以后的几天里,陈士林给我的印象十分好。他是高中文化程度,没有考上大学。他曾在县里物资部门干过,一九六四年搞责任田时辞职回乡。“那时候头脑发热,”他这样检讨着,“不过现在也很好,钱没少赚。”他属于那种想得开、善于宽慰自己的男人。如果不用心细看,是很难发现他知足常乐的表情下面埋着惆怅的。我们差不多喝光了一瓶酒,都带了几分醉意。最后陈士林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说:
“城里人都他妈的没有卵子!”
时至今日,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仍然叫我不知所措。那晚我们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令人不悦或者非常愉快的事。陈士林长相斯文,有一种乡绅的风度。实际上他也算一个文化人。他的古文底子不薄,记忆力也相当强,还下得一手好象棋。在交谈中他常常顺手拈来一些典故、一些诗词名句,都是自然贴切的。他也许因为怀才不遇而憎恨城里人。尽管他手里有大把的票子,他还是有挥之不去的失落感。这是我的判断。
几天后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陈士林的身世,感到非常意外。陈士林可能是个私生子。他像一朵蒲公英似的飘落到这地方。人们仿佛有一天突然发现了这只孤雏,觉得挺好玩,可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处。那时候,他不到十岁的样子。谈话的人大概限于某种心理障碍,就此打住了。私生子都精明,那人说,你看如今的陈士林!
我非常迫切地想知道这些。虽然我是来调查一位英雄的真实死因的,但不排斥我对一个私生子的兴趣。可是我一直不便开口……
——作家手记
半夜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响惊醒。好像是一对巨大的翅膀扑扑的鼓动声,朦胧中我觉得蚊帐被这阵风撩开了。惨淡的月光从北窗射进来,不远的角落里传来蛐蛐单调的低鸣。夜仿佛一口很深很凉的枯井。我立刻拉灯,可是用力太猛,线断了。奇怪的是灯亮了耀眼的一瞬后竟又反弹了回去,吧嗒一响室内恢复了黑暗。在那光明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一个红东西蹿出了窗外。我失口叫了一声,声音居然那样的恐怖。我背上出了汗。
不一会儿,楼下有动静了。我想可能是陈士林醒了,就没有再喊他。我毕竟是个男人,事情弄成这样已经很丢脸了,倒真像应了几小时前陈士林甩出来的那句粗话。楼梯上脚步声响起来,而且有灯光从门缝里透进来。我便下床开门,上来的却是田藕,还有“黑儿”。
“同志,你吓住了吧?”她说着就笑了起来。
不用说我是很狼狈的。“灯坏了,”我边穿长裤边掩饰,“我不过是随便拉了一下。”
田藕把手中的蜡烛方灯放在桌子上:“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了看她,点上香烟。我疑惑不解,似乎刚才这楼上发生的一切她都知道了。不过,我倒想问问这姑娘。
“你怎么知道楼上的灯坏了?”
她又笑了笑。这回她笑得有点儿勉强,我从这种笑中意识到她是个正儿八经的女人而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这极短暂的时间里她突然成熟了。她的胸脯明显地鼓了起来。
“我想你是吓住了。”她平静地说,“以往来城里的客人,也这样。你肯定看见了什么东西。你不要怕。就算是鬼,也有善鬼好鬼。他不会害人。他不过是太冷清了想同外面来的人会一会。”
我没有笑,因为她说得太像煞有介事,说得太认真。我静静地吸着烟。“也许是幻觉吧,”我说,“幻觉往往很美。”
“不是幻觉!”
她说根本就不是幻觉。她说我有文化我读过许多书我不相信书上讲的都是对的。在南方,鬼魂像风一样地漫游。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田藕你别太激动。你坐下。我承认世界上许多事情是说不清的,所以我也不断然否认你的观点,况且我刚才确实见到了一个红色的东西飞出了窗外……
“红色的?那一定是我奶奶……”
她的神色越发凝重了,忧伤使她看起来端庄而富有教养——这感觉实在有点不可思议。我又想到她的父亲陈士林,他的愤怒也许是悲哀所致。我进一步设想,他的母亲一定死于城里人之手,比如说被城里的医生误诊或者因为没有及时付款而切断了氧气和血浆什么的。我很想同陈士林再聊聊。
“你父亲……”我说,“他现在睡了吗?”
她一愣,接着她笑了:“你弄错了。陈士林不是我爸爸。他是我叔叔,实际上也未必是我叔叔。我爸爸进城开会去了,昨天才走。这个客店是我们两家合伙开的。”
田藕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姑娘。她本人就是个美丽的矛盾。正如她所言,她爱读书但又怀疑书上的道理。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总是深刻的。那次谈话我有几点感到迷惑,至少是好奇。田藕在楼下怎么知道楼上发生了事?好像她预先布置了这一切来捉弄我这个城里人。“以往来城里的客人,也这样。”这说明类似的场面已经发生过,而且不止是一次两次。为什么这种怪事只限于“来自城里的客人”时发生?还有,她对我强调的“红色”似乎特别敏感。我记得她一下站了起来,肩上披着的衣服差点儿滑落。关于陈士林,她说:“实际上也未必是我叔叔。”说这话时她的眼神流露出一种轻蔑的开心。这与我后来听到的陈士林的“背景”正好是个印证。她大概潜台词是说,陈不是她的亲叔叔,她没有这个来历不明的叔叔。这只能是一种判断。也许这句话还包含着别的意思。
——作家手记
第二天一早,陈士林就领着乡长来了。乡长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叫秦贞,口气像苏北那一带的。她的装束很入时,也很大方,是一身毛料的银灰色西服套裙。早晨这季节凉意很浓,我注意到她把棉毛裤卷到了膝上,由于她比较富态,所以一坐下来就露出了棉毛裤的边缘。显然,这位乡长来时精心打扮了一下。在她的印象里,作家比记者还带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何况我是由县政府直接介绍下来“了解情况”的。
秦贞看了我的介绍信,连说了几声欢迎欢迎。她执意要我住到乡政府招待所去:“我们还是头回接待作家哩!”
我婉言谢绝了。我说这儿很好,我喜欢这个老房子。为了让这位颇有势派的女乡长宽心,我说这次下来主要是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情况。这儿非常有特色,我必须多到下面走走,回去给省报写一篇。
“那实在太感谢了!”秦贞说,“我这就去同几个厂打招呼,让他们准备准备。”
“不用不用,”我说,“我只需要随便看看。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找老陈好了。老陈,你看呢?”
“责无旁贷嘛!”陈士林笑着说,吸烟。
“那你算找对人了!”秦贞说,“陈士林可是这罐子窑一带的地保咧!在我们乡,罐子窑是老先进老典型了,你会有写的。比如说糙坯子……”
“操什么?”我没听清楚。
“糙坯子,就是田藕的爸,是绰号,大号叫陈士旺。别看名字土拉吧唧的,手可巧着哩!他做的货漂洋过海销到了外国。上到省长、专员,下到书记、县长,家里都有他的泡菜罐!这不,又去地区开表彰会了……”
“秦乡长你也来一支吧?”陈士林突然递给秦贞一支烟。秦贞怔了一下,手在半空悬着:“老陈你开什么玩笑!”
“女人抽烟也是时代特色嘛!”陈士林说。
“去去!你这家伙总没个正经相!”秦贞推了陈士林一把,敛住笑容,想把刚才岔开的话续下去,可一时又没找到头绪。于是她就大口地喝茶。(陈士林背过脸去咧了咧嘴,似乎很鄙夷乡长适才一番笨拙的表演。)
我也笑了。
这时候门外有人喊:“秦乡长电话——”
秦贞连忙放下茶杯,匆匆与我握手道别:“再会再会!多包涵多包涵!”
秦贞刚出门,陈士林就悠然自在地吐了一个烟圈:“傻×一个!”
我大吃一惊。我实在没料到陈士林居然如此地蔑视他的顶头上司。他难道就不怕一个陌生人私下塞他一拳吗?不过,对这种人我偏偏有些好感。或许陈士林早已揣测到这一点了。好一个陈士林!
我也点上香烟,微笑着——一种怂恿的微笑,我看着陈士林。
“别听那娘们儿狗屁滔滔!她懂个卵!”陈士林把一只腿从另一只膝上搬下来,“什么先进,什么典型,全他妈的吹灯日×——瞎捣!”
我哈哈大笑。
他凑过来狡黠地盯着我:“实际上你也不会去写这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你肯定不会写!”
“何以见得呢?”
他做了个手势。“我读过你的书,”他说,“所以我想你不会去写。如果我猜得不错,阁下此番是奔一个莫名其妙的幽灵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