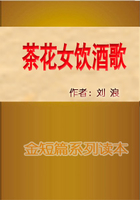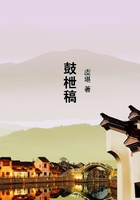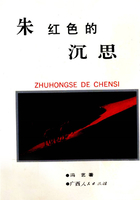那年我第一次下罐子窑的收获是十分可观的。在那不长的几天里我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这些事,其中有不少传说,甚至还有虚无缥缈的传奇故事以及不可思议的事实。所有这一切头绪纷乱的素材,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来的计划。郑海不再成为本书的灵魂,但他仍然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我的意思是想写一部庞杂的书。至于写什么,我不愿意多想——我历来不多想这个问题。至于怎么写,我大体有了一个构想。
第一,鉴于我要写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我有必要不停地调整视角。许多发生了的事限于我的视角位置,我难以说清楚。我只能权且充当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去编排左右这些陈旧的东西。但需要声明的是:我绝不凭空捏造。我可以借题发挥,可以推测,可以再现,当然更多的可能是表现。
第二,有些故事我是听来的。为了保留它的原生面貌,我尽可能采用口述实录。这或许会让人觉得语言风格的不统一。然而这种“不统一”又可能形成本书的叙述风格——请允许我行使自己的权利。
第三,在以后的篇章里将会出现不少“短路”,读者可能有所埋怨我的漫不经心我的草率。实际上这冤枉了我。在本人看来,创作的过程与欣赏的过程是齐头并进的。在不断出现的“短路”间,创作者的意旨传达给了欣赏者,于是他们判断。
作家只能写出小说的一半,另一半由读者写——用心来写。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好的小说是茶叶而不是现成的茶。你想喝就请你自个儿来泡。至于水的度数如何,责任由你负,我只管茶叶。因此你要参与,不能闲着。
我们就这样开始吧。
——作家手记
你无法想象那条河是多么地令人销魂。你写过不少河不少水这是事实,但你即使见到了那条河你也难以把它活生生地写出来。
我就是这河驮来的。那时候,我不过十岁的样子。这是后来我娘告诉我的。我不知道我到底生于何时何地。有人怀疑我是私生子。我也许就是个私生子吧!
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是个晦气的阴天,正度桃花汛。我从山上跑下来,到河边去摘桃花。我喜欢桃花。我就这样在林子里玩到了天黑,突然觉得饿了。越想越饿,饿得没有力气爬山了。我站在河边,向船上人讨吃的。可是没有人睬我。我哭了。这时候从上游划过来一条船,可是船上人没有往这边看。我就一下装着掉到水里,于是岸上就有人大喊大叫说孩子落水了快救命哪!这一喊,那船便急忙拢过来。其实那水不深,只齐我的颈,而且我也会一点儿水。我就做出要被淹死的样子,在水里直冒直冒的。等我第五次冒出水面时,我看见一根撑篙递到了眼前。“快捉住!”船上一个女人喊。我就一把捉住了……
那船非常普通,是长江中下游常见到的那种三板船,不过多加了一顶用竹席弯成的篷。船上有三个人。一个船佬,一个船娘,还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先生,大概是船客。我被他们手忙脚乱地拖上了船。船佬先把我放在一条板凳上,用胳膊替我压肚子里的水,压了半天没有压出一滴水却压出了一个屁。“你这小狗日的!”船佬照我的屁股拍了一掌,“急得老子一身汗!”船娘在边上哈哈笑,把眼角的泪水挥了去。那位先生也把眼镜拿下来拭了拭,然后说:“你是哪家的孩子,怎么这么晚了还在江边耍?”
我说,我就是这家的孩子了。我没有家。谁给我吃的我就给谁当儿子。我饿。
起先他们都不以为然。船佬说你小狗日的莫不是来刮老子油水的吧?他从怀里摸出一块洋钱。“拿着走路,免得老子以后破大财!”我把钱推开了。我说我不是偷儿。我真的没有家。我说着哭着给船佬磕头,船佬这才正了神。他好像一下子变得温柔,不停地舔着嘴唇,拿眼去看船娘——她正在给我煮吃的。船佬走过去同船娘嘀咕了一会儿,用的全是这一带最原始的方言,但我大致能听懂。那船娘说:“一个是养,两个也是养。就让他同糙坯子做个伴吧!”船佬点着头,招手让我进舱去吃东西。然后他把船拢到岸边泊住,下船去了。
那位言语很少的先生也进舱来,看着我吃饭。他又问我:“你果真没有家吗?”
我只顾吃饭。我不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先生。我那时觉得他在刁难我、盯我。
“你属什么的?”那先生问。
我摇摇头。
“你几岁了?”那先生又问。
“你看我几岁了?”我生气地说,“你这先生真是多事,又不要你养我!”
他笑了。“看不出这小东西倒蛮有出息!”他回头看看船娘,“莲子,这孩子我喜欢。就算是我的儿子吧,放在你们名下。”他似乎越笑越开心了。
“二少爷你可别瞎说。”莲子抿嘴一笑,“哪有大户人家做这种事的?老爷要是还在,会掌嘴的!”
“不不,莲子你错了。这种善事将来会有好的报应的。我相信这个真理。我在伦敦念书,就常去那些慈善机构玩。那里有许多像这样的孤儿,又都非常聪明伶俐。所以我时时想,那些为人父母的怎么心这样狠?”先生说完,用手来摸我的头。
“人心难测。”船娘说,把一盆脏水泼到江里。
这天吃过晚饭,二少爷就去了岸上,好像去办什么急事。天像要落雨的样子,他带了把黑伞。我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熟了。我在梦中听见外面已经下雨了,打得船篷脆响。
那只小船当晚泊在离轮船码头不远的一棵老杨树下。船头挂着一盏玻璃方灯。那黄黄的灯火在斜风细雨中一闪一烁,像一只疲乏惺忪的醉眼。船上的人都睡了。那孩子躺在女人怀里,梦里还不断地舔着嘴唇。他吃饱了,可一到梦里他就会饿。后来他说他有一次梦见自己一口气吃掉了一只磨盘大的乳房,但吐出来的却是一堆人的手指头。其中还有染着蔻丹的女人指甲……这个古老的梦折磨了他几十年,至今冷汗不消。
船佬也睡熟了。这一天他过得很快乐。他在江上捞到了一个儿子。他觉得这个儿子一点也不比自己家里的儿子差。他上岸给孩子买了一套新衣裳,还买了一只糖捏的红鲤鱼。他沽了一斤酒,用干荷叶托着两只卤猪耳一路哼着家乡的黄梅调回来了。其实他的酒量很小。他喝不过自己的女人。美丽的船娘天生海量,扬言能喝干这条江——如果江是酒的话!奇怪的是这回她只喝了一杯。这酒好苦哇!她想,这是谁酿的王八酒!她把酒壶推到一边。有一点她没有料到,二少爷把壶儿提到嘴边,想也不想地一饮而尽了。好酒!二少爷说:痛快!似乎在这一刻,船娘才见识了二少爷。几年不见,这个男人还是那样的英姿飒爽。在南京码头,她见到这个男人的那一瞬间,她仿佛失重了,身体像鸽子一样地飞舞起来。当她听见一声“莲子”后,她的一颗泪珠从眼角无声滚下,而这感觉又十分古怪,像一把刀慢慢从眼角往下割……
这个夜晚,只有二少爷没有睡。他也不在船上。二少爷是黄昏后上岸去的。他说他去会一位朋友,今夜不回来了。此刻这位年轻斯文的先生正打着一把乡间少见的黑洋伞走在江城的小街上。这街是多么古色古香。又回来了。离家五载不过弹指一挥间,似乎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二少爷在伞下点了一支烟,他仍然保留着用烟嘴吸烟的良好习惯。他有一根七寸的象牙烟嘴,这是父亲送他的宠物。他还在想那孩子的事。好像是有人在操纵这一切,偏偏在他回来的时候半路上闯来一个野孩子。那孩子嘴紧,只说自己是从山上下来的,哪座山?他脑子里闪过一座名山古刹,不禁哆嗦了一下。可那座山离长江很远,虽说是在同一个省的地界,毕竟一个毛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脚力……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无巧不有,谁能保证这个野孩子与他的归来没有干系呢?
二少爷的脚步加快了,他拐进了一条小巷。那个巷子的地势是一直向下倾斜的,二少爷的感觉像是在下山。在巷子尽头,他听见了第一声鸡鸣。
后半夜雨止了。风还是很大,船被浪推得摇摇晃晃。我让尿给憋醒了,睁眼一看,发现睡在我身边的船娘也不见了!船佬倒是睡得像死猪一样,扯着隆隆的呼噜。我觉得很奇怪,就爬到舱外来看。外面很黑,风声像饿狼一样低吼着,我好害怕。这样的夜总让人觉得要出什么险事似的。我哆哆嗦嗦地把尿撒到江里,回舱的时候我摸到了一把斧子,藏在被子里。不用说我睡不好了,扳着手指等鸡啼。可我又有一些好奇,船娘上哪了呢?会不会去找二少爷了?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偷鸡摸狗的勾当?你看我那时竟生这种念头了,那么小的东西!我当然不是乱猜。我有理由。船佬上岸沽酒那会儿,我看见二少爷悄悄捏了一把船娘的手,船娘的脸就唰地红了,她甩开了他的手,好像低声骂了一句:狗!接着她的眼又红了,湿润润的。船娘说得一点不错,男人都是他妈的狗!连和尚也是狗。我就看见过大白天和尚摸小尼姑的。以后我长大了,我也觉得自己像只狗。我不是讲醉话。
你大概想知道我的来路吧。这两天我看见你在村子里转了不少地方。我料到会有人对你说:陈士林是私生子!你不要不承认。我们中国人讲究面子,不敢当别人面揭短。我不怕。我不管这些。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几十年前睡了一觉,于是有了我。那两个人便是我的父母了。他们是谁?我不知道。我倒是感谢那双野鸳鸯,要不我就看不到这人世间的五颜六色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谜仍是揭不开。有时候我也可怜我那风一样来云一般去的双亲,他们竟没有勇气来看一看我这块骨肉。他们或许见过我,甚至就在我身边转悠着,但他们就是不敢站出来认我。不瞒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他们,当然他们可能早已不在这土面上了。或者,我替他们活着……
我现在再告诉你我爬上那只船以前的事。我说过我是从山上下来的。哪座山,我具体地弄不清了。好像不是座名山。在山上几年我没见到什么香火。庙倒是有一座,也不知道是供哪尊菩萨的,反正是个老家伙,胖乎乎的,耳垂落到了肩上。我不是在山上生的,据说是一个樵夫在山脚下拾到的。那时候我不满周岁。我跑下山的前一天夜里,樵夫喝醉了酒,又哭又笑闹了一整夜。就在这天夜里,一个男人进了我们的小屋。樵夫打算点灯,可那人把划着的火柴吹灭了。他们坐在门槛上,低声说着什么。我只听见那人说:“那小东西还好吗?”我猜指的就是我。樵夫说:“放心去吧,有我在,亏不了孩子。”那人叹了口气,半天不响。过了会,樵夫又说:“你可想看看?我来点灯。”那人说不。那人说不点灯照样也能看得清楚。接着他们摸索到我的床边,我吓得透不过气来。刚想叫,一只大手落到了我脸上,那手好凉哪!那只手先在我脸上轻轻地摸着摸着,再一直往下摸,摸到我的鸡子,我听见那人说:“还真硬朗!”不久,他说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就走了,樵夫送他出了门。送了好远一截子。我悄悄爬到窗口去看,那夜没有月亮,天上只有几粒星子,像贼一样躲躲闪闪。我好像看见那人的个头很高……
我从此知道了原来樵夫不是我的父亲。我是个没有人敢认敢领的野种!既然这样,我干吗还要守在这穷山上?那山太冷清了。我要下山来赶热闹。这不,一下山就热闹了。那天夜里后来再没有发生什么事了。可是二少爷和船娘一直没有回来。
灰色的长衫在小巷尽头消失了。不一会儿,临江的一个阁楼窗口亮起了灯。那灯光恍恍惚惚,把一个男人的身影映到墙上。他摸出镀银的香烟盒,从中拿出一支哈德门牌的烟卷安在象牙烟嘴上。他含着烟嘴没有点火,似乎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在想那个孩子。从见小东西第一眼起,他就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他仿佛面对一个筹划已久的阴谋。那孩子便是导火索,他将引爆一声巨响,引起一场大流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以致他这样文韬武略的人一时间乱了方寸。
屋檐下的水滴落在青石条上,声音单调又稍带一点恐怖。他慢慢站起来,踱了几步。他看着墙上自己无比高大的影子觉得很不舒服。他把灯挪到高一点的地方,让影子退到脚下。这样就宽松一些,平和一些。有人已盯了我好久,他想,只要我一露脸,他们就会将这支冷箭射过来。他们以为这种手段是克服我的最佳手段,让你见血往心里淌!天哪,那小东西,那硬朗的小东西!
他这才点上烟,意味深长地吸了一口。当然,这不一定是真的。只是一个假设。白天的事不过是一宗普通的船佬救孤,像一出折子戏。我这人太敏感了?可是莲子为何落泪呢?天下只有娘识得出自己的儿,女人的感觉,母亲的感觉,这可是连上帝也自愧不如的呀!她用酒漱了漱口。她不喝。她说酒苦——谁酿的王八酒!了不起的女人,让人永远不够的女人!莲子还是当年的莲子。莲子还是我的莲子。你骂我可你还是……你会来的。
楼下有了动静。他转过身,用右手抄起长衫向楼口走来。他先看见一顶竹斗笠,然后看见了莲子那张美丽的脸。
“莲……”他接过斗笠,用手来扶莲子,但她身子一闪,他的手落空了。他不尴尬,他知道女人可怕的不是同你赌气,而是平静如水。
他默默地替莲子泡上茶。
莲子还是不看他。她立在窗口,看着从眼前流过的江。那江是黑色的,风从上面魂一般地走动着。沉默在蔓延,窗外的雨似乎接近尾声了,然而这阁楼上的戏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刻男人就在女人的背后。他几次冲动地想扑上去把她搂到怀里。几年不见了,莲子依然那么勾人心魂荡人心魄。这个微雨之夜正是男欢女爱的良宵。莲子,你转过身来吧!果然,莲子就转过身了,接着平静地说:
二少爷,你的儿子回来了。
我的作家先生,请你放松一些。我不喜欢看人做出思考的样子。有一本书上说得好: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还是随便聊聊,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你最好放弃那种自作多情式的想入非非。我知道你不是个平庸的小说家,所以你要赶快打消你的一些平庸的念头。比如说,你可能会把二少爷同那个黑夜上山摸我的男人看作同一个人。也就是说,你认为我陈士林乃二少爷与莲子私通的结果。这就十分幼稚了。我告诉你,二少爷没有那个男人——就算是我的父亲吧,生得魁梧;他们的嗓音也不像。我还要告诉你,二少爷也不是你要追踪的那个郑海,他叫叶之秋。
你仔细看了这房子了吧?叶家是罐子窑的大户,我来的时候,已经比较败落了。其时叶家老爷刚过世,家由大少爷叶千帆掌握着。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少爷是不大问事的,把持叶家的是一只白嫩的手。那就是叶老爷的姨太唐月霜。叶家有六个作坊,一条窑——就是村南的那条,叫龙窑。还在县城设有一个钱庄。那船也是叶家的。叶老爷叶念慈六十七岁那年下扬州会诗友,在青楼结识了唐月霜,就有意纳妾。于是按唐的意思买了这条船。唐说,她命中与火相克,必须走水路。这唐月霜长得并不标致,但气质高雅,琴棋书画都能来一下子,是扬剧的票友;到这地方不久便会唱黄梅调了。这可是个非凡的女人!
不知你是不是已听说过了那么一件事。有一回唐月霜在皖水岸边散步,遇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叟,她让他看手相。老叟就提着她的手看了,说:“含章可贞。”走了几步,老叟又回头说:“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唐月霜听过有些不悦:这不是叫我做叶家老妈子吗?继之又感到惊慌:难道我身边有什么凶险?就赶快掉过身体去追那老叟,可是他早已消逝了。据说这以后,唐月霜就变得阴郁了,慢慢地,似乎脑子也有了病。不过我见到她时,她还是个活脱脱的城里富贵人家大小姐的模样,少奶奶的打扮,年纪在二十至三十之间。我至今忘不了她见到我那一刻的目光。她好像很激动,又似乎带有一点不可理喻的惶恐。“天哪,这孩子……”她说。我记得她是这样说的。这时候在我身后的二少爷笑着说:“太太,你好像认识这小子?”这显然是句笑谈,可唐月霜把手中的檀香扇一拢:“二少爷,你怎么不说这孩子是我生的?”她的口气虽然平和但十分尖刻。叶之秋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候,门外响起了马蹄声。接着我听见莲子说:“大少爷回来了。”
大少爷叶千帆是个身材高大,腰板笔直,不苟言笑的男人。他上身穿着白纺绸的褂子,下着黄色马裤,留着络腮胡子。当他提着猎枪和两只野兔走进庭院时,大家都不说话了。他首先看见了叶之秋,说:“回来了?路上好走吗?”说完把野兔扔给莲子:“烧出来,给二少爷洗尘。”叶之秋大概还沉浸在刚才的尴尬中,所以没说什么,只对兄长拱了拱手。
“这是谁家的孩子?”叶千帆注意到了我,看着叶之秋说:“你的?”
叶之秋这才笑了起来:“大哥,你可真会成人之美。我倒真希望有这么个儿子……”
突然屋里吧嗒一响,谁把一个罐子摔碎了。紧接着一只大黑猫逃也似的奔出来,听见唐月霜(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屋去了)说:“你这贱骨头!”
叶家兄弟相视了一下。叶千帆低声说:“父亲刚走,难免她……过几天,我们再谈她的事。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叶之秋就把路上的情况说了。叶千帆走过来摸摸我的头:“你倒像一条汉子,好,认我做老子吧!”他说着把我举起来。可是走过来的莲子说:“大少爷,这孩子还是让我领吧,你成天走东闯西的……”叶千帆把我放下来,叹了口气:“儿子离不开娘,谁叫我们叶家都是和尚呢?莲子,你把他领好。”于是他让我跪在莲子面前,让我喊娘。我没开口。等我正打算开口的时候,那个唐月霜又过来了,说:“大少爷,别忘了这屋子里还有一个女人……她也是可以当母亲的!”
事情弄麻烦了。表面上看是一场玩笑,可气氛却是笑里藏刀!真的,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小,但那个黄昏给我的印象太强烈了,太深刻了。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还时常在梦中复制这个场面……
陈士林的叙述始终是在平缓的语气中进行的。好像他所谈的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在说别的人,他不过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或者,是一个机智的故事转述人。有一点颇值得玩味,陈的叙述一旦进入在我们看来的那种“关键时刻”,就无影无踪了。他似乎在努力拆穿什么,但同时又企图把另一些什么埋得更深,这是我得到的感觉。那一次我随着他沿着长水的故道徜徉。我发现,这与我来时路上,在那株古枫树下遇见的老者后来经过的路线不完全一样。陈士林走得要直一些。他完全撇开了那片芦苇荡。我没有多想,但直觉告诉我,老人领我走的路线似乎要可信一些。当然这种细微的变化,地图上是无法反映出来的。“没有水了。”陈士林说,“我就知道它会干的。可它并没有死,它在地下流淌着。”这个中年人说这些话时是深沉的,他很怕你产生以为他浪漫的感觉,所以他后来又说:“我常常听到脚底下叮咚作响。”
暮色苍茫时分我们回来了。陈士林没有和我一道回客栈。在村口,我们分手了。他说晚上不能来陪我聊了,因为要出窑,他要去看看货色。“这几个月生意还不坏。”他说,“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烧窑,也蛮有趣的。”
这样,我就回了客栈。又来了两位新客,田藕正忙着,算盘拨得流水一样响。我在院子里吸烟,看见老槐树上突然筑起了一个空巢。我开始仔细观察这座著名的住宅。这是一个四方端正的院落,连房子在内,占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房子的年代虽然久远了,但保存完好,似乎连草也没丢一根。门前的那块上马石倒是消蚀得十分光洁。我仔细摸着这块石头,它冰凉的表面给人以历史感。我的视线从大门正中穿过去,我想依照陈士林的叙述把二少爷一行回来的场面重新排演一下。槐树无疑是这场戏的中心位置,所有的人都在树下表演。但是,有一个人以后始终就没有出场,这便是船佬。莲子的丈夫。这个人至今是面目不清的,陈士林的叙述中对他轻描淡写,或许是他在以后的故事里无关紧要,或许是陈士林故意将他遗忘冷落。总之,得有个交代。我希望这个问题在田藕,也就是船佬的孙女身上得到一些弥补。于是晚饭后,我找到了田藕。
我爷爷叫陈宗淼——三个水摞在一起的那个淼。这个名字只是在祠堂修谱的时候用。窑上人平常都叫他“六指”,他的左手有六个指头。
我没见过我爷爷。就是我爸爸,他大概记得也不清楚了。爷爷死的那年我爸也只有十岁的样子。我爷爷是个老实人,为人忠厚。当时叶家老爷让他跟班跑船很信得过他,对他也不薄。在一般人眼里,我爷爷倒像是叶念慈的干儿子似的。后来叶家大太太病死了,老爷让太太的贴身丫鬟莲子嫁给了我爷爷。这是民国三十一年的事。据说我奶奶并不愿意,结婚那天哭得很伤心。到了第二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我爸爸出生了。这以后我奶奶的精神面貌才好起来。她很能干,跟随爷爷给叶家跑船,走江闯湖,见了一些世面。
渡江胜利后的那一年,我爷爷死了。是在江上死的,说是喝醉了酒,失脚落水给浪冲走了。这一点我很奇怪,我爷爷的水性是极好的,纵使醉了,也不至于会亡命。不过以后谁也没见过我爷爷了。我奶奶在江上捞到了爷爷的斗笠。那时候,我奶奶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依然是很好看的,但没有再嫁。她的性子又温柔又倔强,居然一个人撑船跑江。据说,这之前她就在给共产党跑交通,她的上司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郑海。关于这一点,我小时候曾经问过我奶奶,我把她当作英雄,可是她总是摇摇头,说:“没有的事。”她甚至还说过,她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郑海!
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个黄昏,我放学回来,看见久病不起的奶奶突然坐在镜子前梳头。我正想过去,被陈士林一把拉住了。他对我轻微地摇摇头,样子很沉痛。我好像预感到家里要发生什么大事了,非常害怕。我们没有惊动奶奶,看着她一下一下地把头上的白发拔去。那头发离开头皮发出“啪啪”的响。这天我父母都去县城卖货了,家中就我们三个。奶奶梳好头,喊陈士林过去,让他帮她换衣裳。我说我来帮您换吧奶奶。她说:“藕儿你还小,到院子里念书去!”她的口齿和神志一样清楚。我就离开了。我在槐树下木呆呆地站了好久,听见陈士林在屋里哭了起来:“娘,你老人家放心去吧!”我连忙又冲到屋里,看见奶奶已经平躺在床上,咽气了……不过半小时的光景,奶奶就这样去了。我后来才听大人说,这叫回光返照。我奶奶显然意识到自己的路走完了,我相信她能意识到的。
奶奶没有实行棺木土葬。遵照她的遗嘱,三年后的清明这天,将她的骨灰撒到江里。奶奶说她要死得清清爽爽,不喜欢别人在她身上乱动。
那天晚上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停电了。田藕在我屋子里摆了一个铜的烛台。它的样子是一条盘绕的龙,看上去是很有年头的,擦得非常亮。田藕说,这烛台是她奶奶结婚时叶家老爷送的,原是一对,后来“凤台”弄丢了。那支蜡烛是红色的,也很粗大。屋里没有风,火焰笔直升起像一杆饱蘸着墨的羊毫。我喜欢这种类似伦勃朗的影调,它给人以幽雅,以宁静,又仿佛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我和田藕面对面地坐着。我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我不是指她的口才,也不是指她的长相。我想我指的大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气质吧。而且,我怀疑她的实际年龄。一个十七八岁的乡下姑娘是少不更事的。她不应该有着同身体一样成熟的思想。我一边听她的叙述,一边记录。她很能掌握节奏。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她有意放慢一拍或者重复一遍。后来她说:“你是不是打算写一本书?”
我笑了笑,也算是默认了。我发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姑娘是可爱的。
她思索着,然后说:“这恐怕不容易。因为许多事情无法弄清楚。”
我说,也许正因为这个“无法弄清楚”,我才有兴趣考虑写一本书。“不过,”我强调说,“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不想去解释什么,这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我想找到那么一种状态,一个作家只能做到这些。”我从口袋里拿出香烟,正想就着烛火点上,突然一阵风从背后袭来,蜡烛灭了。
黑暗中我听见田藕说:
“她来了。”
——作家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