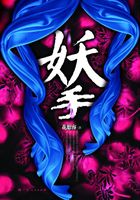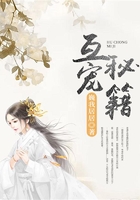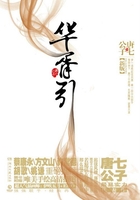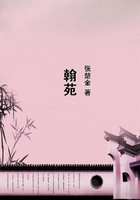沿着上面这条路一直往下就是长江了。你注意看,左边有一个巷口。那天晚上,齐叔叔就站在巷口,等候着少年和他的母亲。少年记得,齐叔叔披着一件烟灰色的棉大衣。
那年,少年高中毕业,在这年的冬季来临的时候,少年的生活里发生了不少大事。班上的男同学正踊跃报名参军,虽然兵种不够理想,但至少可以不下农村当知青了。少年被县征兵办公室安排去街头绘制大幅的宣传画。在石镇,少年的绘画才能受到普遍称赞。树立在镇中心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便是他几年前的杰作。人们谈论这个孩子时总要联想到他的父亲,说那是个多才多艺鹤立鸡群的男人,只可惜当了右派。实际上,少年最初对父亲的判断就来源于石镇居民的传说。少年自己的印象里没有父亲,或者只有一个轮廓,完全没有面目。这是一个假想的轮廓。有一次,他在阁楼上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他下了很大决心,在自己脸上做了富有想象力的安排。
但这不是父亲,倒应该是未来的他。石镇的人都说少年长得像他母亲。少年从不向母亲问及自己的父亲,母亲也一次没说。所以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处于失踪的状态,只有特殊的时刻,少年才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个父亲在世上。比如说,现在。你不要报名参军懂吗?母亲说,你有一个右派的父亲。母亲就说了这么一句,就奔医院去看护她自己的父亲去了。这个瘦弱白皙的女人是石镇出色的黄梅戏演员,但在舞台之外的地方,她的言语很少。1974年是母亲的本命年,36岁,命中注定会有一道深坎。果然在这年冬天,她刚入古稀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外祖父的死对少年的打击很大,从此这个家就只剩一个小男人了。那无疑是一个阴冷晦暗的冬天。少年捧着外祖父的遗像走在送殡队伍的前列。扶棺的是他的母亲。已患上白内障的外婆领着三个外孙女跟在棺材的末端。这支由石镇剧团组织的送殡队伍携带着唢呐、小号和萨克斯管,一路吹奏着《国际歌》,来悼念这位黄梅戏前辈艺人。但是不久,组织者便受到了撤职的处分,说他做得离谱了。那人不服,便质问:无产者为什么不能唱《国际歌》?被质问的人拍案而起:难道还要下半旗吗?这人最后又暗示,死去的那个唱戏的老头曾经有一个划为右派的女婿。
外祖父送上山的第三天,石镇的新兵连出发了。这天仍然没有阳光。少年在桥头看着一辆辆带篷的军用大卡车从眼前驶过,心里很难受。他的几个好同学都在车上。最要好的冯维明现在担任了新兵连的班长。他的军帽让少年用大搪瓷缸装开水熨得平平整整。现在他们都在向他挥动着军帽,在笑。雨后的道路上没有烟尘,少年目送着军车走完了大桥,似乎还能看清同学的面孔。后来他又沿河边走了很久,他发现河水淌得很慢。忽然间,一件东西被脚带出了沙土,那是一副样式很老的眼镜。于是他在河里将眼镜洗干净,戴上,眼前的景物模糊一片,大桥整个扭曲了。谁遗失了这副眼镜?直到1990年秋天,一个省城下来的水利勘测队,在这条河的边缘无意中刨出了一堆眼镜。大家对此惊愕不已,一时间都弄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第二年,一个小说家把它记进了自己的笔记:
1957年初,琴河拓宽河道,绝大多数劳工均为地区之右派分子。其时天寒地冻,劳工风餐露宿,营地皆扎河滩,虽垫有稻草棉絮,仍难御寒气。一宿之后,棉絮均被浸湿,如儿童尿床一般。至翌年全面跃进,劳工每日工作量骤增为十八小时。年底,新河开通,而劳工伤病死亡者众,一般以芦席裹尸,就地掩埋……
二百多年前的一个雾霭迷蒙的早晨,一叶扁舟由青云山而下,在石镇码头做短暂停靠后,便顺流通江直达水市,再北上进京。那时谁也无法料到,这条仍不起眼的小船日后竟会载起半部中国戏曲史。发生于公元1790年的“徽班进京”正是从琴河开始的。后来大闹天桥,轰动紫禁城的程长庚、杨月楼,都是石镇这一带人,史称“无石不成班”。北上的徽腔很快成为京昆的基础,而散落在江河湖泊上的,逐渐演变成了采茶调、花鼓调和黄梅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黄钟大吕的京剧相对,小桥流水的黄梅戏一夜间独领了风骚。但很少有人知道,黄梅调的正宗韵律源于石镇。
1953年春天,一个在水市大学学习外语的青年,本应该去朝鲜战场当志愿军的翻译,却因战争走向尾声未能成行。这个青年人后来竟丢弃了自己的专业,来到石镇从事黄梅调的搜集整理工作。那时的水市还是省政府所在地,青年的家也住在城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手工业主,主持着水市一座著名的酱坊。不过在那时,酱坊已开始衰败,坐落在江边的那座小楼刚刚被没收充公,成为征纳航运税赋的公事房。青年是到石镇文化馆上班的,负责剧目的整理。文化馆位于石镇的西端,一座木制穿枋带回廊的二层楼。青年住在楼上,他的后窗下是一片莲花塘。青年住下的头一个晚上,就听见了莲花塘对面的孙家祠堂里单调的锣鼓声。他可能因为旅途劳累而感到厌倦,但是不久他便为纯正的黄梅调寝不安席。这个晚上后来青年就去了孙家祠堂,在忽明忽暗的汽灯下,他看清了一个小姑娘正在有板有眼地唱着《小辞店》。在侧幕边上,立着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人,他的表情与这出伤感的戏文似乎毫不相干,显得平淡而枯燥。中年男人要做的,便是把端在手里的泥陶壶递给唱戏的小姑娘,让她下场后喝上几口。台下的青年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由此断定他们的关系是父女。他很想上台去同他们聊聊,同时对一把胡琴的伴奏提出意见。这胡琴太干巴了,他自语道,还不如清唱呢!这时候,有人递给了他一碗茶。青年侧过身,想掏出零钱付给这位在戏园子卖茶水的妇人。可是妇人没有接,妇人说:你这位先生是大码头来的吧?青年有些局促,说:我是从水市来的。妇人又问:严先生近日可还在城里登台?青年说还在,并说:我和严先生是朋友。青年说的这位“严先生”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严凤英。青年这才知道,卖茶水的妇人和台上的父女是一家人,和严凤英曾在一个班子里搭过伴,中年男子即是著名的青衣由之先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在青年心中涌动着,他觉得自己和这一家人的缘分似乎已是前定。五年后,他被他们所接受,成了他们的女婿。
据说由之先生当初对这门亲是显得冷漠的。在婚期临近的前几天,他脾气很坏,几乎每天要摔烂一只碗。但他深知独生女儿的个性,覆水难收已是事实。他也奈何不过自己的堂客,在妇人看来,男人的不满是嫌女婿比女儿大了十一岁。她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她也小由之先生十一岁。然而在1957年元旦后的第三天,当女儿被众人送上石镇文化馆的那座木楼时,由之先生竟独自关在家里号啕大哭了。这让他堂客十分生气,她骂道:你这辈子在台上还没哭够吗?养女总是要给人的,你就不为姑娘讨个彩头?由之先生用衣袖拭尽泪痕,然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张签文。堂客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一道凶签。
签文出自青云山脚下的一个瞎子。半年后,这个家庭发生的事证实了瞎子的预言。
我还在梦中徜徉,父亲推门进来弄醒了我,接着告诉我一件事:剧团昨夜烧了。我问是怎么烧的。父亲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有人说是遭到了雷击,电线起火。我匆匆穿上衣服,随便洗了把脸,骑上自行车往剧团去了。那一片天空仍是灰暗的,像一块旧补丁,余烟尚在升腾着。一路上,我碰见的差不多都是剧团的职工,他们的脸上滞留着悲痛与沮丧。我问:烧得怎样了?他们说:你看看就知道了。远远看去,剧场的轮廓还算完整,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可是当我迈进烧焦的门槛时,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
我说不出话。我的胸口完全堵住了,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焚烧发出的爆裂声。这把天火烧掉了我的摇篮。我是在戏园子长大的。五岁那年,我触摸写有母亲姓名的广告灯箱被电流击过,我的右手小指至今还是略显弯曲。我帮助过这个剧团画过许许多多的布景。我父亲创作的剧目,最初是在这个舞台上立起来的。而我的母亲在这个舞台上站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它已成了废墟和焦土!我从剧场走到后台,从逆光中看见了母亲瘦削的身影。
母亲面对的位置应该是一面镜子。那是她的穿衣镜。镜子的左边是一个衣柜,放着她常用的行头。右边还有一个脚箱,那是外祖父生前使用的。在没有戏的时候,老人总是坐在这箱子上吸着黄烟。这面镜子记录了我母亲的一生。她九岁随外祖父走江湖,十二岁顶梁演《金钗记》,石镇剧团一组建,她便成了当家花旦。母亲的戏路很宽,除花旦青衣,她的小旦和刀马旦也十分出色。中年之后,她开始演老旦或者反串小生。1987年,我陪同一位戏曲史学家来石镇考察,便在这个剧场看了母亲主演的《孟丽君》。那一年,母亲五十岁。她在舞台上的扮相依然光彩照人。这个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女人凭着过人的天赋与毅力,在这个舞台上挺立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
我走近母亲,轻轻扶着她。早已泪痕满面的她此刻无力说出更多的感叹,她只是喃喃地说:太惨了。
母亲只说了这一句。
——1997年10月15日
那个阴冷的下午,少年离开河边后又去了老街的一家日杂商店。他想选购几件农具。县“五七”办公室已通知,凡下乡插队的学生必须于年底前去所在地报到。日杂商店的人对少年很热情,因为他们常请这个孩子来这里写楹联。那都是些根据客户需要现写现卖的货色。日杂商店的负责人是一个精瘦的老头,据说从前和少年的父亲私交甚好。在他看来,少年的字比他老子的更有风骨,面目也清秀得多。所以在少年选购完农具之后,他又额外送给了孩子一条毛巾和两块肥皂。1988年,当石镇人争相议论一部关于天灾人祸的长篇小说时,这个刚从日杂商店退下来的老头却在添油加醋地介绍着该书的作者,同时也炫耀着自己的先见之明。
少年又一次走过了那条小巷。一个小女孩正在巷口踢毽子,毽子踢飞了,落到矮屋的瓦楞上。少年放下手里的东西,替小女孩取下了毽子。小女孩用水市的话谢了他,少年有些意外,来自水市的声音让他在这一瞬间想起了小丹。
小丹一家是武斗平息后的第二年迁回水市的。算起来已过去五年了。搬走的那天,少年随外祖父回了老家,那是个离石镇十五华里的乡下,叫罐子窑。外祖父走江湖之前,是一名手艺不俗的陶工,能从一团熟泥中拉拽出各式各样的罐子和壶。那天,少年正在简陋的作坊里用心制作着花盆,他想把这件东西带回来送给小丹。半个月后,他回到石镇时,母亲把一封信交给了他。信是小丹来的。信上只说水市的中学很乱,那些同学把她看作是乡下人,她很苦恼。少年感到有些失望,他觉得这封信写得差劲,也写得干巴,而且字也相当难看。但这毕竟是他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于是他撕下了它的邮票,夹在笔记本里。第二天,他在带回的那只小花盆里栽下了一朵花。这花后来养了两年,少年却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过,他还是很喜欢那张邮票,时常会拿出来看看它。
很多年后,在一次特殊的场合,他突然意识到这张小图画带来的某种暗示,感到了刻骨的忧伤与悲痛。
老街是狭窄而陈旧的。
你如果对建筑感兴趣,便会发现这条不长的街上还存有一些徽派的老房子。从街面上看,这些房子显得单薄而简陋,但它们鳞次栉比,纵深广阔,一个门洞的后面有十几户人家。少年的家就在这条街上,在最里面,后门正对着一条小河。那天下午,少年就是从后门进家的。他看见三个妹妹都在小院里吃着包装很漂亮的水果糖,尚未从丧期步出的外婆在生煤炉,用蒲扇驱散呛人的柴烟。少年便放下手里的农具,想接过扇子。外婆说:你于阿姨来了,在里屋。
于阿姨就是小丹的妈妈,是一名小学教员。她是从水市来的,她已经有五年没有回过石镇了。少年兴冲冲地推开里屋的门,看见于阿姨正和母亲坐在床沿上交谈,但是他有些惊讶,因为母亲的双眼已经红得厉害,而且于阿姨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喜悦,她只叹了声:孩子们都大了。少年这时似乎感觉到,一件意外的事已经发生了,但他不能确定是什么事。
母亲站起来,平静地说:收拾一下你的画,我们去水市。
少年问:就走吗?
于阿姨说:我是来接你们母子的。你爸爸回来了。
谁也不会注意那个黄昏从石镇驶出的一辆装粮食的大卡车。少年的母亲和于阿姨坐在驾驶室里,少年陷在粮食堆中。车向东行,他看见渐渐退后的西边天空突然整个地红了,像在焚烧。这一天里阳光失踪了,却意外地给天空涂抹上了最后的晚霞。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这个黄昏的晚霞沉淀在少年的记忆深处,变得古怪而奇异。
很多的时候,这怪异的图案被理解成沙漠,没有飘逸却日益凝重,它的形状又时刻为风沙改变。在这片沙漠上看不见旅人的足迹,你听到的只是那个人粗重压迫的喘息之声。
父亲的突然出现,在少年心中引起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那是激动伴随着恐慌、欣喜搅拌着悲凉、亲近又不想亲近。1957年秋天这个孩子从母腹爬出时,他的父亲已经成为右派。到了1962年,父亲平反无望只能遣返原籍。他曾经想把儿子带走,但遭到了拒绝。你自身难保难道还要把儿子弄死?年轻的母亲这么争辩着。于是,男人和石镇梨园这一家人分手了。他们对各自的组织打了报告,却不被允许对簿公堂。他们最后由组织出面代办了离婚。男人就此离开了石镇,第二年有消息传来,说这个男人在兴修水库时淹死了。女人感到困惑,她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男人的水性实在太好了。1954年石镇遭受前所未见的大水,正是这个文化馆的干部挨家挨户给剧团的人送来粮食的,他怎么会淹死呢?但是女人也不敢去验证这个事实。1962年女人不过二十五岁,却已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了。过去的一切像是一出苦戏的彩排,这个女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懂戏文的意思,大幕便落下了。她不经意中扮演了一个无人替代的角色。1965年,女人有了第二次婚姻。但这一次还是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在跌跌撞撞几年之后,她自己走上了法庭,放弃了一切财产而要回了三个女儿。这一天,正是她三十五岁的生日。
天渐渐黑了。少年站起来已经可以看见水市的灯火。风很大,但少年浑身发燥。他在这前后两小时里思绪纷乱,他感觉到父亲的轮廓在慢慢清晰起来,但面目则更加迷离。他现在离父亲越来越近了,近到伸手可触,可他还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这感觉在折磨着他,他甚至感到了疲倦。他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现在这一切突然改变了,他显得不知所措。他难以想象一会儿将有一个男人被指认为自己的父亲,而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汽车便在此时驶进了市区。与石镇相比,水市显得要繁华得多。街道宽阔,楼房高大,灯火灿烂。卡车没有直接进市区,而是在西门的一个路口停下。他们都下车了,然后就沿这条路往南走,走上坡面,远远地就看见齐叔在那个巷口等候着,但少年没有见到齐叔的女儿,他的小学同学于小丹。
当年那座老房子业已拆除,你见到的仍是一个复制品。1974年12月的那个夜晚,水市的街面十分冷清,走动的行人都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那一夜风大却不显出声音。无声地逼迫着你。齐叔领着他们走进这座房子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他们都是父母的朋友,在等候着这离散一家三口的团聚。少年已有些紧张,他在判断着谁将是自己的父亲。而这时候听见齐叔说,父亲刚刚去邮局给石镇剧团挂电话了。少年的心有所平缓,他坐在靠门的那张椅子上,屋里的大人正打开他的画夹,在传看着他的画。不断有人推门进来,都还是父母的朋友。他们得知某某人从巢湖边上回来了,必须见上一面。毕竟,他们也是分别了十几年。这些人都是黄梅戏的有功之臣,从最初的《打猪草》《闹花灯》,到鼎盛时期的《天仙配》《女驸马》,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付出。这些是很长时间之后少年才知道的,那时,他已是一名小说家了。那个晚上,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母亲当年的演出和眼前少年的画作。少年显得有些羞涩,这时,他看见坐在对面的母亲表情发生了变化,她的视线落在了少年的身后。少年便下意识地转过身,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穿着一件略显臃肿的棉袄的男人正从门槛迈入。接着他听见母亲轻声地说:
这是你父亲。
1974年12月我在水市与父亲见面,其时我刚满十七岁。如果走在街上,他不会认为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离开我们母子已有十二年。一个轮回。实际上,这个父亲对于我是刚刚诞生——童年的记忆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依稀可辨的是1962年秋天,我随母亲去水市,和一个男人一起吃西瓜,但我无法记起他的形象。所以当他被母亲指认后,我显得很尴尬。面前这个男人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伯伯,与石镇人所说的那种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简直格格不入。我难以把诸如大学、外语、志愿军翻译、戏剧家这些字眼与这个陶俑似的形象联系起来。但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喊了他,接着一种亲情的气息非常自然地在我们之间传递。很多年后,我写过一篇小说,其中一个细节是讲一个产妇怀疑护士把自己的孩子抱错了。那个护士质问她:你凭什么说抱错了?产妇说:我一嗅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儿子。她的话被视为不可思议,但却是对的。原来这个母亲的孩子生下后就死了,丈夫怕她受刺激,才借别人的儿子一用。我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一嗅就知道”的亲情。
那天晚上,齐叔后来烧了一锅胡辣汤,姜味也浓,大家都喝。大人们谈论着这些年发生变化的一些人事,比如说谁得肝癌死了,谁摘了帽子,谁已调动改行了。我才知道,这些人往日也是不多走动的,尽管这个城市很小。然而正是这些人促成了一个家庭的团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自己帮自己。夜已深,人们陆续离去。我已经知道小丹陪她的一个表姐去城西住了,今晚不会回来。我似乎有些失落,很想见到她的一张照片,可是没有找到。这时候,父亲才开始看我的画夹,那都是些素描和速写,也有两张色彩写生,其中一张画的就是我从罐子窑带回的那只花盆,但栽的是一棵向日葵。父亲看过,没说什么,又让我写几个字。我便用钢笔写了“鲁迅先生”。他还是没说什么,接过钢笔也写下了“鲁迅先生”。这让我诧异,因为他的字写得实在太好了。
我们在水市住了五日,父亲又返回了巢湖农村。不久,我收到了由齐叔转来的父亲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让我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是想留下几本书,还是留下几张画?”他这样写道。我回信十分肯定,我说我此生必须做一个出色的画家。那时我还不知道达利和毕加索,心中的偶像是列宾、苏里科夫,甚至包括列维坦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
现在我得说说小丹了。第二天,大人们要去另一个地方聚会,于阿姨便安排小丹回来替我做饭。那时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床头挂着一件钢丝背心,那是齐叔用的。他回到水市以后被安排到码头当搬运工,腰椎受了重伤。齐叔和父亲是同一批在石镇划上右派的,为此父亲一直感到内疚,因为当年是父亲把他拖到了石镇,他们想在黄梅戏的渊源之地大干一番伟业,结果却双双成了右派。那个上午我有些懒散,靠在床头看一本过期的什么杂志。昨夜的事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只是觉得突然了一点,忧伤却是在一年之后。这时,门外有了声响,小丹回来了。第一眼见到小丹我还不敢相信,她已完全像个成人,而且长漂亮了。这或许得助于她的一面口罩,这个平常的东西使她眉眼呈现出极大的诱惑,也使她的头发显得更加亮泽。我喜欢女孩子戴口罩一定源于此刻。这种喜欢同欣赏雪后的景象心理上是完全一致的。雪使一切删繁就简,于是在你的视觉上便产生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奇特效果。我记得小丹取下口罩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饿吗?她的口音已完全变成了水市腔,软软的,但听起来很舒服。我说我不饿。她又问我的鞋码多大。我说三十九码。她就有些吃惊,说你只比我爸爸小一码呀。小丹说她妈妈让她今天为我买一双球鞋。我想这应该是送给我去农村的礼物吧,就问小丹:你下乡吗?小丹说,怎么不下呢?我的户口都寄过了。我们就这样随便说着话,我起床时,她就把我放在椅子上的毛衣什么的一件件递给我,然后又去厨房替我准备洗脸水。她问:你带牙刷了吗?我说忘了。她说那就用我的吧。我看见她把牙膏挤到一把小牙刷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仍是那么鲜活生动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我在感到寂寞的时候,总是凭借着这样的记忆来慰藉自己。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已经长久地占有着对方。但小丹不是我的初恋。
——1997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