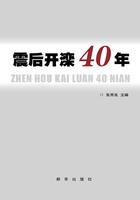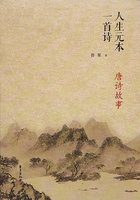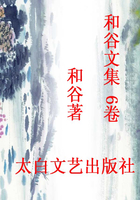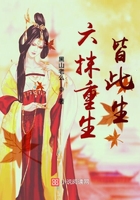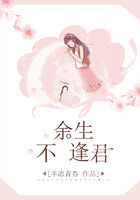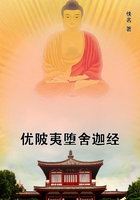采写/月山行
一九九八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到它的人,是政府、银行等国有单位中的白领阶层,那时网络始兴论坛,上面聚集着国内首批高质量网民,大家在论坛上发帖,也有人开始写小说。
路金波、宁财神、痞子蔡,他们是第一批在互联网上写小说的人,后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们得到大量的关注。那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女作家也开始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贴在论坛上的作品,很快因其风格独特而引人注目。大家这样评价她的小说:像开得如火如荼的彼岸花,神秘、绮丽、妖艳,充满令人着迷又窒息的宿命感。只短短两年,她的首本小说集便出版问世,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网络上风头最健的新生代作家。
安妮宝贝的成名,将她置于风口浪尖。网络上对她的评价形成两极化,传统出版界将她划入边缘的异类,但即便这样,也无法阻止成千上万的读者甘愿成为她忠实的粉丝。
她从不公开露面,即便成名,也一贯保持低调,离群索居。这样,更加突显她的神秘。面对公众的猜疑,甚至谩骂,她统统不关心。依旧写作、出书,保持一年一本作品的速度。她看上去似乎与这个世界并无多大关系,但看她的作品,又道尽了人世间的巧合与苦难。早期作品中对情爱的沉沦,以及散文中对物的独特审美与迷恋,让她无形之中成为一个固有的形象,深深烙刻在读者心里。球鞋、白裙、茂盛的黑色长发。一张桀骜不驯的脸,没有太多表情,素面朝天,面对任何事情都非常决绝。
直到她写出《莲花》,这座丰碑的诞生,彻底扭转了她早年网络作家的形象。此后,她成为千万读者的精神导师。有人说阅读她的作品仿佛读经,让人心安。也有人把她后期的作品比作药物,当他们阅读的时候,内心深处的疮口慢慢愈合。
她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和她的生活不无关系。
安妮宝贝的家乡在宁波象山县,那里靠海,有山,夏天的时候有台风。季节分明的南方小镇,塑造了她性格分明的特质。年幼时在乡下的外公外婆家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乡村生活给予她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力。她在作品中写,那时外公带着她去山中掏兰草,夏天刮起台风,大街上吹断的梧桐树散发辛辣芳香。村头的一座古桥被拆毁,只剩下一根桥墩。夜晚睡在乡下外婆家青瓦房里,古旧木床散发独特木头香气。外婆喜欢做糯软的团子给她吃。这些童年的生活经历,赋予她丰沛的情感。成年后写作,这些成为她的宝藏。
如今改名庆山,她的生活更为沉静,如一潭静谧无波而深不可测的水。她研究宗教,认定宗教是一门深厚的哲学,有取之不尽的真理。她时常去藏区寺庙小住,做义工,帮助寺庙里的师傅烧茶煮粥。也去尼泊尔和印度,她喜欢这些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度。她的写作与生活成为一体,探寻世外高人,为此专门著书,取名《得未曾有》。这也是她写作十余年,改名后的第一本书。也如近作《月童度河》上的一句话:如春光寻觅到山峦,如明月感应到净湖。这是她如今的生活内核。
对话
“想以后逐渐离开城市。”
月山行:在家通常怎样度过自己的一天?
庆山:如果写作,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工作。工作结束了,会出门旅行一段时间。在家会看书学习、养育花草、打扫整理,每天早上五公里步行,孩子放学了陪她一段时间。每周也会与朋友们喝茶、读经。
月山行:最近去了哪里旅行?最喜欢的是哪里?旅途中有何收获?
庆山:这两年我较多是在藏区。经常去的是日本。最近想去看一个圣湖。
月山行:早年看《清醒纪》时记得谈到吃素,现在还保持吃素吗?
庆山:没有特意吃素,但平时饮食我很清淡、自然。也一直在实践过午不食,有些反复,有时会中断。希望最终会彻底。
月山行:今年花园里种了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植物?
庆山:我现在对花草没有格外用心,种的都是别人送的种子、幼苗,把它们养大。只要是活的,我就养着。
月山行:提到不断收到各种大学的讲座邀请,以后会去参加这类公开活动吗?
庆山:目前还没有。以后会组织一些合适的形式,互相交流。我不反感活动本身,是觉得有时一些活动过于形式化和杂乱,人们围在一起拍照、发微信,忽略了实质性沟通,这样没有意义。
月山行:也提到做完俗世的事情后,想和爱的人搬到山中,过种菜种花养猫的日子。之前有朋友说在大理遇见你,目前有确切的目的地吗?
庆山:目前还没有。但我的确想以后逐渐离开城市。
“我的心是很安静的。”
月山行:在写作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庆山:写作没有什么大问题。写作是由自己的心带动起来的。所以,一直保持学习、探索,是个比较漫长的高强度的事情。
月山行:你提到时常去咖啡店或者在安静的乡村租一个农舍写作。在安静与吵闹的环境下写出的文字会不会有所不同?更喜欢在哪种环境中写作?
庆山:我都可以的。写作需要少一些俗事打扰。但这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毕竟还需要照顾孩子。
月山行:写作时长久闭门不出,突然进入人群中,会不会有不适感?庆山:我的心是很安静的。长时间一个人独处,也没有什么波动。但进入人群,与人互动,也并不隔膜,也没有年少时候的封闭和敌意。这是自己的修习所带来的结果。
“外界是由我们的心投射而成的。”
月山行:在《净化》中你说,到这样的年龄,不可能再是以往那个写着早期的动荡情爱和黑暗青春的人。如今的写作主题是什么?
庆山:其实我所有的书都是在写人与心灵的关系。先探索自己的心,再去理解他人的心。外界喧嚣沸腾,但很多信息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人如果连自己的心都无法感知、控制,外界又有何用?外界是由我们的心投射而成的。我希望用书写,与读者一起去探索这个心与自我领悟的关系。
月山行:现今社会中,很多年轻人受到拖延症的困扰,究其原因无非是自身难以摆脱的恶习和懒惰造成。在你一贯的写作中,一直强调惜时惜物,在生活中要做到优雅,而优雅的首要是珍惜生活,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刻。扫除时,全身心投入扫除,做饭时也同样。这让我想到,你是否会时常给自己制定日程表,每日按部就班依照表格上的计划度过一天?你会给那些道理都知道,却始终难以做出改变的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摆脱拖延症?
庆山:我有大概时间表,就是写作、旅行、放空、学习、再写作。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表,因为每天生活都会发生变化。有三种懈怠,对应该做的事情拖延懒怠,沉迷低劣俗事,自轻沮丧。这些是可以对照的。如果人们有拖延症,一般可以在三条里找到对应。
月山行:你说自己是个物尽其用的人,手机摔到无法发出铃声和震动依旧在用,直到有人赠送新手机。然而如今社会,地铁上,甚至走在大路上,很多人都在低头看手机。不少年轻人迷恋物质,为了融入圈子,手机要最新款,衣服要赶上潮流,为追逐表面上的美丽去整容已成为家常便饭,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庆山:年轻人可能需要经历一段物质时期,来弥补自己内心的匮乏。但这个时期不能过长,否则,一生都会被它奴役。
月山行:现今随着网络的普及,欧美流行文化的侵入,比如在许多美剧、欧美流行音乐中,都大量充斥着对金钱、性、毒品的痴迷。脏话连篇的歌词,大量裸露的滥交和血腥的镜头,一些年轻人在这样的熏染中成长,导致认知和观念上的趋同。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庆山:社会的文化污染很严重。隔绝有一定必要,人要有意识地切断自己没有任何觉知的沉溺。我很多年没有看报纸、杂志、电视,也不看新闻。同时,始终保持学习一些有体系有深度的内容。这最终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被世俗潮水拖着走,会一无所获,又心中躁动。每个个体都注重完善自己,社会也会逐渐趋向完善。
月山行:年少时觉得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是什么?现在觉得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又是什么?
庆山:年少时,觉得被人爱很重要,对如何去生活没有想很多,觉得怎样都可以。现在觉得,如何去爱他人很重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很重要。不重要的是周遭的评价和判断。
“感情需要智慧与慈悲。大部分感情,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慈悲。”
月山行:早年的作品中所描绘的相爱和现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相爱有何区别?
庆山:早年作品中描绘的相爱有比较多自身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此经常也是有损伤的。现在的作品中的相爱,是有觉知的,其最终目的是趋向自我完整与和解,也能够给予彼此自由。
月山行:如你作品中写到的那些爱情,年少时我们往往会在情爱的泥沼中一再跌倒,即便明白各种道理,分得清好坏,但都是无用。要经历的还是奋不顾身扑进去。年长后,是否对情爱会更放得下,更理性,更果决?如你在《月童度河》中所说,让自己陷入泥沼、倒退和麻烦中的感情关系,要果决地斩断。年长后,是否能够更轻易地做到这种果决?
庆山:感情需要智慧与慈悲。大部分感情,没有智慧,也没有慈悲。只有各种欲望、纠缠、损伤、苦痛。
月山行:有些人在感情关系中受到伤害后会选择独身,你如何看待独身主义者?
庆山:比起独活,有伴侣是更好的。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对境,可以检验自己的成长、完善。但前提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善待伴侣,否则就是在为自己制造烦恼。
“如果放下期待、恐惧,自由会带给我们深深的满足。”
月山行:在《月童度河》中你一直强调,自己和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人,彼此都需要学习和进步。你会放下她,长时间地远行或工作。印象深刻的一处是,某一次你要去寺庙小住两个礼拜,她着急地问:妈妈,你这次要去几年?当时觉得她这样留恋和依赖你,那样深爱你。再后来,你送她去寺庙过假期,她变得不再对你痴缠,只是远远对你挥手离开。这种转变的过程,在你心中会不会有失落感?长久的分离,会不会担忧她?会不会怕她觉得你不够爱她,对你有怨怼?
庆山:这书中的两个细节,不存在转变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她小的时候,不怎么痴缠我,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需要工作、外出。她长大一些之后,我会特意留出时间陪伴她,与她一起做一些事情,相处、聊天。我希望在她心里,我是一个有意思的可以做朋友的成年人,一个可以信任、欣赏的对象。所以,现在我们反而是更亲密的,她的心智也成熟了,可以理解许多事物。她知道我足够爱她,没有什么怨怼。我从不试图控制她、要求她。一直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待。
月山行:以后会让女儿写作吗?
庆山:让她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事情。
月山行:看到和女儿的温情日常,时常感动难言。印象深刻的一处,是你给她买了礼物放在客厅小桌子上,等她回家看到那些美好的小物件,内心欢喜雀跃。想,如果恋人之间有这样的关系,该是多好,那么赤诚天真而单纯的爱。你觉得这两种爱之间有何共通或可借鉴之处?
庆山:可以共通的。常人对伴侣较容易有挑剔、期望,对孩子也较容易有控制、期望。这是很容易伤害到对方的。如果放下期待、恐惧,自由会带给我们深深的满足。
“希望《莲花》《春宴》这样后期比较厚重的作品,能够在日后拍出作品。”
月山行:很早前就得知作品要被拍成电影,除了已经上映和确定会上映的《七月与安生》和《八月未央》外,还有新的作品开拍吗?
庆山:如果有可能,还是比较希望《莲花》《春宴》这样后期比较厚重的作品,能够在日后拍出作品。这些作品有可能更符合原著,因为原著本身够强壮。早期作品都是写得太快速的小故事,也没有太多深思熟虑。
月山行:自己要参与到电影改编的工作中吗?
庆山:目前没有任何参与。如果要参与,我需要清楚认知这个团队和他们的想法。
“只想沉溺和躲避在集体、人群之中,是软弱、懒怠,也是不独立的表现。”
月山行:微博刚兴起时,博客一一倒闭,看到一些写作者表示对微博这种快餐式信息感到排斥和不适应。你在《月童度河》中多次提及微信、微博,并且向大家分享自己朋友圈的面貌。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如今的微信,你似乎一直都在热烈参与和娴熟运用。你如何看待拒绝网络甚至拒绝使用手机的写作者?网络对你的写作和生活有何影响?
庆山:时代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在可以坐飞机的时候,你也不可能骑马去旅行了。文字如果可以给他人带来一些帮助,那么让它们更直接更广泛地传递,是更好的。至少需要的人可以更方便地得到这些文字,这对他们有益。仅仅是为了流动文字的工具,没有其他什么意义。我除此不在网络上有什么活动,不看乱七八糟的新闻、视频,也不参加任何组织、社团。网络就是收发邮件、传递文字所用。虽然文字未必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受用的,也会有人排斥或反对,但总是会对一些人发生作用。这是随缘的。
月山行:你多次提到修行,你是一个修行者吗?修行中具体要做一些什么?
庆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修行者。这是训练自己的心,让它趋向平衡和向上扩展的方式。修行具体怎么做,这是有次第的。最初级的可以从阅读、听闻、思考开始,再逐渐进入实践。
月山行:怎样理解“月童度河”这个书名?
庆山:这是代表一种行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代表流动、开阔、天真、有光照耀的一种状态。
月山行:觉得在《月童度河》里,你始终在围绕一个核心,关于人如何穿越妄想和欲念,寻找到自我所在实现超离,这点和《春宴》的核心相似。其中首发于《城市画报》的《长亭》也收录其中,阅读这个短篇小说会联想到《春宴》,它应该是《春宴》的前身吗?《月童度河》所围绕的主题与《春宴》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庆山:《春宴》要穿越的是情爱、情欲的妄念。《月童度河》的范围更广阔一些,议题也更广泛。《长亭》是为杂志的情人节特刊写的邀约文章,所以,写的是男女之情,与《春宴》一样,也是由经过情爱历练来引发个人思考。但它不是《春宴》的前身。《月》更像是《春宴》的前身。
月山行:你的阅读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看对你的访谈和作品,提到多次的是古代笔记和典籍,在近作《月童度河》中,有更为宽阔的描写。诸如川端康成、辛波斯卡、阿多尼斯、吉根、麦克尤恩、安妮·普鲁等以往从未提到过的作家。现在的阅读面是否有所改变?
庆山:这些是我为写作部分保留的阅读。现在的阅读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文。这包括大乘、小乘、金刚乘、禅宗、瑜伽、印度教、苏菲派等许多分类。我也读过《圣经》和《古兰经》。它们属于人类智慧的核心内容,远超过文学、艺术这些人为的创造形式。
月山行:阅读佛经的时候能够完全理解经文的要义吗?会不会请教师父?
庆山:有些即刻理解,有些可以逐渐理解,现在也有很多历代高人阐释经文的著作,自己探索、理解的过程更有意思。阅读经文不需要请教师父。
月山行:在《月童度河》中发现你的语言相较以往作品有更为口语化的倾向。《得未曾有》出版时,有人评论说语调变得很“三联”,更有人说你已经抛弃了“安妮宝贝”时期的语言模式。这本书中,近期写作的散文和较早写就的《月》也有语调上的不同。又比如,以前很少看到使用“呢”字或者问号,现在渐渐使用起来了。很多人一直喜欢你的书面语言,包括我,觉得极赋魅力。会坚持使用书面语吗?
庆山:《月童度河》的文字清简、质朴,较随意和口语化,有点类似笔记体。通常长篇小说的书写会显得更为精巧、优雅,也就是更优美一些。但散文中的观点直白朴素地说,较节省彼此思量。小说要搭建一个新世界,它是另一个体系。不是风格变化,是随体裁而描述有所转化。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写作水平在提升,语言也会逐渐明净克制,而不是更加复杂繁冗。这是跟心力相关的。
月山行:《月童度河》中提到,朋友看到你现在写作的变化。朋友说的变化,具体是指什么?
庆山:变化很明显,我在《月童度河》里也写了,自己已经翻越过的主题,不会一再回去写了。他人再喜欢也不可能为他们而写。最好大家一起往前走。
月山行:在《黑枝豆》中你再次写到日本,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在日本有很多单个出现的男女,无论街上还是地铁中都能见到。在国内,却是相反的现象,人们喜欢成群结队,害怕单独行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庆山:孤独是对人有益的。适当的孤独,可以让我们的心独立、沉淀、思考、有进步。只想沉溺和躲避在集体、人群之中,是软弱、懒怠,也是不独立的表现。
“这个时代科技发达,它对我们的包裹和捆绑过于紧密了。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出离。”
月山行:有一年夏初时我梦见和你一起在藏区旅行,途中发现一朵盛开的花,不断地开出红、紫、蓝、青的花瓣。你说这是佛陀的花。在《净化》中,你也提到有读者写信给你,说梦见你。你如何看待在梦中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相见?
庆山:我在书中也写过,有时见面与否并不重要,因为能量通过无形有形等很多方式在传递,尤其是心的能量。
月山行:在《月》中你写:“她的母亲,生性独立,所以也从未真正地溺爱过她。有时对她的需求或情绪故意不见,向前一步,等待她自己振作。也从不在别人面前炫耀她,认为她美或聪明。母亲一丝丝自豪或沾沾自喜都没有。”包括在后面你写自己年幼时因为爱的匮乏,导致自己的阴阳面失衡,一直觉得被爱得不够。在早年的作品中,诸如《清醒纪》里也写到和家中关系不亲密。《月》中描写的母亲,是自己母亲吗?
庆山:《月》写的不是我的母亲。我写母亲,散文里有真实记录。父母有他们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但当你成年之后,有了理解力,会发现他们已经付出了能力局限范围中能够付出的一切。他们是竭尽全力的。这需要成年之后才能体会。小时候我有叛逆心理,但现在对父母是完全接受和理解的。
月山行:年幼时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总觉得母亲不爱我,年长后才明白,是她们表达爱的方式不被那时候年幼的我所接受。但成年后,因为童年长久的内心爱的匮乏,导致有无法抹除和消解的缺失感。如今你自己有了女儿,在关于她的那部分文章中,时常被你们之间的互动所打动,那种没有任何条件的无私的爱,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宝贵。你这样爱女儿,是否因为年幼时的遭遇,希望能够在女儿身上得到弥补?
庆山:由自己的经验出发,比较能够明白一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我尽量避免以无知伤害她的心灵,而是给她空间、自由,又有指引,让她自己慢慢往前走。
月山行:最近在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推荐几部好书和电影吧。
庆山:最近在读金刚乘的专业书。没有看什么电影,已经没有时间像以前一样看碟了。电影院如果有好电影,偶尔会去看,主要是去电影院这个形式有仪式感。如果要推荐书,还是读读《枕草子》《西游记》《聊斋志异》这样的古代的书吧。阅读与这个时代拉开一些距离比较好。这个时代科技发达,它对我们的包裹和捆绑过于紧密了。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出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