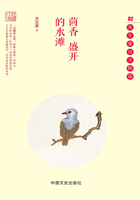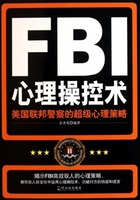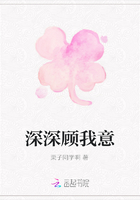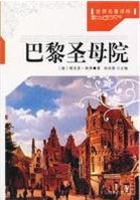THE FUGITIVE MONK
兰州是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座大城市,位于西安西北大约300英里的地方。兰州在黄河边,黄河这个名字是对泥褐色河水诗意而理想化的描述。这是一道有棕色泥浆颜色的裂缝,并不好看。兰州跟西安差不多,不过更原始,许多设施尚处于建设之中。十七年前我来过这里,在我记忆中,相比西安,兰州是一个更小的城市,也更像中亚的城市,有巨大的穆斯林市场,里面有许多摆着切开的羊肉的肉摊,以及一麻袋一麻袋的干果和调料。现在的兰州更大、更嘈杂,中国特色更浓。主要街道上,高层建筑一栋接着一栋,玻璃立面的大楼拔地而起,外表线条流畅,是一种包豪斯风格。忠梅去拜访当地的舞蹈团,王勇则跟我去市场吃午饭。我们像伊斯兰帕夏[16]一样支使小吃摊老板,让他们从不同的摊位上把食物送到我们桌上。小吃摊有非常美味的清蒸鸡、辣味烤羊肉串,还有加了芥菜的汤面,芥菜被称为“中国西兰花”,但比西兰花好吃多了。
“你吃过羊头吗?”王勇问。
“羊头?你是说羊的头?”
“对。”
“嗯,我在法国吃过小牛头,挺恶心的,真的。”
“我们到哈密以后可以吃羊头。”王勇说。
王勇成了我的导游。
离开小吃摊后,我们看到一群戴着小白帽、穿着长袍的男人,决定跟随他们。他们显然是穆斯林,正要去做祷告,而我们也想知道哪儿有清真寺。他们走进一条笔直狭窄的小路,入口处挂着“文明示范街”的横幅。这条路的一边是一排用高墙围着的房子,另一边是铁路,偶尔有货运列车经过,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还路过王彦邦医生的“国际著名针灸诊所”,招牌是在一层楼高的柱子上撑着的水泥砖瓦砌的方形盒子。我们能听到前方传来“真主伟大”的祷告声,诊所外面,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被一个推三轮车的男人骂哭了,好像是那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三轮车。
那些身着长袍的男人转过弯消失了,我们快走几步想要赶上他们。转过街角,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中国式的清真寺宣礼塔,塔顶上是新月和星星,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混合。我们跟随那群男人进入清真寺的院子,他们先到旁边的屋子斋沐,然后开始祈祷。外面,一个破衣烂衫的小个子男人正盯着我们看,痴痴地笑着。其他大部分人都只是瞟我们一眼,没有任何表示,既没有敌意也看不出友好,他们已经习惯了偶尔出现的带着相机的游客。
离开清真寺,我们打了辆车去往兰州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五泉山。出租车背后贴着的宣传标语倡导每个人都做“文明天使”。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是一辆夏利,一种车型很小的模仿菲亚特而制造的中国汽车,前后座位之间有安全网隔开。司机是一个女人,戴着光滑的黑色锻面手套,穿着紫色套头衫,袖子上装饰着黑色的大扣子,还有弹力裤,齐肩长发染成浅棕色。她拉上我们,在一条中央有隔离带的路上走错了方向,我很高兴打到这辆车,也很高兴看到她在中国的街道上开车,所向披靡。
我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碰到女出租车司机。“女司机很多,”她说,“我们从工厂下岗,反正也挣不着钱,就开出租。”
寺庙入口处有个牌子,写着“从今天开始,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破坏公共财产……”《兰州晚报》头版有一篇报道标题是“甘肃二百城镇文明宣传战开端良好”。报道说:“昨天,省委宣传部召开特别会议,宣布我省建设精神文明的宣传战正式拉开序幕。”这项活动“在精神文明委员会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将会展开文明竞赛,精神文明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将受到嘉奖,获奖名单将刊登在报纸杂志中”。
这场关于文明的竞赛很有意思。我以前住在中国的时候,最常见的标语是“争取更大的胜利”。从那以后,政府从充满革命激情的组织变成一个要求人民讲文明、讲卫生、不随地吐痰的机构(这只是我从坊间日常中得出的结论,并非基于普遍的观察)。现在还有精神文明宣传办,以及可敬的官员。
那天是“五一”,国家法定假日,而五泉山又位于城市商业区的一座小山上,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上山去寺庙的路和下山回城里的路都是如此。在大殿里,一个僧人站在巨大的佛像前,时不时敲一下大铁钵,让游客快点儿离开放着铁钵的供桌。我给这位僧人取了个名字——“愁眉苦脸佛”。在寺庙办公室前坐着一群老人,其中一个鼻子上坑坑洼洼,穿着蓝色哔叽西装,蓝衬衣敞着领口,露出里面的蓝色针织背心。
“我要重走玄奘去印度的路。”我跟这个老人说。
“是吗?”蓝衣老人回答。
“你了解玄奘吗?”
“了解。”
“他来过这个庙吗?”
这个人肯定地说没来过,因为玄奘没来过兰州。到达兰州必须渡过黄河,而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我对他的解释表示怀疑。
“那时没有桥。”他坚持说,他周围的人也表示同意。
“有船。”我说。
“不,也没有船,”他说,“玄奘从陕西出发,去了天水、陇西、临洮和永靖。”
稍后,我看了地图,发现那条路线玄奘可以在兰州西边大约50英里的地方渡黄河。这条路线是有可能的,但即便这样也需要过黄河。慧立还提到玄奘到兰州停留了一个晚上,所以我也在这儿停留一个晚上。我问那个穿蓝衣服的人是怎么知道玄奘的路线的。
“书里看的。”他回答。
“哪本书?”我问。
“不记得了。”他说。
离开寺庙的时候,我看到一位老僧人。在我看来,他眼睛周围的皱纹代表了智慧。
“你知道高僧玄奘吗?”
“不知道。”僧人急急忙忙往前走着回答。
我不知道这位是“无知佛”呢,还是“不想找麻烦佛”。
晚上八点半,我们坐上了去往嘉峪关的火车,火车终点在兰州西北400英里以外。
经过又一个无法安睡的夜晚,早上我们已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上。这是一片灰白天空下广袤的戈壁平原。窗外的输电线和祁连山脉通向南方,北部的黑山山脉有更多电线杆,不过那些山脉都只是薄雾笼罩的地平线上模糊不清的影子。列车驶出嘉峪关二十分钟以后,地表变成一种砾石颜色的细沙。南面低低的丘陵看起来像是一些曾经宏伟的景观被侵蚀后留下的残迹。我们的北边,远处地平线上耸立着工厂的烟囱里时不时喷出灰色的浓烟。旅游手册上说嘉峪关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而在历史上,这里是通往西域的门户,现在这里生产水泥。这时一阵凉气涌入软卧间,在我们准备下车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小小的雨滴打在地面干燥的尘土上。
王勇在嘉峪关有个朋友,那个朋友有车,在车站接我们。我们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面馆可以吃午饭。
“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他说,我们飞速驶离沙石路,往城里开去。
我们吃了有牛肉和红油辣子的汤面,那家小饭馆条件一般,老板却是一个过度热情、热衷于为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民互相了解彼此贡献出自己力量的典型。
忠梅问他有没有餐巾纸。
“Yes!”他用英语回答,以表现自己对这种语言的掌握。
“哦,你说英文!”我讨好地说。
“几年前我看到两个美国人在街上找东西,他们说邮局什么的,”他开始用中文跟我们讲起来,“但是我的英文太差了,不懂‘邮局’是什么意思,结果我把他们带到了政府,而不是邮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邮局’是什么意思,但太晚了。他们已经生气了。后来我给他们指了邮局的方向,但他们不相信,不愿意去。我感觉很不好,于是决定把英语学好,然后我就学了。”
“嗯,那是美国人不对,”我继续恭维他,“他们应该学中文。”
“我想请你们尝些有中国特色的菜。”老板说。他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个小个子姑娘穿着满是污渍的灰色衣服。店里墙上挂着大大的图片,其中一幅是西式早餐——大杯的橙汁,盘子里是培根和鸡蛋,另一幅是画着水果、奶酪和红酒的静物画。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约好七点半再回来。这时那个男人注意到我随身带着的小笔记本放在桌上,打开着,就在面碗的旁边。
“你是个间谍还是什么?”他问,盯着我,气氛有点儿变化。饭馆老板脸色黝黑,穿着紫色夹克,抽一种很粗的中国雪茄。他目光平平地看过来,充满敌意。
“如果你觉得我是个间谍,”我说,“什么秘密都别跟我说。”
“好吧,如果你是间谍,我就是警察。”他说。他靠在墙上,往天花板吐了口烟:“不过你来嘉峪关到底要干什么?”
“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忠梅说,而我则在默默地为自己用中文乱说话和拿出那个可疑的小本子而自责。
“那好,如果是对中国历史有兴趣,怎么都行,但如果是那种想要给中国找麻烦的美国人,我们可有办法对付他。”
“没人想找麻烦。”王勇说,努力想要缓和气氛。
“美国佬就是在找麻烦。”饭馆老板大声说,那个穿着脏衣服的小姑娘吓了一跳。我继续吃着面条,想要赶快吃完离开。“他们觉得能控制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威胁我们。美国佬不想让中国变强。不过他们办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就是纸老虎。”他笑起来,非常疯狂。他还在看我,而我还在吃面,辣得鼻涕都流出来了,额头和腋窝里都是汗。
中国有个说法叫“爱国分子”,显然我们就面对着这样一个人,理智上我知道他没有任何力量制造麻烦,但还是忍不住想象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我不觉得自己真的有被捕的可能,但这个之前还是朋友的饭馆老板,去公安局报告有可疑的、会讲中文的外国人在嘉峪关转来转去,还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警察听到他的报告,也许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谁知道呢。
离开饭馆后,我们去参观明长城遗址。它的起点在嘉峪关几英里之外,耸立在黑山上几百米的地方。花两美元就可以爬上去。我非常享受那儿的风景,西边和南边是沙漠,绵延不绝,穿插着几道起伏的山脉,那些山脉一路延伸,最终与喜马拉雅山脉相连。
伊丽莎白·韦兰·巴伯在《乌鲁木齐的木乃伊》中认为,从新疆东部发现的木乃伊来看,那里的居住者是白种人。他们讲的是现在已经消失的吐火罗语,他们的纺织品跟遥远西方的凯尔特人有相似的地方。[17]巴伯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凯尔特人,主要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以及这些新疆的居民(你在乌鲁木齐博物馆可以见到他们的木乃伊)属于同一个部族,也许都来自北部里海的某个地方。在某个时期,他们分裂成两支,一支去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另一支开启了这条“大事之路”(The Road of Great Events):他们慢慢向中亚大草原进发,越过高山来到塔里木盆地,在绿洲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文明。这些幽灵般露齿而笑的尸体在沙漠中被风干,从新疆西南部的和田到最东边,沿途的考古发现中都找到过干尸。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欣赏眼前的风景。但同时我也告诉自己,对先前在饭馆里的遭遇大惊小怪是多么可笑。的确可笑,但紧接着我就看到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在长城上向我们走来,他们肯定是冲着我来的。他们穿着带有红色领章的草绿色制服,慢慢地走着。我站在城墙的最高处,看着他们费力地向前走,在陡峭的地方俯着身子。他们跟着我们一路到了最高处,当我们下去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下来。他们笑着给彼此拍照片,背景是一片空旷的深色沙漠,仅此而已。
“嘉峪关”的意思是“通往嘉峪的关隘”,是我们停留的小城的名字,也是附近古代边防堡垒的名字,还是连接中国和西域诸国的出入口。慧立没有提到嘉峪关,他提到了玉门关,在嘉峪关西南100英里以外,现在的安西县附近。事实上,数百年间,这个关口的实际位置变了好几次。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地方作为边界,并以不同名字命名,名字相同的关口有好几处。如果在别的地方修起了新的关口,老的就留在那里变成废墟。现在的玉门关在敦煌的西南,而玄奘时代的玉门关则已经埋在人工湖泊之下。但是,不管在哪儿,它们都保留着类似的基本建筑样式,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矗立在山脉之间的沙漠平原上。军队驻扎于关口和附近的烽火台上,看守着这个地区,以保证没有商队和其他旅行者越过边界。
关于这些关口,有着大量诗歌和传说,记载着它们作为中国内地和外部野蛮地区疆界的故事。诗歌中描写了被流放者的悲伤,因为关口之外就是敌国所在,失败的将军、遭贬黜的大臣被流放至此,也许是几年,也许是一生。当然,还有传说中的美人坐在轿子里被送到这里和亲,好让这里的沙漠暴君不要侵犯中国的领土。我们在嘉峪关那天,一辆自行车——颇有超现实主义的风味——停在关口,它的后面是绵延无尽的紫色、棕色相间的沙漠,那些将军、被流放的人、公主们看到的是否也是这样的景象:无穷无尽的沙砾与流亡。
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他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介绍了中国和关外各地的关系。[18]在帝国衰弱的时候,突厥、蒙古、匈奴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就会占领关外。而中国强大以后,会把入侵者赶走,强大的中国军队把敌人一路追赶到大夏和费尔干纳波斯帝国。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英雄,其实是作为外交使节的将士,他们到达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地区,跟一些部落结成联盟,以对抗另一些部落。
大量这样的历史记载使得中国人把匈奴视作敌人。法国伟大的中亚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说,那些游牧的突厥—蒙古人,从东西伯利亚发展出好几个部落。他们骑马带箭,穿着长裤和靴子,而不像习惯久坐的汉人那样身着长袍。为了迎战匈奴,中国将在内战中使用的沉重战车换成灵活机动的骑兵。也正是由于这来自突厥—蒙古部落中最强大的匈奴的威胁,才迫使中国第一个皇帝,残暴的秦始皇修建了长城。
即便如此,匈奴还是进犯到长城以内。公元前2世纪,匈奴侵犯中国都城太原[19],汉高祖通过和亲政策拯救了自己和国土。他把一位汉族少女——诗歌中称她为“可怜的鹧鸪”[20]——送给了在诗歌中被称作“蒙古夜鹰”的匈奴统治者[21]。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了一名叫张骞的外交使节越过帕米尔山脉,到达现今乌兹别克斯坦所属领地,想要跟那儿的斯基泰人结成联盟(斯基泰人在被匈奴打败之后定居于此)。但途中张骞被匈奴抓捕,羁留了十几年,当他最后见到斯基泰人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连横结盟以与匈奴较量的建议。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张骞最后回到中国,跟他一起出发的上百名随从只剩下一人。张骞向皇帝报告了西域富裕文明的国家——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印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那一带包围着自己的野蛮部落中,存在着伟大的文明世界。于是,中国决定打通穿越塔里木盆地的道路,让商业和政治活动得以实施。大概一百年之后,一个名叫马埃斯·提提安努斯的马其顿商人派人穿过沙漠和高山,勘查通往中国的道路。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用他收集的信息,为现在位于叙利亚的安提阿和中国之间的地区命名。西方由此发现了中国,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是以商旅带来的中国制造的美妙产品命名的。丝绸之路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提提安努斯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汉朝晚期(公元第1、第2世纪),又一位伟大的皇帝掌握了政权,他派将军班超到塔里木盆地,彻底打败了匈奴,班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从西部的和阗、喀什和莎车,到靠近中国一边的龟兹、吐鲁番和哈密,发动了一系列残酷的战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认为必须要以战争消弭战争,这是伟大君主应该完成的大业。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班超砍下数千人的头颅。中国正史中记载称赞班超“定远慷慨,专功西遐”。“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献上土地出产的财富,或者献上本国重要人物做人质。他们摘下帽子,匍匐膝行,(这些人质)转向东方,向着天子顶礼膜拜。”[22]
丝绸之路从西安延伸至嘉峪关,然后在敦煌分成两支。一支经由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的绿洲,一支沿着南边绿洲而行。西行的路要么越过天山进入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要么经过帕米尔高原的几个山口后到达现在的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玄奘选择从北线进入印度,南线是他回国的路。他证明了数以万计中国士兵开拓、守卫的路线,并非只为贸易、外交和军事之用。这条路也用于为中国带来精神上的变革,带来佛教的慰藉和哲学思想。
***
嘉峪关在戈壁深处约1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工业城的西边。嘉峪关由高高的城墙、烽火台和厚重的城门组成,两个城门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现在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旅游景点,进入需要买门票,你会看到牌子上写着“禁止摄像”,穿过几个防御工事和纪念品商店,还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保护环境之类的标语。你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唐朝时的关口,而是一千年之后明朝重建的,最近也做过大规模的修复。西边的城门外是一片壮观的沙漠,多付一点儿钱(大约五十美分)就可以穿过城门。你可以得到毛笔书写的通关文书,上面盖着仿制唐朝将军的官印,这样你就可以前往西域了。城门外,一个男人穿着破旧的古代服装和裂口的盔甲,骑在一头很老的白色毛驴上摆着姿势,高举着一把剑。
“玄奘没来过这儿。”他骑在温驯的坐骑上向我们宣布,他说的没错。毕竟僧人是为了取得佛教真经而逃离中国的,是个非法出境者。“他从那边走的,”骑驴的人指着北边起伏的群山(当地人称之为黑山),“那边很难走,很危险,不过他只能走那儿。”
“问问他那要花多长时间。”我跟忠梅说。自从在面馆被认为是间谍之后,我不敢再冒险说中文了。
“两年。”那个人说。
他说的不对。玄奘没有说他花了多长时间绕开嘉峪关,但他到达印度一共只花了一年,在黑山花的时间一定比两年短得多。但是,看着西边的沙漠,我还是觉得,虽然这是个靠与游客拍照挣钱的假边关士兵,但他对于那位一千四百年前没有经过这里的谦卑僧人的认识,还是很可靠。
第二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又上了火车。祁连山脉在南边闪着微光,令人敬畏,它们从干枯的草地和戈壁滩上拔地而起,延伸到1600英尺的空中。烽火台遗址、残破的用泥和稻草筑成的塔柱,向西延展出去。沙漠的颜色从赭色到铁锈红色都有。沙漠中有溪谷、沟壑,还有干涸的河床,时不时也会出现绿洲、泥砖盖的房子和几棵树。我们经过玉门火车站时,我注意到几幅广告,倡导十二亿中国人民讲文明、懂礼貌,广告上写着:“不能只有内在变,内在外在都要变。”
我们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柳园。
“柳园没有柳树。”我说,看着四周灰乎乎的荒地。
“那是一种理想,”忠梅说,“有的时候你取的名字是你没有的东西。”
我们住在辉铜旅馆,有独立的卫生间,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供应热水。这个城市没有什么特色,一条平淡无奇的大街,两旁是面馆和几座大一点儿的建筑,楼外墙贴着白瓷砖。我们在一家新疆饭馆吃了一份非常可口的羊肉,喝了一瓶西凉啤酒。饭后去旅馆附近散步,我们走进一条小路,发现那儿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安西县旅游景点”,地图上一条弯弯的蓝线是玄奘在此地经过的路线。
玄奘在兰州待了一晚上,碰到几个骑马的人,他们答应带他到凉州,这是玄奘途中所遇的第二个大城市。凉州现在名叫武威,没有什么特色——除了近年来发现了有名的马踏飞燕,还有7世纪修建的纪念鸠摩罗什的佛塔。那是一位中亚高僧,在4世纪晚期将大乘佛教经典从梵文翻译为中文。到了7世纪,凉州成为帝国西北要冲,也许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交通要冲。来自遥远的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的旅行者在此相遇,偶尔也有朝圣者去往敦煌的寺庙,但去往印度的朝圣者更为罕见。
已经声名远播的玄奘到达这里,僧人和一般信众迫切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涅槃经》和其他佛教的奥秘,他则展示了自己的智慧明达。慧立说那些听到他讲学的人,“有盛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他们还给他“金钱、银钱、口马无数”,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说起法师将要西行去到婆罗门国——印度追寻真理。
玄奘的才智让他备受赞美,但这差不多也是他遭遇困难的原因。慧立这样解释唐皇为什么禁止向西旅行:“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当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听说有一位来自长安的僧人想要西行,将玄奘召来,要求他返回长安。玄奘没有表现出任何违抗命令的样子,甚至还给人遵从命令的印象。但他从河西的佛教高僧那里找到了同道,让两个弟子秘密护送他经玉门向西行。
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奘开始隐秘行事。他昼伏夜出,就像一个流亡者、走私犯、抵抗组织成员,同时受到那些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的帮助。
他想办法到了凉州西部的瓜州,与当地州吏相谈甚欢,并得到粮草补给。他询问前方的路况,被告知要经过一条发自玉门关的凶险河流。关外西北有五座烽火台,彼此相隔20英里[23],“中无水草”,这让他“闻之愁愦”。这位逃亡的僧人“沉默经月余日”,思考着难以预料的形势。当他犹疑不定之时,凉州有人带着文件前来,要求各地区官员缉拿玄奘。瓜州官员于是召见玄奘,问他是否就是文件上要捉拿之人。
我们不难想象玄奘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如果他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不仅违背了禁止向西的命令,还犯了伪证罪,那时候的官员有办法对伪证罪人做出严厉的惩罚。但如果承认,又会被抓捕遣返回长安。因此他一言不发。
“师须实语。必是,弟子为师图之。”地方长官说。
要知道那时佛教在中国是最重要的宗教,其信众遍布中国官僚体制的各级官员之中。玄奘这时一定意识到在这场审讯中,自己碰到了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一个私底下的弟子、一个秘密的同道、一个宗教上的兄弟。于是他承认了,并说出自己要做的事情。地方长官撕掉逮捕令,让玄奘快快离开,这对他们两个都好。
玄奘时代这个中国最遥远的地方的宗教问题,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1982年,我为《时代》杂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采访。那时乌鲁木齐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吐鲁番是新疆仅向外国游客开放的地区。我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酸奶,看摊的女人问我是否是天主教徒。我说不是。她说自己是。我很惊讶。我在新疆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转变,新闻记者很自然都想要采访天主教堂或者基督教堂、佛教寺庙和清真寺,因为这些地方在“文革”之后重新开放了。我通过官方渠道询问过乌鲁木齐是否有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堂,被明确告知没有。但这个卖酸奶的却说有,而且告诉我怎么去。
在一条又长又窄的巷子深处,在两堵高高的泥墙中间的一扇门后,我找到了那座天主教堂。几十个人在忙着修整这栋虽年久失修但明显是个老教堂的建筑。那个时候中国各处都有教堂庙宇在翻修,但翻修必须经过宗教委员会的批准。无论是基督教、罗马天主教都属于叫作“爱国会”的组织。他们可以举行仪式,庆祝感恩节、复活节和圣诞节,但神职人员得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我受到这些是天主教徒的木匠和泥瓦匠的热情欢迎,他们带我参观教堂。
1982年的乌鲁木齐跟7世纪时候玄奘碰到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没有得到新建立的唐朝中央政府的许可,而地方官员则愿意暗中支持他的行动。但即使玄奘沿途受到了那些信奉“四胜谛”的人们的帮助,他的焦虑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他还远远没有离开唐朝的管辖范围,并且现在又碰到了新的问题。还记得吗?在兰州的时候,有两个佛家弟子陪同他经过玉门关。但到达瓜州以后,其中一个离开返回敦煌老家,另一个虽然留下来了,但玄奘发现他年老体衰,很难陪他走过严酷的沙漠,于是玄奘劝说他回家,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向导了。
玄奘向着未来之佛弥勒发愿。他听说有一名叫达摩的僧人梦见自己坐在莲花之上向西而行。“梦为虚妄,何足涉言。”玄奘说,他相信世界是一种幻相,但这个特别的梦还是让他重新燃起希望。这时,一个“胡人”来到此地礼佛。那个人看到玄奘,看到了他身上的神圣,绕着他走了三圈,以示尊敬。玄奘法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槃陀。玄奘留意到他健壮又恭肃,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计划,并请求他的帮助。槃陀答应护送玄奘经过五烽,把他送到通往哈密的路上,这是西域第一个独立的佛教地区。
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槃陀把一位奇怪的老翁介绍给玄奘,他也是一个胡人。须发灰白,骑着一匹瘦马,他列举了前方的艰险、居住在那里的恶魔、无可遁逃的热风,还有无尽的流沙,试图劝说玄奘放弃此行。
“徒侣众多犹数迷失,”那个人说,又说像玄奘这样一人独行,一定更会遭遇那些不幸,“况师单独,如何可行?”
玄奘说自己是为了寻求大法而去往西方,不到达婆罗门国绝不回来,即使死在路上也无怨无悔。
“师必去,可乘我马,”老人说,(慧立在对玄奘穿行沙漠的记录中,没有提到凉州商人和僧人赠予他的无数口马最后怎么样了。)“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7世纪的伊吾在现今哈密附近。
然后槃陀和玄奘出发了,他们夜间行进,抵达河边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玉门关。槃陀砍下树枝,在上面布草填沙,搭了一座桥。他们在最窄处过河,过了河,两人筋疲力尽,在沙滩上铺开垫子睡着了。半夜的时候,玄奘醒来,看到槃陀手里拿着刀向自己走过来。他坐起来,开始向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祷告。这里出现的场景蕴含着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一边是不忠的仆从,一边是向着看不见的神明祈祷的圣人;围绕着他们的是沙漠和黑暗,在不远的地方耸立在黑暗天空中的剪影,是带着敌意和不可饶恕的权力的象征——烽火台。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近在咫尺的权威,也许只是看到了祷告的圣人——槃陀转过身去,玄奘毫发无损。
清晨,玄奘跟向导有一次谈话。向导提出前方的危险。在玉门关的西边还有五座烽火台,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抓捕这些违抗皇帝禁令的偷渡者。槃陀说:“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在讲述了路途多么艰险之后,看得出槃陀自己已经失去热情,跟不久前他同意护送玄奘到哈密时不太一样。他建议:“不如归还,用为安隐。”
玄奘当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又走了几里——一里相当于五分之一英里——槃陀拒绝前行,对此玄奘并不十分惊讶。槃陀说,考虑到家人,他不打算冒险违反国家大律了。他丢下玄奘一人离去了。
“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慧立写道,“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幻觉折磨着他。他看到数百个穿着皮毛、毛毡的人骑着马,骆驼在沙漠上出现又消失,“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着,渐近而微。”但是玄奘听到空中传来声音,喊着:“勿怖,勿怖。”八十里之后,他看到了第一座烽火台和后面的池塘。但是当他灌满了自己的水袋——那也许是一个羊皮做的袋子——一支箭呼啸而来,几乎射到他的膝盖。他终究还是遭遇了帝国的军队,即使这已经是玉门关外。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所有人都劝他回去,烽火台的校尉也不例外,他还提出会派人送他回敦煌。“彼有张皎法师,钦贤尚德,见师必喜。”
不用多说,玄奘拒绝了他的好意,坦率地告诉这位好心的官员没有必要向中国的法师学习。他说,很多年来,即使是最伟大的法师也无一例外地向他寻求智慧。“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敦煌耶?”
第二天一早,玄奘继续上路,带着第一烽火台校尉给他的一封文书,用以出示给其他几个烽火台的长官。晚上他到达第二座烽火台,在附近的泉中取水的时候再次遭遇飞箭。跟第一次一样,他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受到长官的欢迎,并为他提供住的地方,马匹也得到照顾。法师吃完饭后,长官把他叫到一边,警告他不要接近第五烽火台。那里的守卫“彼人疏率,恐生异图”,长官说。他提出一条别的路线,一百里以外的野马泉,可以在那里取到水。
玄奘进入沙漠之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这是他后来告诉慧立的。他一边走一边念着《般若心经》,也就是伟大的智慧之经,帮助人驱走恐惧和痛苦的真言。绝对真实的最高表现就是“诸法空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能想象玄奘一边走一边念诵,在黄色的天空下,孤独而渺小。他又想起了观音菩萨,第十八位大觉者,为帮助受苦的生灵开悟,他推迟了自己脱离这个生与死的世界的时间。就是观音菩萨从耆阇崛山顶峰见到五蕴皆空。五蕴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全都为空。“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玄奘走了一百里之后,找不到野马泉。这没关系——他带的水够支撑一千里的。但当他举起沉重的水袋想要喝水时,水袋从手里滑落,掉在沙漠之上,珍贵的水打湿了砾石,渗进沙子。玄奘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哈密行进,路线蜿蜒曲折,迷惑人心,他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他一度想要调转脚步,回到第四烽火台,但很快就想起自己发誓说宁死也不要向东走回一步。他向慈悲的神明祈祷,朝着自己认为的西北方向继续走去。
“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慧立写道,“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然而,虽然玄奘在五天四夜中滴水未进,“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他躺在沙漠之上祈愿:“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他一直发愿至深夜,一阵凉风不期而至,让他精神一振,也让筋疲力尽的马儿重新站起。
他继续前行十里地,这时马儿突然向着另一个方向奔走,不管玄奘多么努力地想让它走上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向。几里之后,玄奘惊奇地看到一大片绿色的草地。这不是海市蜃楼,他下了马,让马吃草,自己又步行了一段路,“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他明显感到“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菩萨慈悲为生,其至诚通神,皆此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