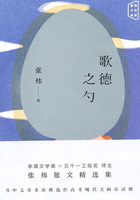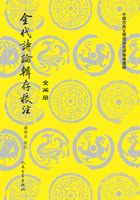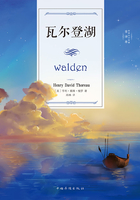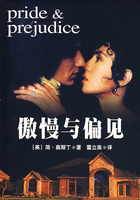THE LONG DEAD
第五天晚上,我们买了去吐鲁番的硬卧票,我们爬进靠得很近的铺位上,就像笼子里的老鼠,火车在塔克拉玛干荒凉的沙漠边缘轰鸣着缓缓前行。玄奘的旅程也是断断续续。经历了沙漠的苦难之后,他在伊吾得到休整,却在旅程中下一个国家遭遇统治者过度殷勤的挽留,几乎送命。这就是高昌国,位于现今吐鲁番的东郊,高昌国王听说有东土高僧到达伊吾,派出包括几位大臣在内的特使,骑马护送玄奘迎入自己的国土。玄奘花了六天才来到白力城,疲惫不堪,希望休息一个晚上,但护送的人催促他继续前行,告诉他前面已经准备好替换的马匹,只要赶赶路,就可以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到达高昌。
玄奘同意了,甚至把他从瓜州开始就骑着的红马抛在了身后,那匹马曾在沙漠之中救过他的命。午夜时分,他们到达高昌,国王亲自出来迎接。从洞窟壁画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盛景。高昌官员穿着长袍,系着腰带;他们胡须弯弯,锥形发髻用丝带固定。包括王后在内的女人们身着织锦衣裙,手镯、脚环、玉佩和头饰让她们熠熠生辉。一千支火把照亮了一千张脸,也照亮了杨树、桃树和杏树,在昏暗的夜色中排列在地平线上。兴奋的君王将自己称为玄奘的“弟子”,告诉他自己是如此盼望他的到来,以至于寝食难安。
众人纷纷表示敬意,包括王后和宫女,这时天将欲晓。玄奘请求休息,国王不情愿地同意了,留下几名黄门侍宿。玄奘秘密离开了一个自己不受信任、处处受阻的地方,来到这片佛教占统治地位、自己不仅受到欢迎更受到尊重的土地。而且,在这片土地的国度里,佛教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受到拥有权力的国王和可汗们的大力支持,这样的国王和可汗将会给予玄奘极大的荣耀,玄奘也没有拒绝。
高昌在吐鲁番东部30英里的地方,是现在丝绸之路旅游路线上一个重要的目的地。这里的高度在海平面下500英尺,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吐鲁番像一个炉子,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一些街道上搭着葡萄架,年轻人在饮料摊子旁边打着台球。我们租了刹车失灵的自行车,在上午的热浪中骑到附近的景点看了看,包括一座18世纪的清真寺,以及被称为苏公塔的宣礼塔。这座塔是苏莱曼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额敏和卓而修建的,根据旅游手册所说,额敏和卓“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苏莱曼向乾隆皇帝称臣,作为奖励,他按时得到乾隆后宫中的舞女(这些交易手册中没有提及),同时也收到资助来修建塔和清真寺。苏公塔是一座120英尺高的柱形高塔,上细下粗,看起来像一颗指向天空的子弹,非常壮观。这座塔使用的是淡蓝色的砖块,现在已经褪成棕色,砌成三角形、水纹形、菱形和四瓣花形的图案。
第二天我们去了柏孜克里克石窟,是这趟旅程中的第一座佛教洞窟,嵌在火焰山上一片光秃秃的崖壁上,火焰山极其炎热,呈现出如月球表面般的铁锈红色。洞窟建于5世纪到6世纪之间,建造经费来自想要得到美好来生的富有商人,他们的塑像就立在他们所资助的洞穴的某个角落。这些壁画在中国石窟寺庙中保护得不算最好,最好的在敦煌,玄奘在回程中曾经拜访。在去往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路上,我们第一次听到对斯坦因长篇大论式的批评,以后还会听到很多次,他切割了很多壁画,带回伦敦,现在在大英博物馆中还能看到。虽然这些柏孜克里克壁画比较小,但有一种特别的光彩,一种绿色、赭色和焦黄色的交错,给那些佛像带来某种柔和的光晕,好像墙壁后面有光照着他们。跟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和敦煌的洞窟一样,很多壁画讲的都是佛本生故事,具有教诲意义的数百个佛的前生故事,讲述他在早期轮回中如何积累功德,从而使他成为了佛。佛本生故事充满了自我牺牲的行为,一个人只有在充分相信轮回的基础上才能做出这些自我牺牲——就像那位王子为了饥饿的百姓,投身到河流之中,变成可以供大家食用的鱼类。还有充满哲学意味的故事,其中动物和僧侣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最痛苦的事情?”鹿说“饥饿”,蛇则说“毒性”,鸽子说“性欲”,鸟儿回答“口渴”。僧侣说:“活着是最痛苦的事情,活着就是受苦。”
然后我们去了吐鲁番市博物馆,那里最重要的展品是6世纪到8世纪的木乃伊。其中有一位女性,去世的时候大概三十岁左右,也许是在分娩时死去的。我仔细看着她,她平躺在一个玻璃盒子中,就像被麻醉后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她的嘴微微扭曲,眼睛无神地睁着。她的头发梳成发髻,不过有几绺从古老的发环中掉了出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小心地用红布条遮住她的私处,显然不希望她的仰慕者产生任何下流的想法。她的皮肤干巴巴的,但没有破损,双手握在胸前,她有一张幽灵般的脸。
这个女人散发着某种魔力。她身上有一种黑魔法的气息,那里所有的木乃伊都有,这是所有遗迹中最令人着迷的部分。木乃伊有着某种净化过的恐怖感。它们是尸体,但又太过古老而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因此不像新鲜的尸体那么恐怖。我在想她是否有后代活下来,很可能有,这让我想象看到远古祖先的尸体会有什么感觉。看看陶片,看看洞窟壁画,甚至只是看看照片,这是一回事。而看着一个千真万确的人,一个也曾会呼吸和思想的人,想象着如果你被埋在干燥的沙子里,一千年后看起来跟她应该差不多一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玻璃盒子里的女人跟玄奘生活的时代差不多一致,她也许就是高昌国一个小小的国民,也许就是深夜出来瞻仰火光下的大师的人群中的一个。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与数百年前的旅行者的联系,看到这个完好无损、可以辨认的人,能帮助我建立那种联系。
毕竟,历史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视野,看到人类努力生存的巨大舞台。我们都是有关联的。说得更具体、更紧密、范围更小一点儿,这形成了卡夫卡所谓的“血缘圈子”。它给了我们可归属的更大的范围。因此,看着这双干涸的葡萄干一样的眼睛,它们可能注视过玄奘,会给予我正在寻找的历史,一种内在的轮回转世,一种类似人类转世的东西。当然我明白,这位女性看到玄奘的可能性非常之低,但那种可能性还是给予这具干枯僵硬的木乃伊奇异的力量。我盯着她看了相当长的时间,下午的时光在流逝,就在一千四百年、七十代人以前,她消磨过炎热的时间、多尘的吐鲁番,我感受到她神秘而亲切的气息。
那天晚上,王勇照常带我们去夜市吃晚饭。那是电影院外面的一片空地,附近街道上的标语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人的义务”。这里的食物是维吾尔族风味的,绝对多肉,显然与佛教不符。大锅里是羊百叶、羊肺、羊舌头和羊蹄,最后跟辣椒一起炖得烂烂的。还有一整盆羊头,牙齿裸露在外,笑容狰狞。我们点了一些浇着红色卤汁的羊肉,还有一些烤肉,配上汤面和温热的啤酒。我们还买了一些西瓜作为饭后甜点,一边走一边吃,把瓜籽吐在地上。广场上都是音乐声,尤其是一位名叫阿卜拉江的歌手(在吐鲁番非常有名)唱的《进入沙漠》,还有什拉利的《我爱的人》,音像店用大喇叭同时播放着他们的歌曲互相竞争。
我看到一个老妇人拖着几个摞在一起的纸箱,走到一个西瓜摊要一牙西瓜。瓜摊老板用长长的弯刀切下来一牙递给她,但是她听说价钱是一块,大概十二美分,嘟囔着太贵了,摇着头,走开了,纸盒子在她身后扬起灰尘。我赶上她,说我想给她买一块西瓜。她看起来对这个会说中文的洋鬼子没有那么惊讶,但还是摇摇头,谢谢我的好心。我告诉她不必拘礼,天气这么热,西瓜凉凉的,一定很不错。但她还是摇着头,有尊严地拒绝了,再次谢过我,继续往前走,在她身后是忧伤地思考着年龄和贫穷的我。生活这样漫长、这样艰苦,却没有一点儿钱可以在夏日买一牙西瓜作为安慰——在那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女人。
第二天我们去了高昌古城,在吐鲁番东约30英里的地方,离柏孜克里克石窟不太远,二者渊源颇深。建造佛教石窟有几个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用于雕刻的石灰岩壁,旁边还要有一条溪流,工匠需要长期居住于此来完成捐赠者托付的任务。高昌有水源,但没有石壁,柏孜克里克有崖壁也有水源,但地形狭窄。高昌地势平坦,绵延在炽热的天空下达数公里之远,如此之大,需要乘坐驴车才能去看烽火台、谷仓,以及上万居民居住的住宅区和礼拜塔。这座古老的城市由汉代皇帝建立,因为他需要一个地方驻扎军队,守卫西部边疆。当玄奘在629年或630年到达此地时,这里已是历经多个王朝的独立王国,而此时正值一个王朝的末年。在玄奘回到长安之前,李世民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把这里作为唐朝西部管辖区域的首府。现在这里的废墟也许会给人灵感写出诗句,感叹快乐的宫殿化为尘土,鲜花变成野草,蝴蝶无处嬉戏。但曾经一度,这里是伟大的中亚帝国,有着权力带来的所有虚妄和浮华。
国王名叫麴文泰,这个男人极其顽固,以致给自己造成悲剧,这些我们可从他日后的命运得知。在慧立根据玄奘口述所作的记载中,麴文泰是个忠诚而热情的统治者,但同时作为君王也有着君王的打算。他让一位八十岁的法师劝玄奘放弃西行,留在高昌。几天之后,国王亲自表达了这个愿望,玄奘诚惶诚恐地拒绝了,国王表示他终究会同意的。这场7世纪时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被慧立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富有修辞之美,适于诵读。
“已令统师咨请,师意何如?”国王说。
法师回答:“留住实是王恩,但于来心不可。”
国王说,在隋朝的时候自己去过中国,途中遇到很多高僧,“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
玄奘认为“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他还说:
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26]。决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波仑问道之志,善财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坚强,岂使中涂而止?愿王收意,勿以泛养为怀。
国王的答复就像一个不能接受被拒绝的情人:“弟子慕乐法师,必留供养,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
“又大王曩修胜福,位为人主,”玄奘回答,“非唯苍生恃仰,固亦释教悠凭,理在助扬,岂宜为碍。”
国王坚持说自己没有导师,因此希望法师留下,“屈留法师以引迷愚耳”。但玄奘还是拒绝留在高昌,因为伟大的追寻真理之旅还没有实现。
在这种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国王开始变得恼怒。从衣袖里伸出手来,他说:“弟子有异涂处师,师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相顺犹胜。”
法师回答:“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
国王继续为玄奘提供供养,这似乎给了玄奘一个主意。慧立形容为“端坐”,意思应该是背部挺直,双腿盘在前面,他三日内不吃不喝。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政治目的的第一次绝食抗议,而且奏效了。到了第四天,国王看到玄奘已经变得虚弱。他感到羞愧、悔恨,在这位绝食的朝圣者面前跪了下来,说:“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两个人为了表达诚意,一起去寺庙礼佛。玄奘终于能够前行,但有一个条件:回来的时候要在高昌住三年。玄奘同意了。
紧张关系结束了,玄奘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再度变得友好而彼此尊重,充满华丽的语言和互相仰慕的表达。国王为法师准备了应付前途寒冷天气的衣物、面罩、手套、靴袜。还给他黄金一百两、白银三万、绫和绢五百匹,足够二十年之用,这是旅程预计需要的时间。他派出二十四名仆佣,三十匹马,并给前方各国首领写了文书:“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
撇开其他不谈,从这些往来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谦恭而精致的礼仪,7世纪时候的交谈技巧体现在这位君王和法师之间。玄奘对国王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钦贤爱士,好善流慈。”
在玄奘重新启程的时候,国王带着自己的僧人和大臣送到城外,“王抱法师恸哭。”现在的玄奘随从甚多,相形之下更像军队而非朝圣者,向西穿过吐鲁番洼地,高昌国王和臣民的伤离之声回荡在火焰山的红色岩石和塔克拉玛干炽热的空气之中。
公元3世纪的历史记载说,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一位名叫景卢的中国官员受斯基泰使臣口授《浮屠经》。我们不太清楚这次佛经口授是发生在中国,还是斯基泰,即现在的阿富汗到印度中部的地区。不管在哪儿,这都是中国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最早历史记录。半个世纪以后的汉朝晚期,汉明帝同父异母的兄弟楚王英为本国佛教信众举办了一次素宴。这是中国第一次记载有佛教群体的存在。
佛教从斯基泰传入中国,这是合理的。我们还记得公元前2世纪中国使臣张骞到达大夏国,在他回到中国以后,报告了帕米尔以西存在的富裕而发达的文明。整个汉朝,在中国称之为“月氏”的斯基泰和中国之间,一直都有贸易往来。斯基泰商人乘坐大篷车穿过高山和塔里木盆地,作为佛教徒,他们可能在沿途的佛教寺庙中停留休整,为了表示感激和获取功德,他们也会行善布施。僧人也在商人的队伍之中,随身携带能普度众生的经文。这样,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商路也服务于精神之旅,通过这条路线,一种在印度消亡多年的思想,得以在中国并随后在日本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佛教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向外传播。在佛陀圆寂之后的头两个世纪,佛教教义并没有传到很远的地方。而后,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皈依佛教,印度无数旅店和饭馆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将佛教定为印度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态度一样。阿育王在印度各地敕建弘扬佛法表示虔诚的纪念碑式圆柱,这些阿育王石柱现在是印度重要的旅游景点。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派人到附近的疆域传播佛教——南部的锡兰,北部的犍陀罗和克什米尔。
同时,被匈奴驱逐出中国西北家乡的斯基泰人,定居在大夏,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这个地区从亚历山大时期就有希腊人居住,现在斯基泰人取而代之,开始扩大他们的影响,包括希腊风格的绘画和雕塑。在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斯基泰人拒绝了张骞结成反匈奴联盟的建议,将疆域扩大到南边的马图拉和贝拿勒斯,成为整个北印度的统治者。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国王迦腻色迦一世,在公元1世纪皈依佛教,而且,跟之前的阿育王一样,大力提倡佛法。现在,从恒河到乌浒河,从印度到犍陀罗、克什米尔和大夏,整个地区都信奉佛教。一定有传教僧人从这些地方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尤其是于阗和龟兹这两个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重要王国,一个在商路的南线,一个在北线。无论是从中国到西方,还是从西方到中国,都必须经过这两个佛教国家中的一个。
佛教在中国并非一直受到欢迎,在这个儒教国家,它总会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中国汉朝的文化是非常讲求实际的,皇帝本人也信奉一种世俗的、以社会关系为指导的思想。儒家思想在汉朝取得了正统地位,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夫妻的纲常关系。遵从这样的伦理从属以保证国家与天伦的和谐。天、地、人都统一在以天子为代表的统治者形象中。表意文字“王”,有着三条横线,分别代表天、地、人,一条竖线将三者联系起来。皇帝进行的仪式,很像古代希伯来人在所罗门王圣殿中的仪式。仪式上奏起音乐,保证天、地、人之间的平衡。儒家六经所培养的精英分子掌握着从先王开始流传下来的智慧。
这样的体制要求皇帝压制异端邪说,历史中记载着儒家官吏敦促皇帝打击佛教的种种故事。一位唐朝官员上书说佛教以其虚妄之言鼓动无知百姓抛弃祖先留下的教诲,引诱他们追求假想的幸福。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仇视佛教的国家,佛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要知道,没有什么野蛮异族的思想在这个中央帝国取得过胜利,而早期的印度佛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外来之物。佛教强调的是一种普世的精神救赎伦理,而中国人看重的却是家庭和国家的关系。
正如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所说,佛教具有一些抽象甚至相悖的观点,主要是说事物并非其表现出来的那样,人们感知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对世俗目标的追求只会导致苦难,对自我的执念也会带来痛苦。佛教哲学详细阐述了一种深奥复杂的玄学思想,这种玄学思想对务实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因为指导他们的并非终极真理等之类问题,而是统治社会的规范。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个人的成功和家庭的繁荣,争取入仕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消磨时间的办法是与妻妾厮混或者写诗。这样,佛教“一切皆虚妄”的观念必定显得既无用又懦弱。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佛经大概是《四十二章经》,它强调人的痛苦来自爱欲。“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早期来自梵文的翻译中,有包括集中思想来战胜欲念的建议,比方说要处理淫欲,可以去墓地,想一想尸体在不同阶段腐烂的情形,而不是做那些祭祀祖先的事情。佛教传递“空”这个概念,在对现实存在同时又不存在的冥想之中达到“无我”的境界——对过于实在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马上就能理解的观念。
当然,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逃离”的需求,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总有劳作、痛苦、疾病、死亡和悲伤,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神秘主义来平衡,或是一醉解千愁。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对上述需求的回应。道教重“自在”,逃离儒教社会的陈规和束缚,强调的是自然力量的平衡和无为,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智慧。表面上看,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芮沃寿提到,佛教诸多概念一开始是用道教的语言体系翻译为中文的。比方说梵文的dharma,意思是“教义”、“佛法”,而中文里被翻译为“道”,意思是“路”——《道德经》难以理解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但是,道教的教义是让人们逃离中国社会中的各种规范,从来都不是一种普世的救赎。诗人们寸缕不挂,坐在草屋之中,喝着酒,写着诗,就像伟大的诗人杜甫所写[27]:
哀歌时自短,
醉舞为谁醒。
道教人士思考庄子的悖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他们服用长生不老和提升智慧的药物,也修炼吐纳之法,以期实现永生。但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整套心理学和认识论的体系,来解释一切经验的虚妄本质。佛教比道教更加完善,它有体系,包括体制上和智识上的,保证只要修持就会得益,并且不需要对月饮酒。在大约1世纪的时候,汉朝的儒教稍稍有所衰落,佛教填补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个时候道教试图与影响力日益壮大的佛教竞争,于是创造出一个“化胡为佛”的故事,说老子去了印度,化身佛陀,改变了那里野蛮人的信仰。
我们已经知道,311年匈奴攻陷西晋首都洛阳,几年以后占领长安,其后三百年汉人失去了对中国的控制。早期来自大夏、犍陀罗和克什米尔的佛教僧人致力于让这些野蛮部落的首领皈依佛教,用佛法来让他们信服。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但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库车的佛图澄在自己的托钵中变出一朵美丽的蓝色莲花,使得原本无知无识的匈奴国王成为热心的佛教资助者。那种资助意味着在那些外族统治国家中,建立了某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些国家政府授权宗教组织建立并督管学校和庙宇。在中国北方兴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北魏,其皇帝甚至成为佛的化身。在来自印度的佛教教义被更好地翻译为中文之后,佛教从语言上与道教厘清了关系。隋、唐让中国重新回到汉人的统治下,之后,佛教完备的体系使得统治者不再把佛教看作是外来的邪恶教义而加以拒绝。他们利用佛教来赢得爱戴,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被芮沃寿称为恺撒式教皇统治的佛教寺院。
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鸠摩罗什,芮沃寿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库车的公主,在他七岁时母亲出家为尼,并带儿子到遥远的克什米尔去向当时最伟大的佛教高僧学习。他一开始学习的是小乘佛教,后来去往喀什,在那里转向大乘佛教,尤其是深入研究“空性”和缘起论,即是说所有事物都是有因缘的,一切事物都是空,不能独立存在。接下来二十年他都住在家乡库车,声誉日隆,最终一位中国僧人将他的声名传播到了中国。前秦,皇帝请鸠摩罗什去往长安,鸠摩罗什也同意了,但在去往长安的途中被非佛教信徒的首领扣留于凉州,直到后秦皇帝派兵攻城,才将他迎至长安[28]。
于是在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终生被尊为国师,主持了规模宏大的译经工作,参与的僧侣和学者达数千人。他翻译了《阿弥陀经》,这是中国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还有译于404年的《般若经》;接下来是《百论》、《中论》、《十二门论》、《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十住毗婆沙论》、《成实论》。他所翻译的经论,对印度哲学家龙树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龙树正是玄奘所崇拜的瑜伽行派创始人的世亲、无著的先辈。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些比较艰涩的内容。龙树巩固了大乘佛教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事物皆有因缘,没有什么是独立的存在——即上文所说的缘起。“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是他最有名的偈语。
换一句话说,我们执着于这个现象构成的世界,执着于累积财物、感官娱乐,而一切都是虚幻,苦难因此不断产生,且不可避免。这是跟中国传统多么不相符的思想,而鸠摩罗什在翻译中将这些思想善加表述,使之成为了中文世界的经典。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深刻的文化传播。在鸠摩罗什和他所指导的数千僧人的努力下,佛教最终在中国生根。鸠摩罗什去世两百年之后,我们这位孤独的非法朝圣者从吐鲁番向库车前进,在他头脑中熊熊燃烧的思想,若要达到圆满,只须完成那位印度—库车混血译者(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为藩国效力的蛮族)曾经做的事。这件事让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更加融为一体,就像中国的儒家思想、书法,以及关于月光的诗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