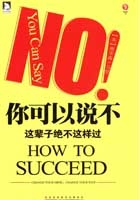他此时才明白,这趟旅程将会是多么悲伤,多么徒劳。
她送他走向死亡,这就是旅程的意义,而她别无选择,只能送他上路。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日,星期天傍晚。海缇·柴尔兹呼唤儿子罗比到大屋里。他从古老的原野走回家,走下高处的草地,沿着牧场围栏徒步而行。牛群正在草地边缘埋头吃草,舔食地上窜出的春草嫩芽。
他的步履蹒跚,膝盖前后摆动,肩膀左右摇晃。他的双手已像个成人,方方正正,手指前端逐渐变细,一头乱发垂在肩上。他的身体已经发育,往后还会长得更高,最近更是长得特别快。他曾在一夜之间就长高整整一英寸,当清晨降临,他觉得身体像是被撑开了,全身都痛,一坐起来就忍不住大叫。
几只狗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母亲问他那天早上在烦什么。最近她开始失去耐心,因为男孩和男人老是有暧昧难明的需求,总要冲动行事,那些事情他们明明还不懂,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她心里,男人就像干旱的日子,或是突如其来的无雨暴风。他们来了又走,他们会痛苦渴求,会私下窃笑,自顾自地叫喊,仿佛察觉到天外飞来的无声召唤。男人永远像孩子,讨人喜欢又经常骚动不休,听觉如狗一样敏锐。男人就像月亮,每隔八天便要改变一次。
他抓着头,手指卷弄着长长的头发。他觉得自己在夜晚被鬼魅攫获,因此辗转难眠,身体抽搐扭曲。
他告诉她,他不知道自己被什么附身。既然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不是故意要对她装聋作哑;但他认为,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耐心等待,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似乎是这样吧。”她说。
在那个寒凉如丝的春天傍晚,他沿着围栏走来,手上的山胡桃木杖哐啷哐啷地拖过木条交叠堆成的泛白栏杆。他想起离家上战场的父亲。他总是想着父亲,好像只要一个念头、一个字或一个手势,父亲就会来到身边。他对远方的父亲大声说话,对他发问,对他发表见解。睡前向他道晚安,醒来时问候他早安。他觉得,要是随时走过转角就看见父亲,看见他坐在凳子上,那也不奇怪。可能不久后就会看到父亲,甚至此刻就能相见。他出生的房间,就是母亲生他那晚睡的卧室。但父亲坚持说,他不是妈妈怀胎生的,而是他们捡到的孩子。他们发现他在水塘里游泳,或睡在牛槽里,或蹲伏在一颗橘色南瓜上,或躲在牛舍后面。
那天傍晚,一堆蚊虫聚集在他的头边,其中有一群初生的朝生暮死的蜉蝣,像是被丢弃的谷壳,鼓动着苍白的翅膀嗡嗡飞动,使逐渐转暗的天空出现无数皱褶。不到一小时前,他才看着它们出生,它们像天使一样飘逸地飞起,飞出石缝中汇集的溪流,在满布大石的草原上画出银色弧线,坠落悬崖之下。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母亲悲伤的声音。
当他走下高处的草地时,狗儿站在她身旁守候着她,姿态肃穆,瘦削的身躯紧贴着她。
一开始她只是轻轻地说,但他似乎无法理解。这时,她才用决断的语气重述:“汤玛斯·杰克森死了。”[1]
“结束了。”她没看他,没想着他的双眼,只是越过他看着远方,话语中没有任何感情。他找不到自己能解读的暗号,没有任何暗示能揭露她的深层思绪。她的神色沉静,那表情只属于某种人,他们经历过无法挽回的事。事实无法改变,就这么简单。他一手紧握着自己另一只纤瘦的手腕,换了只脚站着,仿佛这个动作能让他参透一切。他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当她准备好的时候,就会说明一切。
“汤玛斯·杰克森被杀了。”她终于说了:“这样继续下去根本毫无意义。”她停顿了一下,寻找能表达想法的字句。“这是个错误,我们知道得太晚,但错误已经酿成了。去吧,去找你父亲,然后把他带回家。”
她的话宛如从时光机中穿梭而来,她像一个年老的母亲,一个从古代穿越来的女子。
“我要去哪里找他?”他挺起肩膀踏稳脚步,让自己站得笔挺。
“往南走,然后往东进入山谷,再往北边走。”她说。
她为他缝制了一件有纽扣的紧身麻质夹克,饰有下士穗带,扣子是用锯断后漂白的鸡骨头做的。她告诉他,他当晚就必须离家出发,路上不得有任何耽搁,务必尽快找到父亲,一定要在七月前找到他。
“你必须在七月之前找到他。”她说。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放弃自己的马。如果他和任何人正面遭遇,就说自己是个信差,要说得很急促,表现出匆忙的样子。除此之外什么也别说,只能听别人话中的讯息,就像他现在听她说话一样。她还说,有些人会让大地的水、空气和土壤蒙上一层阴影,他在旅程中会遇到这种人,他父亲也是这种人。然后她停下来思索,接着告诉他:将来你也可能变成这种人。她的语气不带任何批判意味。
“对帮助你的人要千万当心,也要注意提防某些人的善意。”接着她面无表情看着他,要他为了安全起见,绝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不要相信任何人。不管是男人、女人或小孩,都不要相信。”她说。
夹克的一面呈暗灰褐色,以绿矾和胡桃壳染制而成。她翻到夹克的另一面,是蓝色的,还配上了相称的位阶穗带。她告诉他,必须视情况换穿夹克的两面,不管选择哪个颜色,都绝对不能失去戒心。
“找几把护身手枪,尽快去找。多拿几把,子弹永远保持上膛。子弹打完后,立刻把枪扔掉,然后从被你杀掉的人身上取走他的枪。如果觉得对方可能对你开枪,那就不要犹豫,立刻先出枪打他。”她说。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听不出有任何慌乱不安。她很冷静,坚决地指示他,仿佛预料中的时刻终于来临,只是把早已决定好的事告诉他。
“是的,妈妈。”他静静说着,再对她重复她刚才的话:“先开枪。”
狗儿在颤抖,它们低声鸣叫,下颚喀喀作响。
“要记得,”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挺身面对危险,才能和危险擦肩而过。”
他还记得十二岁那年,她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了,能在土地上工作了,但还要再过几年才能为土地而死。至少必须满十四岁,才能为土地而死。他现在正好十四岁。
等她发布完所有指示,他就从井里打上一桶冰凉的水,从胸口冲下,再用毛巾擦干身子。他摊开一件干净的麻质衬衫,套上黑色斜纹布裤和紧身夹克,再穿上父亲的平底皮革工作短靴。他方正的手掌和清瘦的手腕露出袖口,长裤裤脚在靴尖上收拢。他扯扯袖口,拉拉鸡骨头制成的纽扣,挪出空间让自己的胸膛舒适一点。
母亲注意到他长高了,她好像很惊讶。他的脸染上几片红晕,因为她的声音带着母亲的温柔。但大部分的时候,母亲还是保持疏远的态度。他离开前,她没有让他先吃点东西,也没叫他先睡一下,更没要他等到天亮再走。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视线才落在他身上,但是脸上没有笑容。她抬起手,他弯下腰,她迟疑了一下,摸到了他的侧脸,指尖在他的脸颊和脖子周围来回地抚摸,仿佛是个盲人,只能以手视物。随后,她抓住一颗扣子使劲拉扯,他觉得胸膛深处被扯痛了。
他此时才明白,这趟旅程将会是多么悲伤,多么徒劳。她是送他走向死亡,这就是旅程的意义,而她别无选择,只能送他上路。即使他能活着回来,她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竟然让儿子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父亲的性命。
“你把外套脱掉。”她改变了心意,帮他解开纽扣,把外套袖子从他肩膀和手臂上拉下。“尽可能继续当个男孩,这段时间不会太长;然后再穿上这件染过色的外套,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
“是的,妈妈。”
“你不会死。”尽管如此,她的脸上还是笼罩着阴影。“是的,妈妈。”
“你会回来。”她的眼神忽然充满生气,双眼仿佛能看透未来。
“是的,妈妈。我会回来。”门敞开着,他看到了外面的一片黑暗。
“你要保证。”她要求他全神贯注看着她。
“我保证。”
“我会在这里等你。”她伸出一只手捧住他的脸,踮起脚尖亲吻他的嘴唇。
吻他的那一瞬间,她对自己的命令有些犹豫,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就像是神父伸出的祝福的手,碰了一下她之后就立即离去。他等她再开口说话,但她没有。他感觉她的蓝眼睛流泪了,弄湿了他的脸。她再度亲吻他,但这次更加急切,两人都明白,她必须让他离开了,于是她让他走。他往后退开,最后一次挥手,走出门外。
外面,山区清凉的空气缓和了忧愁,黄昏渐渐褪入黑夜。母亲的抚摸仍温暖着他的颈背,他的嘴唇仍因她的亲吻而发热。他为矮壮的灰马系好鞍具,马儿的双眼闪烁着珍珠般的光彩,他骑上马离开家园,走上铜头蛇路。黑暗笼罩四周,如果回头看,他不会看到母亲,只会看到狗儿坐在仍敞开的门口,它们的呼吸规律而缓慢,令人难以察觉。
过了大半个夜晚,他才离开家园的庇护,离开高处的草地和古老原野。他走下山中的蜿蜒小径,进入冷冽潮湿的山谷,离开迂回的山涧,骑马穿过巨大的山谷底部,那里的河上飘起轻雾。他经过树木和突出的岩石,星光被遮蔽了。山中夜晚宁静得很不寻常,月光不时被快速飘过的云朵遮盖,看起来很阴森,但在无云之处,月色穿越云层间隙照进山谷,让他一直沐浴在白色光芒之中,仿佛山谷不是由石头构成,而是明镜般的玻璃通道。月光明亮,让他能看清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还有粗糙指尖上的漩涡。他还只是个男孩,自然会被很多事情吸引,像是光亮如何侵入黑暗、水如何冻结、冰如何融化、生命如何在一瞬间从无到有、实质上不存在的事物如何能持续多年。他心想,若世界真是圆的,那么自己站的地方永远是中心;春天正转为夏天,而我正前往南方,迎接夏季。他想着父亲多么爱好旅行,他从小也一直梦想要踏上旅程,如今真正实现了,他心中升起一股迫不及待的感觉。
他任由空着的手轻轻飘浮在黑暗的空气中,高举着向天空探去,在那里,他的手指包覆住一颗闪烁的红色星星。星星在掌中升起温暖的感觉,仿佛是跳动的脉搏,像是在手中捧着青蛙,或鸣声如歌的小鸟。他轻抚这颗星星,让它在掌中驰骋,随后他将星星拿近嘴边,将它吞下。
那滋味宛如蜜糖。
注释
[1]杰克森(Thomas Jonathan Jackson,一八二四——一八六三),南北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南军统帅,以骁勇善战闻名,绰号“石胆”,后因己方炮火误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