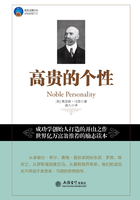他不再想下去,看了看眼前的李胡安,觉得他也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罢了,不值得冒这个险。他只好收起一身的内劲,摊手胡诌:“你觉得我是谁?我是她的儿子!自然要管。”
说着他扶起身后的妇人,附在她耳旁轻声说:“我们快走,有什么事都可以从长计议。”妇人身上受了伤,难以开口说话,被蓝笛搀起走向了医馆。
那几个醉烟楼的护卫汉子松了口气,也不再追,几个人小声疑惑道:老金什么时候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儿子啊?
如先与阿倩二人站在楼上看了许久,阿倩看见蓝笛仗义执言,拔刀相助的威风模样,心中好生佩服,连连拍手叫好,想下去给他助威。
叶如弦赶紧拉住她:“在楼上给他助威也不错,等他打不过了我们再下去搭把手,显示一下武功岂不是更好?”如弦生怕她下去分了蓝笛的心,横生事端,所以加以阻拦。
待到李胡安给他台阶下的时候,叶如弦看蓝笛年轻气盛,怕他忍不住出手,把事情闹大了,惹到醉烟楼的老板那里,恐怕难以收场,到时候三个人就别想按时离开青州城了。所以她们赶紧下楼,又不便开口提醒蓝笛,就重重地踏响楼梯,望他思虑周全。
三人扶着妇人到了青州城里的一处医馆。郎中仔细检查了一番,所幸大多是皮外伤,开了些内服外敷的药,将养数日就能痊愈了。
阿倩将她扶到床上,帮她洗了把脸,露出颇为秀丽的脸庞,又为她整理起衣襟,翻到领口时,只见墨绿色的衣领内侧又用松石绿的丝线绣了一个极为精细的流云纹,云纹和衣裳同色,极为隐蔽,不将衣领翻过来仔细看的话则难以发现。
叶如弦在旁边看着,脑中仔细回想,这流云纹仿佛在“避夏轩”的黄花梨屏风上看到过。一时不知道这妇人和避夏轩的主人有什么关系。她转念一想,云纹有如意的寓意在里面,或许只为讨个吉利。在大樾朝,有许多家族都会将祖训、图腾绣在衣服上,以此表明不忘家族、不忘先祖教诲。
这妇人缓缓睁开眼睛,神智满满趋于清醒。她将眼睛睁大,也不言语,只见她眸子里的泪水终于冲破眼眶,她一侧身,都滴在了枕上,神色可怖,仿佛在回想极其痛苦的往事。
阿倩坐在床边,拿起帕子为她拭泪。她抓住阿倩的手,喃喃道:“你们是好心人…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我…我着实是不想活了啊…”她带着哭腔,话说得断断续续,语气里极尽哀求之意。
阿倩最是看不得别人如此可怜,连忙问她是怎么回事。那妇人叹了口气,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她自言本名叫卫淑静,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庶女,母亲为妾,无奈早亡。
家里的主母和父亲要将她嫁给颍州的徐员外,那徐员外比她老了不少,又名声极坏,她当然不愿意嫁给徐员外。当时坊间有一穷秀才,名叫金不焕,日日给他写诗递书。
今天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明天是“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后天只道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卫淑静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打动,觉得他情深意重,又有父母逼迫嫁给徐员外。一个是青年才俊多风流,另一个是不惑之年多作恶,两相比较,更觉得这是良缘。于是情爱日笃,一来二去,两人就私定终身,结为夫妇,约定逃婚,不日就离开了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