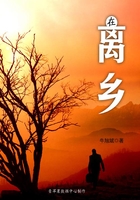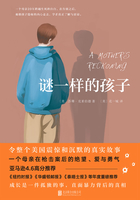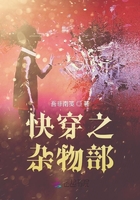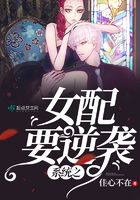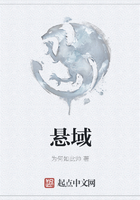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吧,正是青枝绿叶的年龄,我以还算不错的成绩考入了全镇最好的初中的“尖子班”。那是一所满是红砖墙的校园,房前房后种的全是高大粗壮的泡桐树,把整个教室遮蔽得没有一丝烈阳。
这所中学有着一个很理科的名字“十九里中学”,学校里的气息却和文科贴得很紧密。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有个叫“张太守”的大师兄,写得一首好诗兼好字,经常负责全校的墙报。那是一面宽广的山墙,全是由红砖砌成,上面用雪白的纸张写上了大师兄的朦胧诗,还有一些是校园里写得比较出色的作文,还给配上了五颜六色的宣传色插图,引得许多少男少女驻足观赏。
老实说,我羡慕极了那些上墙的名字,羡慕极了墙上潇洒的毛笔字,做梦都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变成”他们,在校园里风光一把。
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呀!诗歌还大行其道,硬笔书法临摹本几乎每个男生都有一册,能作诗、会写字,似乎成了懵懂的少年吸引女孩子们注意的唯一法宝。那时候,我曾为了写诗而买下了厚厚的一册《汪国真诗集》,那可花了我两个星期的伙食费;还曾为了写一手硬朗的钢笔字而练遍了较为出名的“庞中华”“顾仲安”等书法家的字帖。
在夏天的深处,在繁茂泡桐喧嚣的蝉声里,我在写着属于自己的诗,练着自己的字。丝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只要能看到草稿纸的空白处,都会被我密密麻麻地写上或长或短的诗。为了让自己的钢笔字能够尽量“出眼”一些,我的食指肚和中指侧面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即便如此,我仍没有一篇范文能够获得老师的青睐,论写字,我也永远是三名开外的那一人。
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呀!来自农家的我,抱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得泪水奔涌,而那本书,却是我从班上一位女生那里借来的。那是至今最能让我感动的一本书,因为,书里的每一个字句恰恰契合了我当时的心境。依稀记得,那本书,我借故说弄丢了,再也没有还那位女生,直到初三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特意进城买了一本新的给她。
那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去离学校不远处的街边用一块钱(有时候只花六角),喝一碗“油茶”,外加两根油条(有时候只一根),然后吃得满头大汗,走进校园里高声读英文单词。当时,连环画刚刚与我们作别,“李雷”和“韩梅梅”成了英语课本这样一种“外文连环画”里的主角。还有另一件高兴的事情,就是到街上的照相馆里照一张艺术照,把底片冲洗到无比暗淡的地步,在给女同学写同学录的时候贴一张在上面,其实,照片背后是暗藏玄机的,多半被写上了懵懂的小心思、小情愫,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发现。我也早已忘记上面写了什么,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回收一册某个女生的同学录,揭下来看看我照片的后面都写了什么,那应该是我的青春留下的最美印记。
泡桐花的甜香飘满整个校园的时候,一位师兄在春游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时尚的都市女生,她的相貌我早已忘记,名字也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那时候那女生给他写的信,他几乎给班上每一位男生都看了个遍。那女生的字迹谈不上美,却很娟秀、匀称,我记得最清的是信纸,飘着花香的信纸,背景是《泰坦尼克号》里的杰克和罗斯。那女生说,只愿他们也像电影里的“他们”。我们班的男生都红了眼。
我一直忘了补充,我的这位师兄气质自然是非常阳光的,喜欢穿一身红色的运动服,最重要的是,他写得一手非常棒的情书。
仔细想想,以上这些,应该算作是我和文字结缘的真正原因——虚荣、躁动、早熟。
然而,这恰恰成就了后来我坚定与文字为伍的信心和决心,让我这样满怀期待地一直蹒跚走来,这一路上,我得到了无数师者的帮扶和提醒,也得到了无数朋友的鼓舞和勉励,总算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我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
因为,在我心中,始终装着一片别人不了解的梦境,我所经历的岁月也似乎只有我自己才能体察。
今年,我已年届而立,这么多年以来,我心灵深处始终记得初中校园的那片墙报,记得那本被我临摹得变了模样的字帖,记得路遥,记得写在艺术照后面的情书……我记忆里的一切一切都和文字有着某种无以言说的关联……
那真是些期待满满的日子,期待长大,期待自己能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期待能够尽快收获属于自己的爱,而这一切,仿佛也都把希望的赌注押在了文字上!
我想说的是我和文字的缘分,也是和文字有关的期待。
如果你和我是同年代的人,也在小镇中学成长,我相信,这份感觉,你也有……
你懂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