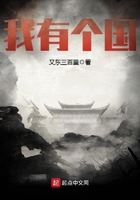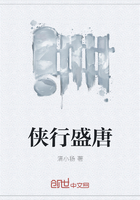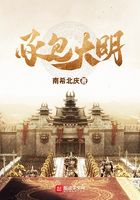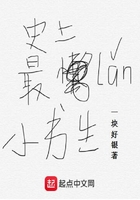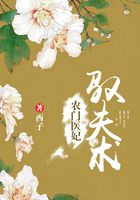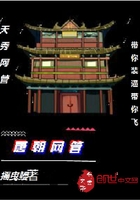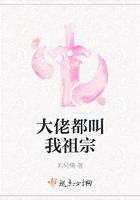汪皇后在来悟道堂之前已经仔细问过了知晓外面情况的内侍们,皇后心想,虽然事起突然,不过最后总还是得息事宁人,勿使事态蔓延扩大才好。
所以当皇后见到皇上及一干朝臣,便婉言说道:京师遂然生变,两宫太后极感不安,故命妾身来此打听。陛下,以妾身浅见,一切总以息事宁人为上。
忠义郡王宪源和大学士陈从圣听了这话,都随声附和:娘娘明见!臣等都是这个意思。
汪皇后说:时不我待,皇上宜早下赦旨,使内外人心安定,则祸乱自平。
在皇后和朝臣的一再促请之下,皇帝也就此下台,命王守礼拨出内帑,以补粮饷之不足。
申时,宫里终于颁下赦旨,将京师变乱归咎于兵部的不察和户部的克扣,两部的官吏上下蒙敝,欺君误国,凌虐下民,禁军的将士出于义愤,替国除奸,虽行事孟浪,惊骇内外,然其情状可悯,忠勇可嘉,因而法外施恩,一律予以宽大赦免。如今祸首已遭诛戳,禁军将士宜各归本营,不得再有非法情事,否则严惩不贷,例无宽赦。
汪皇后见皇上下了赦旨,这才满意的离去,八喜堂那里她还要拿话去稳住太后老菩萨。
然而京师之乱并不因皇上的赦旨而平复,乱兵和暴民嚷嚷着要严惩元凶首恶,说什么国贼一日不除,军民百姓纵难自安。这矛头所指,意在太宰周公。
况且,京中骚动其因在于官库无粮,而私卖猖獗,百姓每户每日所食,官府都给限升限斗,所供的糙米粗粮仅能活命,却难求一饱,然而京师巨商,家家粮油充足,银钱堆积,却还惜售居奇,哄抬物价,强买强卖,大发横财利是,官府对此睁眼闭眼,不闻不问。
京师人人都说,来聚丰、十全记这些商家跟朝中公卿贵戚们有牵连瓜葛,所以才敢这么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对此京师军民早已忍无可忍,敢怒敢言。
今日恰逢军士哗变,城中秩序大乱,于是军民合力将十全记、来聚丰、鑫盛源等京中大店给它来个毁墙拆屋,开膛破肚。这一看可了不得,果然是米谷成山,银钱如海,难怪这天下的米谷银钱都不见了去向,却原来官库通了私库,国税皇粮、民脂民膏全让一帮国贼硕鼠们给盗窃瓜分,藏进了自家的腰包私囊,自然街市上米珠薪桂,搞得军民百姓们活命艰难。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如山的米谷,堆积的银钱,便是堂堂铁证,不需人再作鼓动,京师群情激愤,是以虽有皇上的赦旨,军民百姓却仍要皇上惩治元凶,诛除国贼,不见奸佞的人头落地,决不肯善罢甘休。
乱军暴民不肯归营散去,京师九门洞开,无法关闭,京兆衙门和揖捕司此时几近瘫痪,六部的大火也始终无人扑救,面对这城中之乱,镇抚皆难入手,永寿宫里的皇帝和朝臣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申时三刻,另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入宫廷,南营的禁军眼下也在群起鼓噪,说是要出来清君侧,除奸佞,安天下!
消息是王守礼带回来的,自然内廷令王公公最终没能接管南营的禁军。南营的几个都尉不仅拒绝听从王公公的指令,甚至都不准王公公进入大营。都尉们为此还搬出了祖制国法:按律,皇上委任主帅掌治军务,号令麾下各部,而监军使不过是随军监察而已,岂能执掌帅印,指挥三军?再说国朝从未有过以内侍宫监充任主帅的成例。
内廷令王守礼受了禁军都尉们的奚落,他们的轻蔑不屑也让王公公记恨在心,所以在御前难免添油加醋的挑唆皇上要从严治军,以防变生肘腋,措手不及。
南营北营两支禁军合共有六万之众,而负责守护宫廷的金吾卫,人不过五千,所以一旦禁军生事,再加上暴民鼓噪闹腾,宫里自然难以安生。
忧心不已的皇帝赶紧叫来陆怀,嘱咐他说:外面的情形如此不堪,朕亦不知将何以演变,你速去准备车驾乘舆,以应万全……
朝臣这时都听出来皇上想一走了之,大学士陈从圣忙说:圣驾此时出宫险矣,乱军暴民阻塞街路,圣驾何以出城?出城又欲何往?若乱军惊犯车驾,挟持天子,岂不乱上添乱?
这话把皇帝给吓住了,他皱着眉头,恨恨的说:留也留不得,走又走不脱,难道叫朕困坐此间不成?
陈从圣说:太尉唐郡王父子相率治军,于军中颇有人望,当此危重之际,陛下不妨委之以重任,令其设法安抚。禁军将士如能够说服归营,京师自然重致太平。
皇帝也觉得别无他法,只得降旨以大将军唐觉之掌领军务,出面安抚京师人心。
身在八喜堂的汪皇后,心里一直记挂着悟道堂里的情形。当她从何知书口里得知王守礼被南营将士所逐,而唐觉之将要掌领禁军的消息,心里顿时一沉:禁军哔变,其后究竟有没有奸人操纵指使,不弄清楚这些情况,变乱恐怕难以止息。虽然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一切都是唐觉之在幕后策动,但是在眼下这个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让唐觉之出来掌领军务,安抚人心,汪皇后总觉得不甚放心。
然而在八喜堂这边,两宫太后已经知道京城里发生的骚乱,那些多嘴多舌的内侍们不怀好意的讲述外面的情况,听得两宫太后一惊一咋,皇后在向她们解释的时候,因此枉费了许多口舌,耽搁了不少正经大事。
皇后听到这消息,不得已又要往悟道堂去,登上鸾舆之前,她吩咐何知书,将那些在太后面前多嘴多舌,唯恐天下不乱的混帐东西,每人掌嘴二十,看他们往后还敢不敢混七混八的乱说话。
但皇后到底还是迟来了一步,在汪皇后到来之前,大将军已经谢了恩领了旨,这会儿怕是早出了永寿宫的宫门。汪皇后怔了半晌,一时竟然无语,只在心里叹息了一声,她想:大将军此去,但愿不是放虎归山……
陆正己为颐养病体,住到了城外的山庄,京中大乱的时候,他正在寝室里憨睡,等他一觉醒来,南都已经翻天覆地的换了景象,从人等在床头赶着向他禀报京中忽然发生的变乱。
陆正己竖起两耳在听,听完了,“噫”的一声,忽然翻身下床,他的这一身病,不知不觉中竟然全好了。他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每走一个来回,头脑里油然便生出一个点子,就这样边走边想,大致想妥当了,他才定住脚,大声地吩咐从人:备车,我要进城入宫。
从者面有难色:城里这会儿正乱着,大人不妨等风波稍为平息再进城入宫……
“蠢材!你懂什么!”陆正己按捺不住的大笑起来:“京师生变,这一回注定有人要殉社稷,赴国难,老夫若赶得及,正好可以送他们一程……”
太师的笑声尖利剌耳,从人们都有些毛骨悚然。
承运八年的十月初九,太阳灿烂的照耀了一天,公主府里的每个时辰因此都变得非常的难捱,至少保义夫人悬着的心从日出的辰时到日落的酉时,一刻都没有放下来过。
即使是躲在公主府的深深庭院里面,她和宁安公主以及姚夫人和赵钱氏等人都能听到从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些一浪一浪让人胆战心惊的喧嚣,而这一天奴奴和如如也是出奇的乖,他们呆在大人的身边,既不哭也不闹。
整个一天,外面嘈杂的喧嚣几乎不绝于耳,间或还会传来几声哀嚎与哭叫,府里的门都闭得死紧,壮奴健仆们提刀带剑的四下里巡视待命,这让躲藏在屋里的女人稍稍感到安心。
在屋子里枯坐无聊的时候,屋子里的女人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象宁安公主想到的就是大悲庵里的那个地窖,此外还有卫州城外的那座破窑;二夫人姚璎珞却忆起了兖州城破时,她和姐姐被军校抢入营帐,爷娘兄弟带着家人跟在后面呼天抢地,假如不是路上有幸遇着了姐夫方镇川,自己这金贵的身子只怕就给军中的小校们给生生玷污了……
姚璎珞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不无几分幽怨,她和姐姐姚琉璃本都是洛都的东宫太子看中认定的选侍,正等着来年入洛进宫,这江南兵要是缓来一步,又或是攻取不胜,只怕她们如今已然是长安宫里的妃嫔娘娘了……只可惜人的造化有大有小,福气也有厚有薄,她和姐姐都是有这个贵命,没那个时运,结果没能入居洛都、长安的宫室,却辗转来到南都金陵的贵家,做了别人妾侍二房……虽说也算嫁得贵婿,可是跟进宫做娘娘比,自然差了老大一截。
保义夫人这时也在想心事,她想着她和师父还在大悲庵的时候,也曾躲过好几次土匪山寇的袭扰,只是大悲庵薄薄的两扇门板比不得公主府上的千门万户,所以就算是有人要冲撞进来,这一扇扇的破门入户,恐怕也要费上好大一顿功夫……
所以保义夫人的一颗心虽然始终是悬着挂着,可是她却也未见得有多害怕,呆在公主的府上总比呆在大悲庵里要安全得多,公主府上都是贵人,要是连贵人们都不安生,受到惊扰,那么天底下也就没几个能安生的人了。
但是回头想一想她师父曾经说过的“劫数”,她也觉得很有道理,人都是有劫数的,既然是命中的劫数,那就是各人该受的,自然也就逃不掉,躲不过……
这一天府里没有生火做饭,天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胡乱的吃了点饼子充饥,宁安公主什么都吃不下,她看着外面映红了大半个天幕的火光,心里胡思乱想却什么都想不周全。
天终于黑下来了,屋里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吃了两个饼子的赵钱氏换了一个坐姿,低低的说了一句:唉,老天爷,外面这都是怎么了?闹来闹去的莫不是要变天了?
这话自然是大不妥当的,可是这时候谁也没有精神开口驳她。“阿弥陀佛!”保义夫人先是念了句佛号,跟着低声诵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保义夫人本来想念诵一部长经,只是好多以前背得滚瓜烂熟的经文,她现在都已经忘得七七八八,只有这部心经,因为篇幅短,字数少,所以依然记得牢靠。
这一天京师的大乱,成全了巡街校尉张宝官和他手下的弟兄们。他们趁着这百年难遇的好时机连做了十几票无本的买卖。
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虽识时务,却不想做俊杰,街上都乱成一锅粥了,乱兵暴民甚至连花子乞丐都在抢劫掠夺,他们要是不跟在里面抢,也实在愧对老天爷的恩赐厚赏。况且十全记,来聚丰这些人人咒骂的黑心肠的店铺,就算是抢了那也无愧于心。
张宝官抢掠了几家之后到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领着兄弟们去濡沫坊转了一趟,公主的府第戒备森严,想来府里的豪奴健仆也都不是吃素的,何况贵主的府第,谁有恁大的胆子敢来侵犯?这疙瘩的事看来不需要自己操心费神。只是手底下的李佛奴千恳万求的要留下来守护公主府,张宝官摇头苦笑:这痴儿,陷在春梦里总是不肯醒,也罢,且由他去吧。
当下一伙儿重又呼啸着上街,因都穿着官衣,百姓们到也畏惧,只要见了就躲得老远,所以在京师的街头结党成群、横行无忌的,除了穿甲胄的禁营兵士,便是揖捕司的这些穿“巡”字官衣的军校和京兆衙门里着公服的捕快差役们。
三拨人马都是吃皇粮国俸的,自然井水不犯河水,京师的店铺全、富家多,礼让了这一家还有那片店,所以一路搜来,各有斩获,而待军爷们翻搜抄捡之后,百姓们还要再去洗劫一遍,末了燃起一把大火给他来个毁尸灭迹,这也是京中街街冒烟、处处火起的原因所在。
唐觉之从金吾卫中抽调了百十来名随从,然后快马加鞭赶往禁军南营,沿途所见,六部诸衙门皆成断壁残垣,余火未尽,烟蔽长空,而往昔热闹繁华的朱雀街彩衣街,冷冷清清,一片狼籍,两旁的店铺几无一家能称完好,死尸伏地,三两可见,满目荒秽,遍地萧索,不时可见低头哀哭的百姓,失魂丧魄如行尸走肉。
唐觉之见此惨状,不禁一声长叹,当下心中暗想:为今之计,先须安抚军心,军心安定,则京中灾乱自平,南北营的禁军将士说起来都是自己的部属手下,唐觉之自忖有把握说服他们听从圣命。
等唐觉之一行赶到南营,南军的马行原、储定安等几个都尉早已在门前等候着,见着大将军后都聚拢过来,唐觉之翻身下马,边走边说:南营现在还没有乱,这全赖各位大人持军有道,约束有方,事平后当禀呈圣上,替各位请功……
几个都尉神情怪异的跟在唐觉之身后走进营帐,唐觉之说:北军作乱,京师遭此大难,圣上忧心不已,特命吾来提调南军,惩乱平叛,还望诸位大人鼎力相助。
这时谘议参军参军张成义的走上前说:今日之祸,全在于太宰弄权窃国,大将军当替国除奸,安抚人心,南营将士自当追随麾下,建功立勋!
几个都尉点头称是,都说:吾等愿听大将军号令,不过国贼不除,将士们心寒意冷,未必肯听命上前。
唐觉之道:朝廷养兵千日,指望着用在一时,岂有讨价还价的道理?
张成义道:食君之禄,自应事君以忠,然而眼下人心不服,驱之上前亦未必肯用心用力,大将军如能率禁军将士为国除奸,自然万众响应,马到功成。
唐觉之又惊又怒,喝叱道:张成义,你是想挑动禁军抗命造反么?太宰有罪,自有朝廷圣上议处,与禁军何干?若再胡言乱语,当斩尔头颅!
张成义凛然不惧,侃侃直言:大将军岂不闻陈桥兵变,皇袍加身的典故么?南营的将士如今齐集在大将军麾下,趁此变乱动荡之时,乘风乘势,当易如反掌。
张成义周围的几个都尉听此言都是频频点头,张成义又说:南营将士要清君侧,诛国贼,安天下,谅皇上亦不能不许……
唐觉之道:乱臣贼子,吾辈不为!张成义,你素来有“小诸葛”的名号,却怎地如此糊涂?你以为凭京师禁军区区五六万人便能逆谋成事么?
张成义拱手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将军难道不知?何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此良机,舍之难求,大将军若不肯为,则将士们自为,卑职和诸位都尉早已商量妥当。为或不为,大将军须当机立断。
唐觉之冷笑一声,抽出腰间的宝剑,喝令:你虽曾救我性命,今日之事却不能由你作主,左右将此逆徒与我拿下!
几个都尉脸色为之一变,当下纷纷拨出所佩的刀剑,严阵以待。
张成义却笑道:大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将军虽忠于朝廷,朝廷却对将军百般猜疑,以至于投闲置散,弃如敝履,卑职和诸将士皆为之叹息。今大将军受命抚军,正是一呼百诺,所向披靡之时,若不能顺势而为,他日必受祸于今日,不才所言,惟望大将军深思。
唐觉之怔了一怔,抬眼看营帐之中,人人都是虎视眈眈,这会儿答应不成,不答应似也不成。
正僵持不下,门外却报太师陆正己赶来此处。陆正己本来是想进宫去见皇上,岂料宫中四门紧闭,叩之不应,呼之不开,陆太师正没安排处,且听说太尉唐郡王去了南营抚军平乱,于是便驱车而来。
兵士们将陆正己迎入帐中,张成义喜道:有文有武,有将有相,想来这一回诸事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