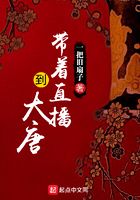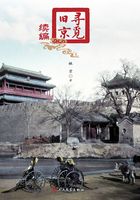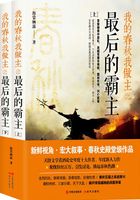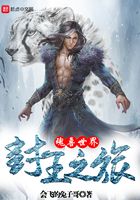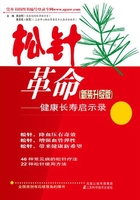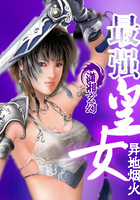陆太师不迟不早来得恰恰正好,南营的都尉们赶来见过,说起这盘桓于心的想法,一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北营的兄弟们因何起事?都是当国的宰执大人们给逼出来的!要我说,京师的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当兵吃粮,吃粮当兵,这粮都没得吃了,还当什么兵?还不如落草为寇,做个逍遥快活的土匪强盗!再说咱们禁军将士,追随大将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那一样都不落人后,可到了论功行赏之时,偏生就忘了咱们的功劳苦劳!同样都是当兵吃粮,比比金吾卫的那些花架子,咱们禁营的兄弟就象是丫头姨娘养的!金吾卫人人拿双俸,逢年过节有恩赏,连吃的禄米也是内府天仓拨给的官用御米,偏偏咱们顿顿糙米粗饭,还短斤少两的不管饱,这都叫什么事!这帮子奸佞国贼不除,还能有咱们的好日子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衰败,说来正是坏在这些国贼奸佞手上,老太师今天来得正好,给咱们拿个主意,好把这些国贼奸佞统统铲除诛灭……”
陆太师听得这话,凛然一惊,当下皱起眉头,轻易不肯吱声,唐觉之等他们说罢,却是一声苦笑:舅父大人听听,将士们口口声声说要清君侧,诛国贼,甥儿一再好言相劝,奈何他们总是不听……
陆正己想了一想,正容说道:当此危难时刻,朝廷和皇上正要借重诸位将军,虽说宰执无能,祸国殃民,不过总要朝廷论罪才行,岂能目无纲纪,以此要挟君上?
唐觉之连连点头附和:正是如此,太宰有罪,自有皇上处置,何须诸位鼓噪生事?将士们齐赴宫门,到底是意欲谋逆还是存心造反?诸位身受国恩,出掌禁军,平乱安民,为国效力,乃是职分,岂能抗旨违令,大逆不道?我奉劝诸位将军三思而行。
马、储等几个都尉面面相觑,一时仿佛拿不定主意。
张成义却道:世事皆在人为,瞻前顾后必然大事难成,众人齐心则无往不利。周氏当国,百姓冤痛,天下谁不衔恨咒骂,今日之乱,周氏实为祸首,禁军将士们声讨奸佞,为国除害,又何罪之有?
陆正己斜睨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你是何人,敢在此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张成义道:不才乃禁军南营的谘议参军张成义是也。
陆正己厉声道:你既是南营的参军,不参预军务却参预逆谋,可知是犯下死罪!
张成义哈哈一笑:人固有一死,太师老大人不必拿死来吓我!古人云,谋定而后动。今日南营的将士替国除奸,为民除害之心,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太师和郡王并非周氏一党,特才以实情相告,尚望太师和郡王能够共襄义举,铲灭妖邪,安定家国。
“天下是吾皇的天下,各位切莫以为只手便能翻得了天!北营将士抢劫官仓,焚毁衙署,齐聚宫门,形同威逼,已与谋反无异,各位岂能不慎!趁现在皇上下赦旨,法外施恩,南营将士当效命吾皇,整肃京师,平叛弥乱,这实是立功受赏的大好时机,各位何苦乱上添乱,自蹈不法!”唐觉之面色一紧,苦口婆心犹在好言相劝。
张成义道:“北军已乱,京中能仰仗者惟我南军,此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尽归于我,若不趁势而发,此后再无机会。我与军中的都尉早已计议良久,再无变更的余地了。老太师、大将军若能共襄义举,南营将士必奉号令,以供驱使,否则多说无益,只能委屈两位大人暂留军中,以免走漏消息。”说完环视众人,马都尉储都尉都是点头不迭,连声称是。
陆正己一声长叹:唉,天下未乱,自家人到先乱了……想不到这一乱一治,竟是由天不由人的。
马都尉说:北军哗变,皆因上司凌虐士卒、克扣粮饷,故其事出有因,而南军逼宫,乃是代民请命,此行兵谏皇上,亦是迫不得已。诚如张参军所言,事如箭在弦上,当不得不发。两位大人要么随军同发,相共进退,要么就只好借二位的人头祭我军中大旗。
唐觉之又惊又怒,喝道:你们、你们真的想造反了不成?
“诛国贼,清君侧,吊民伐罪,何以言得造反?及至事成之日,天下太平,将士当诣阙下请罪。”储都尉手握腰间的刀柄,目视众人,张口大叫。
眼见着帐中几位都尉都在摩拳擦掌,而帐外整装待发的将士已奉命列队集结,陆正己料是阻拦不得,只得道:请各位不妨稍待,容吾与郡王小叙片刻。
张成义点头首肯,陆太师当即与唐觉之走至无人处,唐觉之尚未及讨教,陆太师已低声说道:今日事已至此,是福是祸难以预料,须走一步看一步才行,吾看这张成义不是凡类,今日事必是他于其中鼓动引发,此人如不能为我所用,郡王应设法剪除,以绝后患。
唐觉之皱眉道:南军兵谏逼宫,干系非同小可,咱们掺合此中,罪过不少,这岂不是授人以柄,而家族蒙祸……
陆正己道:假如能借此扳倒周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何况法不责众,咱们参预其中,既能居间转圜,又可见机行事,皇上知道亦未必会怪罪……
唐觉之乃有些犹疑:舅父大人,周相是太后之弟,储妃的祖父,若是扳而未倒,将来仍能起复,到时候岂肯罢休……
陆正己铁青着脸说:今日事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你死我活,本来如此,若是能借刀杀人,岂不更妙!何况事皆禁军将士所为,乱兵逞凶施暴,谁能奈何得了?大将军不过顺势而为罢了。
唐觉之道:禁军要是作乱,其祸定然不小,京中要是无人约束统辖,当不知会乱到什么时候?乱成什么样子?唉……我只怕乱源一起,诸难并作,天下危甚!
陆正己道:周氏既灭,唐氏可出山矣!大将军何忧之有?再说,今日之事,凭你我可以阻之么?既不能阻,又不能置身事外,那便只有随机应变而已。
南军逼宫从戌时一直延续到亥时,初始还只是兵士们在闹,慢慢地京城的百姓都闻声而来,听说禁军将士们要诛国贼,除奸佞,都是大声叫好,打听得众将士居然没吃夜饭,赶紧的去生火忙活,不大会功夫,饭粥糕饼的就都送来劳军。
皇帝接到警讯,连差十几位内侍到丽景门的城楼上打探,都说外面军士连同民众里三层、外三层的将永寿宫围得如铁桶一般,打着得灯笼火把照得一片雪亮。
内侍们还说:乱军暴民皆说,请皇上舍周相之头,安众人之心,息天下之怒!
皇帝感到震骇,连声问座中的朝臣:兵士们是想造反么?皇叔,你说说,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将士们眼中还有朕么?还有朝廷么?还有王法么?
忠义郡王宪源说:陛下,禁军将士出于公心,不得已方行此兵谏之事,不过是吁请皇上为民作主。
皇帝摇头叹息:吁请?朕看这是胁迫!此乃国朝肇基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太宰有罪,自有国法处置,岂能听任乱军示威要挟!禁军今日既能行此悖逆之事,他日又有何事不敢为?此例断不能开!
皇上的突然决绝,大出朝臣们的意料,只有太宰周如乐颤声说道:臣负恩如此,万死难辞其咎……
皇帝瞥了他一眼,冷淡地说:卿有大过,且去职待罪,等候议处吧;皇叔宪源宜任太宰,左相戴有忠废爵留任。王守礼,你这就到到城楼上宣谕,将士百姓聚啸宫门,法所不容,律所严禁,宜自行散去,否则以图谋不轨论。
王守礼口里应诺称是,却不忙着走,皇上这是在气头上,这样的圣谕要是照本宣科的宣下去,这事可越发闹大了。
京兆尹崇恩赶紧道:请皇上收回成命,乱军宜抚不宜激,一旦激生事变,只怕后果堪虞!
大学士陈从圣也顿首说:皇上且忍一时之气,待日后人心初定时再作计较不迟……乱军所逞不过匹夫之勇,只要皇上温言抚慰,当不至于胡作非为,而若是激起凶焰,于京中横冲直撞,反而难以收拾。
忠义郡王宪源则说:宫禁重地,至为紧要,倘若金吾卫不能守,两宫太后因此受惊,皇上何以自处?
皇帝呆了一呆,终于放缓了语气说:王守礼,你去告诉将士们,太宰已遭罢职,其罪朝廷正在议处,禁军将士忠公体国,心存社稷,朕皆知矣,明日当拨内帑银两犒劳诸将士,夜深更寒,将士百姓其宜自散。
王守礼这才领命,疾步跑去宣谕颁旨。
承运八年的十月初九,张福妃自涎下麟儿后,便昏睡沉沉,所以外面即便闹得沸反盈天,她都不知不晓,自然也就少却了许多伤心烦恼。
除了一些留下来侍候的太医和嬷嬷,八喜堂里的后妃贵人们早都散了,这一夜注定是个无眠夜,宫里没人能够睡得着觉。
周太后听说乱兵暴民的事后,一直有些惴惴不安,她想借颂经念佛来定定心神,可是这经文一张口就给忘了,既然定不下心神,周太后只好借着人多来壮胆,她把陈太后请来坐镇,又把汪皇后给召来,还把贵妃康妃寿妃甚至宁妃都叫到体仁阁里,陪着她一块闲坐。
汪皇后心里其实急得不行,外面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这马上都快子时了,宫门外的士兵百姓们怎地还聚拢未散?皇上只怕又犯了心慈手软的毛病,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是委决不下的。既然举国都说太宰有罪,那就该让他去领这个罪!眼前可不是行仁义的时候,乱兵和暴民要是头脑发热,做下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那才真正是天大的祸患!
唉,往往这没有替罪羊的时候,无中生有的都要找出一个来,眼下现成的替罪羊就在宫里,却舍不得抛出去息人怒平人怨,皇上怎会如此的没头脑?放着圣明天子不做却去做昏君!
汪皇后如坐针毡的陪伴着周太后,屡屡提出要去悟道堂,可是周太后偏偏不肯放皇后走,汪皇后心里因此有些抱怨:皇上和太后这母子俩个都是一样的糊涂,绑死都要绑死在一起!
体仁阁里,大家坐在一起,一开始还唠叨琐碎的说上几句,到后来这话就越说越少,越说越不知道该说什么。王宁妃瞌睡虫上身,早背着人偷偷打了好几个哈欠,说也奇怪,她听得周太后说话,就想要打哈欠,止都止不住。
时已午夜,周太后遥遥听得远处的喧哗叫嚣,忽然一声哀叹:禁军究竟为何事闹腾?就算再没有饭吃,也少不掉禁军的这一口哇……
王宁妃正躲在陈康妃的身子后面闭目打盹,听得周太后这声哀叹,眼睛还未睁开,就接上口说:都说是太宰周大人祸国殃民,搞得天下民心尽失,所以才会动荡不安,祸延宫里……
周太后听了这话,勃然大怒道:又赖上我们周家了不是!这都是江南遭了水旱,天灾引起了人祸,于我周家有什么干系?你们老是纠缠着不放!这些乱兵暴民都是身上长着反骨的贼强梁,皇帝待他们就是太心慈手软了!早该将他们抄家灭族,看他们还敢不敢犯上作乱!阿弥陀佛!真要气死我了!
王宁妃怯生生的说:太后老菩萨,这可不是奴家瞎编话,宫里人人都是这么说的……
周太后高声道:太宰再不好,与你有什么相干?皇后,你说说,后宫的嫔妃一个个都管起外事来了!
汪皇后没好气地道:太宰再不好,与你王宁妃有什么相干?什么祸国殃民,什么民心尽失,当着太后老菩萨的面,这话就能随便说么?再说这些谤讪,明里骂的是太宰,暗地里却是在骂皇上……你们当真看不出皇上是在代人受过?京中闹了一天,铺子抢了,六部衙门也烧毁了,闹啊闹的,总算闹出事来了,却没个人出来担责顶罪,这不,终于闹到宫外来了,自然也都成了皇上的不是!哼哼,等到闹进宫里来,那就不仅仅是皇上的不是了……
皇后话里有话,周太后听得一怔,想想也有些道理,一时到说不出什么狠话来了。
陈太后在一旁赶紧打起了圜场:时辰不早了,打发她们都去安歇吧,乱兵暴民想来也不至于在宫外安营扎寨吧,等皇上出面抚慰,该治罪的治他几个,隔上几天也就应该无事了。
陈太后事实上内心也在担忧,她这天前后打发了十几趟人去金仙坊接长公主,可是宫车连宫门都不能出,更遑论出宫去接人了,所以竟不知道长公主到底安然与否。
听了陈太后的话,周太后终于有气没力的摆了一下手,点头说:那就都歇着去吧,说不定到明天就大事化小了。
王守礼站上城楼宣谕的时候,还以为皇上这道谕旨已经算是低声下气了,乱军和暴民应该知足而止,四散归营。谁知,宫外的百姓将士们仍然不肯散去,嚷嚷着定要见到奸佞国贼的项上人头。
王公公一时生起气来,站在城楼上大声呵斥:你们莫非是想谋逆造反?要挟天子,诛杀公卿,聚众生乱,目无国法纲纪,实属大逆不道,若不翻然悔悟,则身死族灭,感叹无门。今日之事,皇上已予宽宥,若还聚啸宫门,便是抗旨违命,罪同于谋反叛逆!到时候法不容情,虽有丹书铁券,亦救不得自家的性命!南营的马都尉,储都尉,钱都尉都在么?还不出来约束部下!皇上对你们一直寄予厚望,你们就是这样报答圣恩的么?
张成义暗中安排军士们同声高喊:周公不死,国难未已,请皇上诛奸佞人头,取信于天下万民……
王守礼怒道:朝廷之事,与禁军何干?太宰有罪,自有圣上降罪惩治,岂容尔等喧哗鼓噪,朝廷养兵,难道是让你们围宫逼君的吗?养狗都还知道护主,养你们竟不知君恩深重?……
王守礼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一枝冷箭从他的帽旁飞过,一箭之后,乱箭齐射,吓得城楼上的几个小内侍叽叽哇哇直叫唤:“反了!反了!禁军造反了!”当下簇拥着王守礼朝楼下飞奔而去。
子夜时分,汪皇后从体仁阁出来,本来想去悟道堂,临时却改变主意,去了太子所居的景明楼。
太子刚刚睡下,皇后便不让人惊动,太子妃和良娣也都刚睡,听了传报后,赶紧起身迎接母后的大驾。汪皇后看着她们两个,先叫唐良娣去歇了,却单独把储妃留下来陪在自己身边。
太子妃周鸾这会儿手足无措的显得有点紧张,因为皇后沉着脸,一直没有开口说话。而等到皇后说话时,这劈头第一句就让周鸾心惊肉跳。
“禁军要诛国贼,清君侧的事,东宫想必都知道了?这国贼奸佞,太子妃想来也应该知道是谁吧。”
太子妃面色发白,张口结舌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汪皇后看着她,叹息了一声: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所以我才来听听你的意思……
太子妃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颤颤地说:儿臣惟父皇母后是命,何敢有微辞!
汪皇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储妃讲,她的眼睛移向头顶上明晃晃的宫灯,灯亮得有些刺眼,汪皇后的眼光一掠而过,最终又落在周鸾的脸上,储妃的脸色有点凄惶,皇后不觉有几分怜惜,因此皇后特意放低了声音对她说:有些事,你就咬牙忍着吧!忍到你出头的时候……
周鸾低着头,垂着眼皮,应了声“是”。
汪皇后淡淡地说:你也去歇着吧,凡事别想得太多,皇上也有皇上的难处。
太子妃强忍着不曾流下泪来,但她的身子却有些发冷,她明白她爷爷周太宰这回性命难保,而她却什么都做不得。
皇后在来景明楼之前,心中已经有了主张。要是情形实在不对的话,那也只有做弃卒保车的打算。被汪皇后所弃的当然是太宰周如乐,周如乐是太子妃周鸾的亲祖父,所以她先来跟周鸾说一声,让储妃心里有些准备。
汪皇后还想着闲话两句,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在踢踢沓沓的疾跑。
“反了!反了!禁军造反了!……”内侍们的声音因为过于紧张而显得凄凉凌厉,象夜枭的叫声,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直叫人汗毛倒竖。
“反了!反了!禁军造反了……”汪皇后的身子一阵阵的发起了寒颤,整个人就象失足掉进了冰窖,给冻得麻木了。